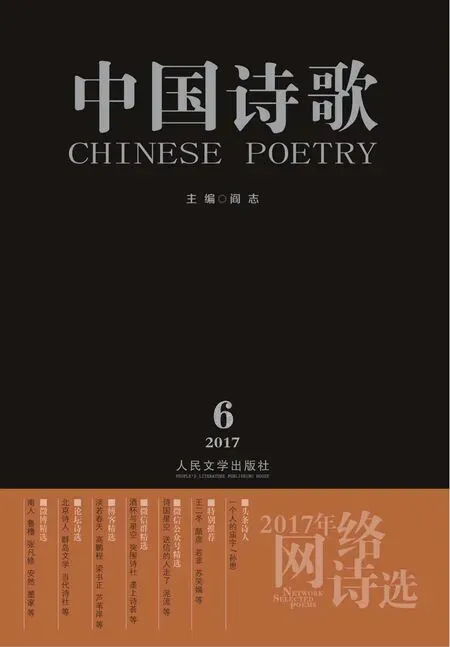一個(gè)人的廟宇
□孫思
一個(gè)人的廟宇
□孫思
·組詩·
一滴淚
一滴淚
從心里洇出,漫上眼睛
經(jīng)歷了怎樣的歷程
它的清涼與安靜
是不是讓我們想到
一個(gè)眉目清晰的女子
嬌弱的黛玉一樣的女子
它的晶瑩與圓潤
與一顆露珠多么相似
它從一個(gè)人的眼睛里
滾落、下跌,其距離和速度
與一顆露珠從天空到
一棵草一朵花的距離及速度
誰更遠(yuǎn),更快
它落下
是不是不及捧起就碎
它有時(shí)是否,更像一粒
火燒過的炭,其灼痛
能傷及我們多久,會(huì)不會(huì)
讓我們瞬間失去辨別
失去邊界
它為什么流
為誰流,里面是否藏有一個(gè)人
這個(gè)人什么樣子
有著怎樣的一副俠骨
它是從什么時(shí)候開始
以這樣的一種方式看他
凝視他的,他到底帶給它
多少的傷痛和悲涼,他知不知道
這一生它注定,為他生而生
為他死而死
從他走進(jìn)眼睛的那一刻
它便從心起,為他站成
一個(gè)人的湖泊,今生今世
再退無可退
因?yàn)?/p>
一滴淚承載的
必定是一顆心承載的
一棵樹
一棵樹站在高處
被風(fēng)吹,冷不冷
從出生到死
一直站著,如果能松一口氣
是否想過跪一次
除此外,有沒有想過
這是自己的第幾次輪回
下一次,又轉(zhuǎn)到哪里去
前世愛的人在哪里
這一世她投的什么
一匹馬,一頭牛,一只兔子
飛蟲、蚯蚓,甚或一條魚
她從你身邊經(jīng)過時(shí)
能否認(rèn)出,你是她前世的愛人
每一世里
你所必須承受的一切
擔(dān)當(dāng)?shù)囊磺校θプ龅囊磺?/p>
又是為了誰
這樣的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在六道中輪回
能有幾世相遇
這個(gè)詰問
于你是不是一個(gè)死扣
今生無法明了
來生也一樣
一雙眼
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遠(yuǎn)處的,近處的
入到眼里來,入不到眼里來
取決于視力,還是取決于心
如果空出內(nèi)心
一雙眼是不是可以看得更遼闊
眼里有的,是否心里有
眼里無的,是否心里無
迎面過來一個(gè)人
眼睛看到了,心能否看到
心看不到,這個(gè)人存在
還是不存在
有時(shí)不用眼睛看
我們是否能在心里模擬出一個(gè)人
并一廂情愿地遙想著他的一切
他的飄逸、灑脫與才情
只要想著他,我們的思想
就可以飛越三千里,于一個(gè)夜晚
抵達(dá)他溫暖的懷抱
然后,忘記歸途
如果別離真的
不能不來,離開他的一瞬
是否就會(huì)凋謝,就如三月或四月
落在地上的花,雖然眉目依然清晰
其蒼涼和安靜,卻如同水面
這時(shí)的月,應(yīng)該是下弦
缺月疏桐間,回響著更漏的凋零
似乎一夜之間,已然深秋
這樣的一種涼,他會(huì)否憐惜
而那些曾經(jīng)擁有的
是不是也會(huì)變輕,并漸漸
沒有了重量,仿佛風(fēng)和水
也能從里穿過去
即便這樣,是否仍想過
把他的身影,身影后的木格子窗
窗下的水,水上的燈光
以及那點(diǎn)秦淮的味道
一起放在,心的驀然回首處
即便目光看不到,心看到
一扇門
一扇門
開與合,是不是人心的
開與合
開時(shí),什么能進(jìn)來
什么不能進(jìn)來,合時(shí)
什么能留住,什么不能留住
這些,人是不是無法左右
偶爾,門外飄過的細(xì)雨
像不像,你心里那個(gè)女子的淚
這一生,你是不是注定
要負(fù)她
偶或的瓢潑大雨呢
像不像你內(nèi)心的起伏
一波按下,一波又起
你真的打算
讓她永遠(yuǎn)立在門外
立在門外,誰的心更疼
有一天
她真的不見了,你到哪里去找
你能相信
今生忘了她,她的清純她的脫俗
她的純良,她的不食人間煙火
你都能忘
那么她的眼睛呢
那雙把所有對你的情藏在里面的
深潭一樣的眼睛
你曾用筆描繪過的眼睛
還有永遠(yuǎn)為你所想
為你所痛,為你死去活來的一顆心
像一張白紙?jiān)谀忝媲罢归_
什么都不占的一顆心
你真的舍得舍棄
真的舍棄了
你能告訴我,今生
你還有什么
還能剩下什么
一座城
一座城
給予我們的留戀
如同,我們對某一個(gè)人的留戀
沒有了那個(gè)人
城便是一座空城
那些人來人往
車來車去,那些繁華與熱鬧
行走在我們身邊,如行走在紙上
沒有一絲熱氣
那些晚上亮得像白天的燈
于我們也是冷的,涼的
像這個(gè)城里,人看人的眼睛
還有那些樹木花草
院子房子,甚至一雙碗筷
一道歌聲樂曲聲,也都是別人的
只有一兩只不知名的鳥
或麻雀什么的,偶爾會(huì)
停在我們的腳邊,深情款款地
看我們,讓我們懷疑自己前世
也是一只鳥或麻雀
在這座城里
我們只有他一個(gè)人
因?yàn)檫@個(gè)人
我們最終選擇了留下
選擇了留下,我們便從此選擇了
孤獨(dú)和凄清
那些我們甘愿咽下的
甘愿承受的,甘愿柔腸寸斷的
是我們的苦,也是他的結(jié)
我們在這座城的每一個(gè)黃昏
每一個(gè)夜晚,都會(huì)眼巴巴地
盼著他出現(xiàn),像云出現(xiàn)在天空
風(fēng)出現(xiàn)在原野,星星出現(xiàn)在天幕上
那么自然
但是這樣的盼望
總是令我們落空
于是,這樣的黃昏和夜晚
我們只能學(xué)著
把自己的心剁碎,往神壇上供
供成一座城的模樣
一張紙
一張紙
空空時(shí),其白是不是
明凈的白,白天一樣的白
這個(gè)時(shí)候
它的明亮,多么像我們的童年
清澈如水的童年,鴿哨一樣
清脆與遼闊的童年
一張紙如果落上什么
它就是人間,就是生活
或者舞臺(tái)
有人在上面演戲
讓別人哭,有人看別人演戲
自己哭
它很熱鬧
只是這樣的熱鬧,是遙遠(yuǎn)的
不著邊際的,是人家的
雖然很生活,卻又似乎在生活之外
一張紙如果落上一幅畫
不管濃墨還是素描,近的、遠(yuǎn)的
我們就想靠近它
然后任憑自己的想象
在畫面上走,或?qū)ふ?/p>
那些被我們丟失的,忽視的
或遺忘的
有時(shí),一張紙上
會(huì)迎來很多人,來自天南地北的
說著各種方言的,但這些人里
沒有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親人
始終立在,一張紙最初的
空白處
這么多年
他們沒有移動(dòng)過
從來沒有
一場雨
一場雨
起源于哪里,它的水從哪里來
是一片云,還是一條河
每次的來與去,有沒有
命定的秩序
一場雨下來
最先澆濕的是植物、房屋
生靈,還是人心
讓太陽走開
讓三萬里月光隱沒,讓天地微瀾
讓所有生靈草木,低頭接納
讓一種寬廣的透明
直抵萬物本心,之后
藏起一身的肉欲
這樣的雨,是不是
有我們不知道的,無數(shù)可能
它從上而下的清洗
鋪天蓋地的清洗
還原了什么
一塊石頭還原了俊朗
一朵花還原成女子
一棵樹還原了六根清凈
落葉還原成鳥在飛
人呢,被清洗后
還原成什么,能否丟掉愚癡不化
回到人之初
即便有,還原也只在一瞬間
或更短的時(shí)間
人世間一切
都在往前走,人、動(dòng)植物、河流、日子
一切有生命的,無生命的
都無法停下,回頭
我們曾經(jīng)的愛
也不能,那些黃昏那些夜晚
我們說過的甚至起過誓的日日暮暮
你儂我儂的日日暮暮
過了就過了
再回不來
沒有什么能改變
一場雨也不能
一滴水
一滴水
從天空、從房檐、從樹上落下
是否感受到,風(fēng)如刀片般
穿過自己的身體
能否聽見風(fēng)聲
從身體里呼嘯著穿過
這種漏風(fēng)的感覺
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摔在地上
碎成粉末,潰不成型時(shí)
它是不是五內(nèi)俱焚
躺在地上
散發(fā)著的骨質(zhì)的寒涼
是不是讓每一個(gè)經(jīng)過它身邊的人
不敢回望
它被蒸發(fā)前
惟一的意念是什么
是天空,還是深愛著的人
有時(shí)候,我們多么喜歡
把一滴滴水疊加,放進(jìn)鍋里、壺里
燒上一百度,然后九死一生地
把它倒進(jìn)茶杯
讓它把茶葉泡成森林
似乎那里,是惟一沒有污染
非常的潔凈和透明,是高處的湖泊
它應(yīng)該在,必須在那里
我們甚至不及問問它
被燒煮時(shí)的翻滾和呻吟
是它痛到極致的歡愉
還是因?yàn)椋瑥慕窈?/p>
它再?zèng)]有了
一年四季的涼
一片云
一片云
在天空飄,有沒有想過
在什么地方,棲下來
偶或的雨
是不是它的淚
它是否想過跟太陽
跟月亮,跟星星,甚至跟風(fēng)說說
說說這些年的艱難
說說這些年的孤寂
說說這些年所有的無助和無依
這樣想著的時(shí)候
它是否早已眼睛發(fā)燙
淚流滿面,直至熱淚滂沱
其實(shí)它知道
說能怎樣,不說又能怎樣
某些東西
或許永遠(yuǎn)不能說
那種潛藏到深淵里的東西
比如一份情,對誰都無法說
我們曾經(jīng)多么希望像它一樣
在天空里自由自在
停停息息,息息停停
走過的所有地方無跡無痕
什么都不沾
但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無有來,無有去
無有增,無有減
做不到,不是我們因緣不具備
是我們的智慧之源
被我們的欲望占領(lǐng),然后不得不
為我們的欲望付出代價(jià)
我們回不到,永遠(yuǎn)回不到
生命的原態(tài)
一幅畫
一幅畫色彩的明與暗
與一個(gè)畫家一段時(shí)間里生活的
明與暗,是否有聯(lián)系
畫一幅畫
要準(zhǔn)備些什么
除了筆、墨、宣紙、色彩
是不是還有原型
即便沒有
也該畫那些在心里久存過
映照過的
如果以上都沒有
我們能否畫,比如靈魂
比如令我們害怕的鬼
它們究竟長的什么樣子
有沒有腳,有沒有臉
是行走,是飄,還是飛
我們從沒見過的
是不是不能憑空捏造
或者虛構(gòu)
就如鏡子
有,才能照出有
無,照出的一定是無
一幅畫有時(shí)是不是
比畫家站得更高更遠(yuǎn)
就如同一部小說比一個(gè)小說家
活得更久,是否如出一轍
張大千、徐悲鴻、豐子愷
梵高、莫奈,他們有無相似
如果沒有,有象與抽象
線條與色彩,這兩個(gè)東西方特點(diǎn)
怎么相輔相融,同立一幅畫
都說水有魂魄
臨到絕境,總會(huì)瀟灑一拐
畫上的那些花卉、山水、動(dòng)物
是否也有,如果有
它們會(huì)在什么時(shí)候開放
流淌和奔跑
它們會(huì)不會(huì)因此
讓一個(gè)畫家,深夜停在
宣紙前的時(shí)間更長
一座廟
我們對一座廟的膜拜
與故鄉(xiāng)是否一致,那個(gè)
清貧、空明、澄凈的故鄉(xiāng)
在我們心中,是不是
如同一座廟宇
那些親人呢
是不是都是我們心里的佛
皓月當(dāng)空的夜晚
立在田野里的莊稼,在我們眼里
是否如同菩薩
一個(gè)宇宙盛得下
百千萬億的佛,或無量佛
一個(gè)故鄉(xiāng)能否盛得下
一座廟能否盛得下
我們懷著敬畏和信賴
與一座廟會(huì)晤,走近臨于我們的佛
把我們原本的自己,我們的罪過
帶到佛前,懺悔我們的罪
這個(gè)時(shí)候
那些掙扎那些不堪那些無法回首
又不能不回首的,那些我們不愿做
又不能不做的,是不是都可以放下
求得暫時(shí)的清明
一炷香、一個(gè)跪拜,
一聲禱告,真的能抵消
十萬八千個(gè)孽障,如果可以
我們是否愿意每天長跪不起
待經(jīng)聲響起,我們和那些
生長在山川險(xiǎn)谷,黑暗隱蔽之地的
花木藥草、大小諸樹、谷物禾苗
飛鳥禽蟲,是不是都該低垂眉目
虔誠傾聽
那些逝去的
在泥土下一直仰頭看著我們的親人
是否也能聽到,聽到后
他們是不是就不會(huì)冷
不會(huì)感到黑
每去一次廟里
我們是不是有
回一次故鄉(xiāng)的感覺
然后,心有皈依
一座橋
一座橋
把自己放于水之上
四面的風(fēng)朝著它吹
是否給我們
一種獨(dú)立于世外的涼
那些立于水之下的
比喻水草,比喻魚比喻礁石
以及月亮的投影,像不像
水里的另一個(gè)天空
水上的你
涼薄的身子,平直的身子
弓了又弓的身子,像不像一條路
偶或的一兩聲鳥鳴
是不是你懷里的春天
每日里
你把一些人流和車流
從此岸渡到彼岸
再把另一些人流和車流
從彼岸渡到此岸
這其中有多少
是去了又回,回了又去的
又有多少是去了
再回不來的
撞開的歲月的出口
是不是你的出口
這些你獨(dú)自看到和承載的
應(yīng)不應(yīng)該歸于虛妄
歸于虛妄,所有的生滅就沒有生滅
沒有生滅,你才能如見如來
就像人們心心念念放不下的
如同水露,如同閃電
雖然呈現(xiàn)過,不久又消失的
不可取不可說的愛情
一切佛、一切法
一切僧發(fā)愿,讓眾生不愚癡的愛情
于你,它們是不是
無所來,無所去
經(jīng)年如此,終身如此
一間屋
一間屋的木訥與內(nèi)斂
會(huì)不會(huì)讓我們想到一個(gè)女子
想到一只陶瓷的端莊與靜謐
其地方的狹小
是女人的直徑,還是半徑
其一生在里面走
是否有過心生厭倦
于男人,是否如同酒店
人棲下了,心在另一個(gè)地方
除了男人女人孩子
還有什么,壁虎、蟑螂、臭蟲
蚊子還有灰塵,是否與他們同住
最終,是人住得久
還是它們住得久
有時(shí),當(dāng)我們
帶著蒼涼、隱忍、苦修
仰首問天,還不如回到屋里
坐在一盞燈下,喝一杯熱茶
聽一句軟語
但我們在屋里
總想著往外跑,情愿把自己置于懸崖
鞭打、推搡,搖搖欲墜
讓自己,處于臨淵狀態(tài)
我們不知道
這樣的心幟在外,終有一天收不回
當(dāng)風(fēng)吹著,這世界只剩下風(fēng)
我們能從,哪個(gè)風(fēng)口回來
回不來,我們的家人怎么辦
我們的孩子怎么辦
到那時(shí),即便我們懺悔
這樣的懺悔,一座教堂
盛不盛得下
從此后,家人是不是只能
立在窗口、門口、陽臺(tái)、院子里
朝著一個(gè)方向眺望
那個(gè)時(shí)候,我們在哪
是不是變成翅膀,羽毛似的翅膀
手臂一樣的翅膀,在黑暗中飛
一直飛,一直飛,即便墜落
卻不知道疼
一枝葦
纖瘦地立著
一邊是水,一邊是岸
內(nèi)心究竟傾向誰,是否想過選擇
還是無從選擇
夜晚,風(fēng)很大
吹得黑夜像一張網(wǎng)
你在風(fēng)里搖擺,彎腰、匍匐
風(fēng)過,再還原,這樣的折騰
從生到死,有沒有停息過
我們不能用英雄的名字
命名你,只能用草的名義
所以枯了,也說是死
不是犧牲
你在水邊出生
走時(shí)也在水邊走,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
多么像一個(gè)男人
如果把水比喻女人
就連默默地,無遮無擋
被四面的風(fēng)吹,霜打,雨雪浸染
其活法,也是男人的活法
冬天里,你一頭白發(fā)
被風(fēng)掀起,四面八方飛
這樣的辛酸,會(huì)令我們想起童年
想起母親,如今她在哪里
那頭白發(fā)是否有人給她梳理
每日里,看著夕陽沉降
一點(diǎn)點(diǎn)地,消失于天際
是否想過,明天,太陽升起的時(shí)候
自己還能否站在這里迎接
如果不能,于你是不是一種解脫
人生像復(fù)雜的四則運(yùn)算
你肯定也不例外,無論過程多么曲折
得數(shù)終究是零
人總是對不按規(guī)則的事
心生恐懼,你是否也同樣
一條河
一條河
一直向前,從不回頭
是否因?yàn)椋仡^無岸
長年的奔跑
它都經(jīng)歷過什么,有過
什么痛,什么苦,什么樣的
牽腸掛肚
它的身體又承載映照過什么
船、水草、樹影、帆影
天空、太陽、月亮、云朵、星星
閃電、雷聲、鳥聲、笑聲
路燈微明
它一路馱著它們
像馱著自己的親人
不離不棄
從我們第一眼看到世界時(shí),
它就在那里,無論見與不見,
無論我們幸與不幸
它都在
秋天里,最早落下的葉子
最早帶著一絲冷意的風(fēng)
最早變冷的暮氣、寒露
都先從它身上過
它知道花蕾、小草、樹是什么
知道它們在三月的春天和九月的秋天
是什么樣子,知道人的一生有多長
多長時(shí)間,能度過
知道除了河流、石頭和土塊
這世間的一切事物,都不會(huì)長久
都將會(huì)化為無
化為無
才能沒有痛苦
沒有守望,沒有死去活來的愛
并達(dá)到最終圓滿
因?yàn)橹挥凶顖A滿的
才無相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