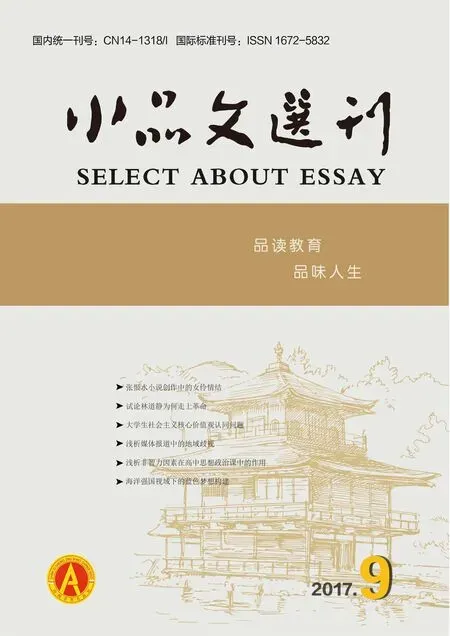戚城會盟臺之盟誓文化
崔閃閃
(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戚城會盟臺之盟誓文化
崔閃閃
(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本文以濮陽市戚城文物景區為研究對象,對其特色資源構成、特征進行系統地分析,全面了解內在文化與價值,進一步引申春秋盛行的鼎盛文化對戚城的反應及帶來的影響。盟誓制度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際交往、斗爭與聯合,推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到今天,國際間外交盟約的活動越來越頻繁,這種盟約逐漸演變成了合同、契約的形式。戚城是豫北地區保留年代最久,延續時間最長的古代聚落城址,它不僅是衛都帝丘北面的重要屏障,也是諸侯爭霸的戰略要地。
戚城;會盟;盟誓
1 戚城會盟臺概況
公元前623年晉楚“濮城之戰”之后,晉國稱霸中原,繼而衛國自楚丘遷都帝丘,在此之后,戚城的戰略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諸侯國都竭力控制這片區域,戚城逐漸成為諸侯會盟進行重大外交活動的場所。據《春秋左傳》記載:從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這近一個世紀內,各國諸侯在衛國境內會盟十五次,其中七次在戚城,會盟議題涉及戚地的歸屬,衛國內政,援助被侵略國家,背盟與續盟等事宜。
戚城會盟臺位于濮陽市戚城文物景區內,戚城又稱“孔悝城”,是一處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同時是豫北地區保存較為完整的古城址。會盟臺位于戚城遺址東門外80米處,有一方土臺建筑基址殘存長達20米,寬16米,高4米,為春秋時期夯筑高臺,原有東、西兩臺,現僅存東臺。臺上面積至今尚有畝余,生長著茂密的植被,會盟臺最底層由十幾層古方磚壘搭而成,上面覆于毛土,成金字塔狀,巋然不動屹立至今。1991年戚城文物景區建立,成為集古遺址保護、歷史文化展示、旅游觀光、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歷史文化大觀園。
2 原始社會始會盟,至春秋而盛
會盟始于原始社會,盛行于春秋戰國時期,是當時諸侯或卿大夫為達到鞏固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的政治目的,經常舉行的一種具有制約化作用的外交禮儀活動。會盟各方協議達成后殺牲取血,飲其血,坎其牲,對神靈作出信守諾言的保證,主持會盟者叫盟主,盟主多半憑仗自己的實力,打著“以德服人、抑強扶弱、輔佐周室”的名義來發號施令。涉及援助被侵國家衛國內政、續訂盟約、戚地歸屬等事,諸侯在戚的會盟次數之多,范圍之廣,在春秋史上尚不多見。
西周時周天子在冊命諸侯時,之所以采用盟誓方式目的是為了借助神權約束以加強受封諸侯與王室聯系,并將異性貴族納入周人宗法統治結構,以擴大西周王朝的統治基礎。《左傳》隱公十一年說:“周之宗盟,異姓為后”。由此可知西周統治者對內實行分封,對諸侯、卿、大夫以盟相系,諸侯“分宗”盟誓,是組建西周地方政權,建立諸侯國統治秩序的開端,也是受封諸侯與異姓“分族”構建隸屬關系的主要方式。鼎盛時的盟誓活動是春秋時期最顯著的特點,戰國時已經出現的這一現象被指責為是不德、不信的產物,春秋時期,禮崩樂壞,更加需要利用盟誓取信,以此來維持社會秩序。
《禮記·曲禮下》云:“蒞牲曰誓。”孔穎達疏曰:“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由此足可看出,盟誓儀式的程序分別是殺牲、歃血和宗誓。殺牲歃血的目的主要是敬獻神靈,并通常用牛、羊、豬等這些動物奉獻給神靈,表達最高的敬意。宗誓為向神靈陳述自己的意愿和遵守諾言的決心,后記錄宗誓誓言的載書出現并伴有一定的儀式。當時的人們之所以盟誓,正是因為它是非常鄭重之事。《左傳》成公十一年“齊盟,所以質信也。”《左傳》襄公九年:“盟誓之言,豈敢背之。”《左傳》昭公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以此可見,盟誓正是當時人們消除彼此之間信任危機所采取的理想方式。
3 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戚城遺址
平王東遷后,王室實力日漸衰微,盟辭也顯蒼白,周王逐漸失去了對會盟權的控制,周王室衰落,對以前俯首稱臣、仰其鼻息的各諸侯來說是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最早發展起來的是黃河中下游的鄭、宋、衛、齊、魯、陳、蔡等國。《春秋·左傳》記載,從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近一個世紀內,各國諸侯或卿大夫在戚城會盟七次之多。涉及到戚城的歸屬,衛國內政,背盟與續盟,各國之間的疆界與婚媾,援助被侵國家,討伐某一國家……
《左傳》:(魯)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衛國不尊從晉國,出兵攻打鄭國。在得到周王準許后,晉國出兵討伐衛國,占領衛國門戶重鎮戚城,威脅衛都帝丘。魯國大夫公孫敖出面調停,與晉襄公會于戚,重新劃定戚地的疆界。
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契約和法律的作用越來越大,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逐漸由法律與契約來協調制約,逐漸由強權與實力取代神權。秦之后的盟誓大都流于形式,它的作用在逐漸削弱,盟誓在政治上的作用更是明顯弱化,然而在民間,盟誓仍然持續了一段時間,作為一個團體,一個社團秘密結拜所遵循的形式,直至今天也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古老盟誓的遺跡。
盟誓是一種遠古信仰,信仰在中國源遠流長,歸宗于中國自古就形成的“和合文化”。它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整體系統思想。它的內涵不僅包括“和”的和諧、和睦、和善、和平等與“合”的結合、聯合、匯合、合作等,更重要的還有團結、協作、凝聚、向心的含義。 “山積而高,澤積而長”,“親望親好,鄰望鄰好”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踐行親、誠、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亞洲國家。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愿意支持和幫助亞洲各國人民實現各自的美好夢想,同各方一道努力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發展的亞洲夢,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1] 雒有倉,論西周的盟誓制度[J]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二期.
[2] 馬連城,春秋時期的會盟勝地——戚城[J].中州統戰.1998.05.25.
[3] 康維,春秋盟誓制度的特點及其演變研究[J]2013.05.01.
[4] 吳承學,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蘊[J]文學評論.2001.01.15.
崔閃閃(1990.12-),女,漢族,河南,碩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區域文化與旅游經濟。
I206
:A
:1672-5832(2017)09-01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