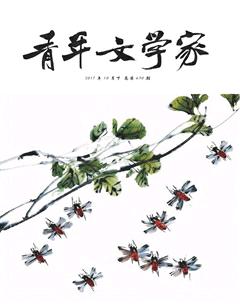格非:從先鋒到隱身
黃澤++王佳豪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江蘇大學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項目基金資助。
摘 要:作為當代文學先鋒作家三駕馬車之一的格非,在2011年十年磨一劍完成了“江南三部曲”的創作,并且很快在2012年推出新作《隱身衣》,兩個系列作品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且創作時間間隔甚短,聯系甚多,作家理念和思想意識的嬗變蘊含其中。
關鍵詞:格非;江南三部曲;先鋒;轉型;隱身衣
作者簡介:黃澤(1996.10-),第一作者,江蘇江陰人;王佳豪(1997.5-),第二作者,江蘇蘇州人。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30-0-03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2011年秋出版后不久的2012年4月,另一短篇小說力作《隱身衣》也出版了。作為80年代先鋒小說“三駕馬車”之一的格非,一向被認為以一種“學院派的精致”區別于其他先鋒派的作家。“江南三部曲”和力作《隱身衣》作為格非在新世紀的轉型之作,體現了他從八十年代敘事技巧上的創新開始轉向關注現實,關注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的思想內容層面的嘗試。
透過“江南三部曲”,格非將中國百年的時代轉型折射于三代人的故事身上。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格非對現實和歷史的思考與追問,其先鋒思想有轉向關注現實的跡象。
可是,當我們以為格非從宏觀的歷史背景和個人敘事角度即將向我們揭露現實的傷疤,或者將帶領我們反思人性現實的底色時,一部《隱身衣》卻向我們展露出作者選擇回避和隱身的消極思想回潮。山東理工大學張艷梅教授分析認為“格非算是理想高地的堅守者”,“他從先鋒到現實,從知識分子寫作到反思知識分子意識,始終致力于祛除歷史與人生遮蔽,而那對隱形的翅膀,是否可以喚醒我們飛越中國式瘋人院,還有待時間給我們更清晰的答案。”[1]
然而時至今日,格非給我們的答案應該很明顯,他沒有像賈平凹閻連科一樣關注并揭露社會底層真實,也沒有像方方一樣用真實的筆端展現普通個人生活的五味雜陳,他沒有從先鋒走向現實,而是從先鋒選擇了隱身。作為象牙塔中的學者型作家,“現實”作為格非創作中的一次漫長嘗試,最終還是沒能堅持下去。
一、“江南三部曲”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江南三部曲”又被稱為“烏托邦三部曲”,其中的人物形象不難看出格非自身的觀念投射與影子。正如格非自己所說,“端午這個人物是不是有我的影子,我固然不能否認。但我想說的是,所有的人其實都有我的影子。我把自己的情感和想說的話,通過某種特殊的處理,分攤到了每個人的頭上。”[2]從作品中知識分子的形象角度可以觀察到格非十年磨一劍的寫作過程中的思想轉變。
(1)《人面桃花》──構建“烏托邦”
《人面桃花》的故事背景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前后的中國,無論是陸侃的“桃源夢”,王觀澄的“花家舍”還是陸秀米張季元的革命夢想,都是在亂世之中從無到有構建理想社會的過程。他們游離于烏托邦的理想實踐和退避歸隱的傳統抉擇之間,他們對現實失望不滿,對理想執著到瘋狂,更存在一種激進的變遷。無論是陸侃和王觀澄這類傳統知識分子的桃源夢境的追求還是秀米和張季元這類現代知識分子對于現實革命理想的追求,社會大環境都是民不聊生,黑暗腐朽的,因此知識分子的追求是有力的是瘋狂的,也是對現狀的大膽反叛。
(2)《山河入夢》——建設“烏托邦”
《山河入夢》中秀米之子譚功達身處社會主義改造階段,比起上一輩人有著較少的束縛和領導的權力支持,但仍在追求自身烏托邦理想時面臨各種各樣的現實矛盾。
在這一階段,社會的總體環境是安定完整的,因此對烏托邦世界的追求是從有到優的“建設”。但是即使如此,小說中譚功達身上洋溢的激情和夢想仍顯得另類瘋狂,作家沒有將這種現實與烏托邦的矛盾在一開始就完全激烈的暴露出,而是以一種充滿陰影和變故的方式表現在主要人物譚功達和姚佩佩精神的掙扎還有與命運的抗爭。建設“烏托邦”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知識分子瘋狂的夢想最后同樣陷入了困境。
(3)《春盡江南》——禁足烏托邦
如果說之前的兩代人關于烏托邦的追求都是構建新的社會或者建設新的世界,那么《春盡江南》一書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則顯得不倫不類。知識分子不再是社會時代的先鋒,時代也似乎不需要知識分子來指引什么方向,八十年代思想的浪潮短暫而尷尬,思想的快速退潮讓很多知識分子沒有做好退幕的準備,更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思考來產生新的有力的理想追求。“烏托邦”再也不是一個追求,而變成了他們中一部分賴以藏身或禁足的夢境。
在《春盡江南》一書中,知識分子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大潮下異化、被擠壓的存在,前者如守仁,吉士,地方志辦公室談《莊子》的馮延鶴,后者如家玉,綠珠等;第二種即像端午這樣活在過去,禁足于自身夢境理想的“正在爛掉的人。”
烏托邦的理想熱情在第三部《春盡江南》中驟然消褪,格非用現實的語言勾勒出當代知識分子的群體現狀。從先鋒向現實的轉型嘗試在本書中達到了最高處,卻也是格非的支持者們最難以適應和接受的:這些瑣碎而日常的生活場景怎么和他之前的風格不一樣?為什么沒有看到崇高理想追求的悲壯失敗,烏托邦的夢想去了哪里?
但是格非本部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在于此,本書作為對知識分子精神和心靈的反應,寄托著格非對存在知識分子現狀的哀嘆和自憐。“縱觀整部小說,似乎沒有一個成功者,而是由一群淪陷于物欲橫流時代的知識分子構成的哀世之書。”[3]這部哀世之書流露出格非對知識分子精神現狀的探索和反思意識,但很遺憾,沒有能夠繼續下去就湮沒無聲了。
(4)從“瘋言瘋語”到“失語”的共同歸宿
從“江南三部曲”截選的三個時代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與現實和社會環境的對抗和掙扎中,知識分子都經歷了一個從“瘋言瘋語”到“失語”的精神狀態。
知識分子時對時代起啟蒙作用,而他們作為行高于人的先行者,作為典型的“瘋子”常常會發表一些“瘋言瘋語”,如果說能夠發表瘋言瘋語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責任的追求之心還存在著,那么知識分子逐漸“失語”的結局是否也意味著理想追求的破滅,最終意識到自身處于社會邊緣化的無力感?
二、《隱身衣》中知識分子形象
(1)《春盡江南》與《隱身衣》的重疊
拋開《春盡江南》和《隱身衣》發表時間臨近的關系不談,新浪讀書等很多媒體在解讀這本《隱身衣》時認為“延續《春盡江南》的現實主題,《隱身衣》是格非在‘三部曲后繼續實現自己‘描寫現實、超越現實的文學野心的作品。”[4]顯然沒有注意到作家現實主義精神的消落和逃避現實的虛無主義精神抬頭。
無論是病重時家玉發出恨不得有一件“隱身衣”的信中感慨,還是《隱身衣》主人公“我”作為制作膽機的音樂發燒友身處于這個世界的隱秘核心,知識分子的形象不再像《人面桃花》《山河入夢》中那樣瘋狂而熱烈地追求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夢想,而是對“理想”一詞產生了漠然的態度。尤其是在《隱身衣》中僅僅擁有高中文化的“我”,披著隱身衣冷眼旁觀著北京海淀的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人物設定,不難看出這種隱身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在狹義上“知識分子”思想傾向流露,更成為普遍的社會生存和生活狀態。
(2)《隱身衣》中知識分子的形象變遷
如果說“江南三部曲”向我們展示的是知識分子以一種悲壯的“瘋言瘋語”追求自身理想,或者“失語”的孤獨狀態,那么在《隱身衣》中知識分子形象則是被嘲笑和虛弱化的存在。長篇大論喋喋不休的教授整天抱怨的是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之類憤世嫉俗的話題,而格非用帶有自身形象象征意味的主人公“我”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態度,“如果你不是特別愛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問底的話,如果你能學會睜一眼閉一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會突然發現,其實生活還是他媽的挺美好的。不是嗎?”[5],尤其是那個有意思的動作細節“站起身來,把褲腰帶往上提了提,用一種連我自己都覺得陌生的語調對教授說。”
在《隱身衣》一書中,江南作家格非更多的成為了久居北京海淀的劉教授,成為了古典音樂發燒友和對“知識分子群體”包括自己本身戲謔的嘲笑者。當代的知識分子形象在《春盡江南》中展現出的是“異化”和“失語”兩類,在《隱身衣》中則分為“向商業化靠攏”和“隱身”兩類,這兩種分類的標準大同小異,唯獨缺少的缺少傳統知識分子如魯迅針砭時弊的形象。格非作為大學教授,在自己的小說中以戲謔的口吻嘲笑大學教授的怨天尤人和吹毛求疵,是自我的無奈和嘲笑,也做出了自我精神價值的最終選擇。
三、從先鋒到隱身的滋味
“隱身”不僅是對于“現實”的退縮,更是未經嘗試而主動放棄的“隱身”,并沒有直接面臨現實擠壓和打擊后的束手就縛。
端午的形象遠遠沒有家玉有力和飽滿,他既沒有體現出像哥哥王元慶一樣與時代抗爭失敗后自己禁錮于醫院的決絕,也沒有像妻子家玉一樣嘗試順從社會卻依舊保持了原來的本性柔軟。端午太聰明又顯得太無能,他不溫不火,聰明地不去掙扎,守著《五代史》守著地方志辦公室的一隅,也似乎體現了作者格非的自我關照,端午不就是自始至終披著“隱身衣”么?即使在面臨花家舍成為銷金窟,即使在面對綠珠生活的各種折磨之后,即使在面對妻子出軌,家庭繁雜爭吵的時候,他無一例外選擇的都是閉上自己的雙眼,退守到自己的一方天地間。
在這一系列的創作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格非的追求和理念在逐漸縮小,他建構的烏托邦夢想世界逐漸坍塌,到了《春盡江南》之后尤為凸顯,端午的理想僅停留于自己詩意的棲居,《隱身衣》中變成了逃避現實生活的音樂發燒友這一身份的自我認同。對現狀的順從和逃避成為格非作為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開出的解決方案,他對生活中各種問題的態度走向虛無,人物形象披上隱身衣何嘗不是長期寓居象牙塔中的作者自己對現實問題嘗試無果后,自身主動“隱身”?
隱身的滋味是怎么樣的呢?用古典音樂作為自我隱匿的寄托,用《五代史》作為蔽身的翳葉,即使甘心身處社會的邊緣,也需要有所寄托,而“寄托物”就是披在身上的隱身衣也是遮羞布。知識分子提不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也喪失了啟蒙作用的力量,用“古典音樂”來作為隱身之所,作為自己劃分“高貴獨特”和“庸碌的蕓蕓眾生”之間的依據,這無疑是把音樂或者詩歌的文化趣味的標志無限拔高,隱身者以“隱身”為自己的人生哲學,暗自還包含著自己給自己建構出來的高貴感,而遠離社會,安于社會邊緣,好歹也少了被扯下遮羞布和隱身衣的幾率。
四、隱身的代價
我們無法輕易地判斷這種“隱身”思想的滋長到底是好是壞,從文學創作的形象本身來說,“隱身”的知識分子形象可以算得上是創作的一種成功,因為格非的筆觸在描繪當代知識分子時,突破了“背叛傳統的異化”與“堅持傳統下的毀滅”兩種常見的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隱身者”具有獨特的冷眼旁觀和置身之外的冷靜與疏離。
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六代:“以1949年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以及‘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6],按照學界對于知識分子的代際劃分,秀米可以劃為晚清一代知識分子,譚功達則應劃為“十七年一代”,他們都屬于前后三代知識分子的第一代,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擁有更多的社會關懷,也處在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夕,考慮的重心更多在于如何實現社會政治變革和社會建設,他們的政治意識非常強烈。而無論是90年代以后的譚端午還是《隱身衣》中的知識分子們,都開始對社會和政治興致缺缺,甚至直接選擇隱身。
知識分子沒有了“先鋒精神”和“啟蒙意識”的責任感,“隱身”的思維看起來還算完美,能夠避免自身時代背景下的迷失和異化,也能夠保持面對現實壓力下僅剩的思想和立場的獨立,然而這種隱身的代價卻是值得玩味的。
端午能夠安于《五代史》的精神世界離不開異化了的妻子“家玉”的內心煎熬和奔波,讓端午不需要操心生計與家庭的責任,否則,忙于生存的端午又有什么條件去隱身于“高貴”的古典音樂和詩歌世界中呢?忙于各種活動和組織想法的綠珠能夠掙扎于“自己為什么而活”,在新時代去追求自己的“烏托邦理想”,離不開“可惡”的姨夫老弟的資金支持。同樣,守著“古典音樂發燒友”身份自我認同的崔師傅“我”,面對姐姐姐夫的現實生活壓力時也無計可施,捉襟見肘,“隱身衣”也沒有什么效果。
因此,在真正直面現實的時候,知識分子“隱身”的思想常常是無力的,依靠某些小眾愛好圈子營造的狹小“自我烏托邦”抵擋不了現實的沖擊,即使加上“事若求全何所樂”的心理自我安慰來試圖割斷自身與現實的糾葛也常常無能為力。只有身處社會邊緣的人才能披上隱身衣,而這件隱身衣在真正面對現實時常常又無計可施。
知識分子能夠達到隱身狀態的代價常常是被忽略的,這需要現實不那么咄咄逼人,需要自我甘心地放逐于社會邊緣,需要消減自身欲望,巧妙機智地維持現狀,也同樣要回避最現實的生存問題。否則,一旦被現實大潮沖掉蔽體的“隱身衣”,恐怕也難逃“異化”或者“毀滅”的結局。
端午對家玉的憐憫和家玉對端午的嫌棄其實是一對矛盾的悖論,這無解的矛盾中看似“隱身”是一種絕妙的關注當下安穩的人生哲學,其實是先鋒作家發現自己對于現實改變無力感后的妥協和自我麻痹。即使格非已經意識到作家身上的反應和反省現實生活的責任感,也因為無可奈何的局限選擇了隱身。這是知識分子群體的無力感,即使冷靜觀察現實如格非者,也無法改變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缺乏文化巨擘,缺乏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的困局。愈清醒看見現實愈發無力,于是格非們選擇了從先鋒到隱身。
注釋:
[1]張艷梅.格非——從先鋒到現實[J].名作欣賞,2013,25,(1).
[2]格非,張清華.如何書寫文化與精神意義上的當代——關于春盡江南的對話[J].南方文壇,2012(2).
[3]張亮,現代知識分子的“哀世之書”——論格非的長篇小說《春盡江南》[J].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報,2014.
[4]新浪讀書.“烏托邦三部曲”后格非再推新作《隱身衣》[EB/OL].2012.6.11http://book.sina.com.cn/news/b/2012-06-11/1909299593.shtml.
[5]格非,《隱身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188.
[6]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