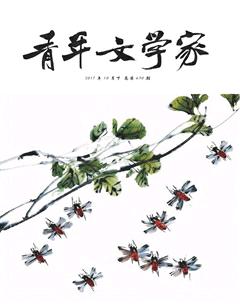阿來小說的地域文化概況和獨特之處簡述
摘 要:阿來《塵埃落定》一書,向讀者展現了宏大的藏族土司制度消亡過程,一個古老制度在現代文明前轟然倒塌的脆弱、無奈和感慨。這本書寫發生在藏地的傳奇,既融入了宗教、民族、自然等獨特的地域文化因素,又把文化的獨特性作為作家自我體驗的外在表現形式,抒發了作家個人色彩強烈的記憶,成功構建了獨具一格的作品風格。
關鍵詞:阿來;《塵埃落定》;地域文化;獨特性
作者簡介:林修蘋,女,漢族,廣西柳州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2015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30-0-02
一、小說的地域文化概況
《塵埃落定》是阿來的代表作,曾獲2000年茅盾文學獎,這是對阿來文學創作的肯定,也是對類似阿來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鼓勵。《塵埃落定》用31萬字左右的篇幅,描寫了四川藏族康巴地區土司制度的消亡史。故事發生的背景設定在藏地,使作品染上了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深厚的民族底蘊
阿來本身是一位民族“混血”作家,他的藏族血統來自于他的母親,父親是回族人。阿來選擇了藏族作為自己的民族屬性,與他浸染了藏族文化是分不開的,藏文化給予了他豐厚的饋贈。小說中不僅再現了民族歷史和人物的性格,而且還使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風格得到真正的彰顯。
藏民族文化的自覺吸收及運用使得阿來的小說創作獨具藝術魅力,阿來感受著古老的歷史文化,將夢兆、預言、靈魂穿插于小說之中,增強了文章的神秘感。小說處處展示了藏地民族風俗人情,涵蓋飲食、禁忌、節慶禮儀等方面。麥其土司為迎接遠道而來的民國政府代表黃特派員,安排了盛大的迎接儀式。“那天早上,我們從官寨出發,在十里處扎下了迎客的帳篷。男人們要表演騎術和槍法”、“土司太太奉上一碗酒、一條黃色的哈達,姑娘們也在這個時候把酒和哈達捧到了那些漢人士兵們手中。”[1]宏大的場面描寫展現了藏族人民對遠方貴客的尊敬與熱情。藏族人民生性真誠、豪放,對兩性關系少了很多禁忌,直視內心的自我欲望,并將這種欲望看做是天性神授。“男人們的目標則是姑娘們的衣衫,要讓他們在晴朗的天空下袒露美麗的乳房。”“麥其土司對兩個兒子說,古代的時候,人們還真要在地頭上干那種男女之間的事情呢。”[2]
藏族民間文化為阿來創作提供了蘊涵豐富的養分。《塵埃落定》中有較多關于藏族宇宙起源的故事,提到了關于世界組成的神話。世界是水、火、風、空四種物質,與藏族的“五源說”有著直接的文化淵源關系。另一重要的方面,《塵埃落定》的主人公傻子二少爺的人物原型,來源于藏族傳統民間故事阿古頓巴的故事。阿古頓巴在藏族人民中家喻戶曉,他智慧、善良、疾惡如仇,敢于跟壓迫百姓的富人作對。雖然傻子二少爺和阿古頓巴在身份、地位以及經歷上沒有共同之處,但二人的精神內核卻有著相似性。在《文學表達的民間資源》中,阿來談及到阿古頓巴和傻子的淵源:“在我的想象中,他有點像佛教的創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貴族階級的叛徒。他背棄了擁有巨大世俗勢力與話語權力貴族階級,背棄了巨大財富,走向了貧困的民間,失語的民間,走到了自感卑賤的黑頭藏民中間,用質樸的方式思想,用民間的智慧反抗。”[3]于是小說具備了藏民族原始古樸的思維習慣和審美特色,產生了獨特的異質感和疏離感。
(二)濃厚的宗教氛圍
阿來立足于藏區社會生活,在他力求構筑的生動、逼真的藝術世界里,必然會有對藏人充滿宗教色彩的日常生活的展示。在小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濃厚的宗教氛圍,無論是那繁復神秘的宗教儀式和傳說,還是其中隱含的宗教信仰與宗教觀念;無論是對信仰和教義忠貞不渝、有著獨特生命體驗的僧人,亦或是普通人表現出來的對宗教的虔誠與敬畏。
《塵埃落定》中描寫了藏傳佛教和苯教兩種藏族地區流行的宗教。其中藏傳佛教又分為以濟嘎活佛為代表的寧瑪派,翁波意西為代表的新格魯派。寧瑪派是西藏佛教最重要的教派之一,小說中濟嘎活佛,既是活佛,也承擔了土司家族醫藥家、歷史學家的角色。新格魯派在15世紀初創立,格魯派提倡僧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律。苯教則是西藏本土固有的原始巫教,其形成時間很早,在佛教入藏之前就已經形成。苯教崇拜天和自然萬物,認為神和鬼怪最多。苯教的醫學源遠流長,書中代表人物是門巴喇嘛,他在傻子二少爺被陽光下的白雪曬傷時,對其進行治療,又在麥其土司與汪波土司的罌粟花斗爭中,用法術給汪波土司下了一場冰雹。
宗教的世界觀、人生觀,在小說中得到了展現。小說中共有八首歌謠,這些歌謠在作品中發揮著塑造人物、抒發情感、表達故事主題,推動情節的發展等功能。如小說在講述麥其家的來歷時寫到:“……經堂里有畫。那些畫告訴所有的麥其,我們家是從風與大鵬鳥的巨卵中來的。……最后一下說‘哈的結果是從大鵬鳥產在天邊的巨卵里‘哈出了九個土司。”這種卵生世界,卵生萬物的觀點,正是苯教關于宇宙起源的基本觀點。藏族說唱經文《馬和耗牛的故事》中,“國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徹底碎了”的歌謠在小說中出現了兩次,就像是預言一樣預示著土司制度的滅亡,家族的敗落和生命的消逝。
小說在敘事上也利用了佛教的宗教觀念。佛教講究因果報應,生死輪回,貫穿整本書的復仇情節,就是輪回宿命和因果報應的體現。麥其土司為了得到查查頭人美貌的妻子央宗,派多吉次仁殺掉了他,但麥其土司隨后就把多吉次仁殺掉滅口了。多吉次仁的兩個兒子帶著對麥其土司的仇恨,子報父仇,殺掉了麥其土司的大兒子和二少爺,麥其家崩塌了。
(三)等級森嚴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中人被劃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套特殊的以“骨頭”為名的身份制。土司是藏地的王,他們為所欲為,眼中只有家族利益和自我欲望,為了達到欲望,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甚至性命。麥其土司為了得到美麗的央宗,先后害死了幾條人命,最后對央宗始亂終棄,把她帶回土司官寨后不聞不問,央宗剛出世的孩子夭折而死,從此生活在無邊的黑暗之中,土司制度對人性的滅絕程度可見一斑。土司制度下的人們不僅在生活中過得不自由,在精神上也被束縛著。由于政教合一的特殊制度,宣揚轉世輪回,人們的思想長時期處于麻木的狀態,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中來排遣現實生活中的苦悶和不幸,生理和心理都淪為土司家族的工具。土司制度這種缺乏對百姓關愛、呵護的專制殘暴制度,在風云際會的年代,勢必走向坍塌滅亡之路。
以上從作品的民族、宗教、政治制度方面體現的地域特色進行了分析,展現了阿來在以藏文化為小說背景的創作中所體現出的獨特性。阿來的過人之處絕不僅僅在于藏地特色文化的描寫,而在于以地域獨特性為依托,融合了作家的自我體驗,個人色彩強烈的記憶。同時,阿來的創作絕不囿于狹窄的民族視閾,而是對權力、人性、命運等人類共同的主題進行了深刻的思索,從這個角度看,阿來的創作真正貼近了文學的根本。
二、地域文化書寫中的獨特之處
(一)寬廣的歷史觀、世界觀
阿來的小說作品,雖都將藏族地域以及藏族人民作為主要背景和主要人物,但所體現的歷史、世界觀卻絕不限于藏地世界。《塵埃落定》選取藏絨地區麥其土司家族的消亡歷史為線索,描述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土司制度在新時代到來之時的脆弱和崩潰。如果從事物發展的觀點看,土司制度的滅亡是有歷史必然性的。作為一位藏族作家,阿來在敘述土司制度消亡過程中,或多或少唱出了一支嘆惋之歌。但即使在這逝去的歷史早已在自己的血脈中留下了烙印的情況下,阿來在情感上始終保持了理性的克制。小說《塵埃落定》這一題目,預示著土司們的命運,大地是由塵埃構成,塵埃飛揚與塵埃落定,在于大地上人類的活動所致,但是無論塵埃是怎樣飛揚,最后的結局都是要落入大地之上。阿來的著眼點從一個單一的民族,從一個單一的地域,上升到了人類文明的高度上,向讀者展示了自己對于整個世界運行奧秘的思索。
(二)包容的民族觀、宗教觀
阿來表示:“有很多的學科在研究此地與彼地,此種文化與彼種化的不同,但是,我認為,一個小說家卻應該致力于尋找人類最大限度的共同點。歷史的必然與偶然決定了不同國度的不同命運與不同的發展水平,文化基因的差異造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面貌,但人類和人,最根本的目的,難道不是一樣嗎?”[4]
在宗教問題上,阿來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對宗教采取了尊敬,但并不盲從的態度。《塵埃落定》中,雖然宗教觀念深入藏民心中,但在小說中,面對麥其土司家強大的權勢,宗教卻成為了政治的附屬品。藏傳佛教和苯教的力量時而你強我弱,時而你弱我強,這都取決于麥其土司的態度。濟嘎活佛和門巴喇嘛為了爭奪麥其土司的信任,進行了多次明爭暗斗。只有翁波意西,嚴格按照格魯派的規則處事,是個真正的傳教者。在面對麥其土司時,他不卑不亢,敢說真話。阿來深知宗教并不是傳教者口中解決一切苦痛的方式,宗教對阿來創作的意義,是增加文學的力量,而不是決定文學的力量。
(三)悲憫的人生觀
嘉絨大地上的藏民很大程度上沉浸在那種亙古不變、寧靜而樸實無華時間中。阿來的小說中,日子成為一個能指,用以隱喻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時間好像停滯,生活永無改變,藏民們所有的歡樂,所有的憂愁,他們的愛和恨,都在這日復一日的重復中慢慢消隱。當這種雖閉塞但寧靜的、樸素的生活在內外勢力的夾擊之下灰飛煙滅的時候,悲涼感油然而生。小說中,無論是地位高貴的土司家族,還是地位卑微的百姓、奴隸,都在阿來的筆下呈現出作為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的渺小一面。《塵埃落定》從二少爺這個傻子的視角去展開,并把他作為一個主導的人物、主導的敘述,這種敘述有一種綿延而去的隨性而自然的力量。二少爺每次睡覺醒來,都要發問自己“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生動地體現了他人格中的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感,同時也體現了作家思想上在歷史長河中的求索。
阿來的作品以淳樸的敘事、蒼潤的文風征服了主流文壇,“我認為文學還是應該有向善、向美的力量,中國文學越來越拘泥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而且我們也別喜歡揣摩人的陰暗面,我們往往把這些丑的東西寫得入木三分,但我們寫不好那種好的東西。”[5]希望阿來繼續以他獨特的地域文化為背景,為當代文壇呈現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
注釋:
[1][2]阿來:《塵埃落定》,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
[3]阿來:《民問文學的表達資源》,民族文學研究,2000年第3期.
[4]阿來:《看見》,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
[5]阿來,陳曉明:《阿來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參考文獻:
[1]《阿來研究》(第五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2]黃山:《阿來作品風格成因研究》,中南民族大學,2015年5月.
[3]劉倩:《論藏文化語境中阿來的小說創作》,山東師范大學,2013年6月.
[4]魏聰:《藏文化與阿來小說創作》,重慶師范大學,2015年5月.
[5]何奕霖:《阿來小說中的西藏地域文化書寫》,《文學評論》,2011年10月.
[6]樊義紅:《阿來的民族文學觀》,《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