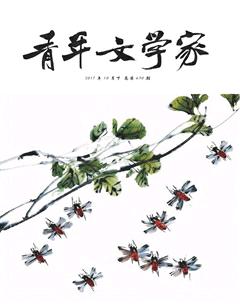論90年代的“陜軍東征”現象及其意義
摘 要:“陜軍東征”是發生在九十年代中國文壇上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沉寂的陜西作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接連推出了幾部達到相當藝術水平的長篇小說作品。本文就以“三駕馬車”(即高建群《最后一個匈奴》、陳忠實《白鹿原》和賈平凹《廢都》)為例,對這一文學現象及其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進行簡要分析。
關鍵詞:地域化;傳統;個體體驗;人物形象;長篇小說
作者簡介:張寧(1991-),女,遼寧莊河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30-0-02
“陜軍東征”是發生在九十年代中國文壇上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學現象,繼1992年陜西文壇相繼失去杜鵬程、路遙和鄒志安三位優秀作家而陷入創作上的低潮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忽然涌現出一批達到了相當藝術水平的長篇小說作品,評論界用“井噴”來形容這些作品的出現,并且從這一年開始,陜西作家以其創作,對中國文壇尤其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地域化的寫作特色和傳統化的創作方法
縱觀當代文壇,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以后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故鄉為故事背景。例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劉震云的“河南延津”甚至余華的“我們劉鎮”。在這一點上,陜西文壇的作家們也表現出了對故鄉的依賴與熱愛,“東征”的“三駕馬車”中,《最后一個匈奴》的故事主體始終沒有離開“膚施城”,而在《廢都》和《白鹿原》中,“西京城”和“白鹿原上”也承載了全書的主要內容。作家們把故鄉作為敘述的基點,站在他們熟悉的這片土地上講述一個宏大的故事,并且在書中處處流露出對故鄉深深的熱愛與向往。尤其在《最后一個匈奴》和《白鹿原》中,作家多次通過行走在山野之間的人物角色如楊作新、朱先生等人的感官,細致并充滿熱情地向讀者展現了關中平原的自然風貌和人文景觀。此外,在敘述語言和人物的口語中,陜西方言也是層出不窮。在白嘉軒、莊之蝶、楊作新的口中,讀者們聽到了一個又一個陌生而帶著陜北高原上黃土氣息的全新詞匯,尤其在《最后一個匈奴》中,作家更是幾乎前無古人地大量收錄了陜北的地方民歌“信天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東征”使得關中地區真正進入到廣大讀者的視野之中,成為當代文學一個不可忽視的素材。
而對傳統文化和敘事手法的繼承也是這一時期陜西作家在創作上共有的特點。在“三駕馬車”中,《最后一個匈奴》和《白鹿原》被評論界冠以“史詩”的稱號,在書中對風俗、文化、傳說等等一切“傳統”的體現俯拾皆是,而作為賈平凹第一部以城市生活為內容的長篇小說,《廢都》卻顯然借鑒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方法,并且在內容及思想意義上也與古典小說《金瓶梅》暗合[1]。這不能不說是陜西作家在創作上對傳統的完美繼承。而我們在書中隨處可見的人們對故土的依戀,對城市文明的畏懼和排斥,又與20年代鄉土文學中體現出的戀鄉戀土情結構成了藝術手法上的繼承關系。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陜西作家在20年代鄉土文學的基礎上又有所開拓,他們不再否定近代化、城市化給鄉土中國帶來的積極影響,順應歷史潮流,又充分刻畫了人物復雜的性格與內心世界,表現出生活“側面的本真”[2],這正是“東征”作品在藝術上體現出的鮮明特征。
二、個體體驗的關注與鮮活形象的塑造
相較于建國以來四十年間產生的許多文學作品,這一時期的陜西作家們在創作中似乎更加樂于把著眼點放在對個體生活體驗的真實反映上。不同于以往作品偏重于對故事的敘述和情節的渲染,“東征”作品對人物的內心世界加以更多的關注,例如在《白鹿原》中,作家用大篇幅的文字來描寫白嘉軒、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復雜心理活動,而這一特征在《廢都》中莊之蝶與唐宛兒、柳月等人的糾纏中表現得更為直接。同樣地,在《最后一個匈奴》的下部中,對丹華、黑壽山、楊岸鄉的心理刻畫也同樣能夠體現出人物的復雜心情和艱難的思想斗爭。可以說,對個體生存發展的近距離觀察和刻畫,是這一時期陜西作家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創作方法突破了過去把“現實”觀念化、意識形態化,要求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自己的人生體驗而不得不遵從“現實”的創作模式[3],更多從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去觀照,這是對長篇小說創作方法上進行的一次偉大的洗禮。
真實反映了個體生活體驗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塑造出一群血肉飽滿、性格復雜的人物形象。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尤其是“十七年文學”時期,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黑即白,這種簡單粗暴的價值判斷標準顯然已經不能符合新時期讀者的心理預期,也不能適應文壇對于優秀作品的要求。因而,“東征”作品中的人物,總是帶有鮮明而又復雜的特征,很難有一個標準來對他們的善惡是非進行判斷。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和鹿子霖,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善一惡,一正一邪,然而白嘉軒——乃至于被視為“圣人”的朱先生也未嘗沒有過欺壓田小娥冤魂的行為,相反,鹿子霖對孫子的照顧則處處體現出一位祖父的慈愛之心。同樣地,《廢都》中的莊之蝶在人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他對周敏等年輕人的提拔和優待也體現出長者的溫厚。至于《最后一個匈奴》中的楊作新,他與好友之妻黑白氏的偷情行為、他休掉發妻燈草的“負心”之舉,我們也很難說這是一個完美的正面人物應有的行徑。筆者認為,優秀的作品中從來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和“壞人”,而只有,也只能有一個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陜西文壇的崛起與長篇小說的興盛
通過“東征”,原本漸趨灰暗的陜西文壇得以重振,而更為重要的意義則在于,陜西作家從此開始正式以光榮的姿態進入到中國文學評論界的視野中,并迅速成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東征”的“三駕馬車”中,《白鹿原》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而《廢都》的作者賈平凹也以另一部長篇小說《秦腔》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加上此前已獲茅獎的已故作家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陜西作家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而此次“東征”在實際上是一件必然要發生的事,陜西文壇在靜默的發展中最終成熟,并借由九十年代文化與市場相結合的重要契機走進了廣大讀者的視野中。這對陜西文壇是一個極大的喜訊,更為重要的是,對那些依然潛藏在民間進行文學創作的青年給予了重要的鼓勵和支持。可以說,作為當代文壇上再也不能被“復制”的文學現象,發生在90年代初的“陜軍東征”無異于一陣西風,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陜西作家的成功同時也刺激到了其他省市的作家,這一刺激的最終結果,就是文學界迅速衍生出相當一部分優秀的長篇小說作品。從茅盾文學獎的獲獎名單上來看,前三屆的獲獎作品如今讀來在文筆上、內容上都稍顯稚嫩,并沒有體現出大氣和成熟。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則無一例外地或以其敘事之宏大,或以其表現手法之獨特,或以其思想內涵之深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回味。這些也許都得益于陜西作家這一次“東征”的刺激。因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將純文學從精英階層的小圈子里釋放出來,走向了普通大眾。從而使這種大眾文化生產方式在中國成為可能。盡管法蘭克福學派所批評的大眾文化的平面化、膚淺化、庸俗化問題隨之而來[4],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學不再高高在上,而真正地成為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這些都是“陜軍東征”帶給中國文壇的深遠影響。
發生在90年代初的“陜軍東征”現象,以其自身獨特的藝術特征和新穎卻又不乏對傳統的繼承的創作手法,將長期以來未受關注的陜西文壇推向了廣大的讀者。陜西作家所進行的對個體體驗的真實表現,也為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線。同時,在陜西作家崛起的刺激下,中國文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極大地豐富了這一時期長篇小說的創作。總而言之,“陜軍東征”也許難免有它所引發的消極一面,但總整體上看,這一文學現象對中國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
[2]高建群《最后一個匈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3]賈平凹《廢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4]白燁《作為文學、文化現象的“陜軍東征”》,《小說評論》1994年第4期。
[5]黃洪旺《論“陜軍東征”的藝術特征與追求》,《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8年第4期。
[6]王鵬程《一件拙劣的仿制古董》,《名作欣賞》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