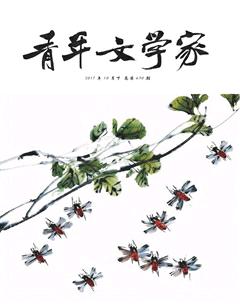納須彌于芥子,藏文化于方寸
摘 要:臺(tái)北故宮博物館里一枚陳祖章所刻的橄欖核舟,成為了本文的由頭。核雕名人王叔遠(yuǎn)的桃核舟、核雕藝術(shù)的社會(huì)地位、形成的時(shí)間特征以及空間特征都是本文的討論重點(diǎn)。
關(guān)鍵詞:核雕;陳祖章;王叔遠(yuǎn)
作者簡(jiǎn)介:劉玥琳(1993-),女,漢,重慶市人,上海大學(xué)上海電影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理論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shù)學(xué)理論。
[中圖分類號(hào)]:J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7)-30--01
根據(jù)臺(tái)北故宮博物館的官方資料,陳祖章所刻的橄欖核舟“長(zhǎng)1.4公分,橫3.4公分,高1.6公分”,“來(lái)自廣東,於雍正時(shí)期已進(jìn)入造辦處的陳祖章,在乾隆二年(1737),依照橄欖核天然的外形,將一個(gè)果核雕琢成一艘小船,船上乘載八人,每一位人物的動(dòng)態(tài)、表情各有不同。最特別的是,船底刻蘇軾的〈後赤壁賦〉全文,三百餘字,細(xì)密井然,堪稱鬼斧神工”。
陳祖章吸取清代以前的經(jīng)驗(yàn),不僅提高了技藝,還發(fā)展了內(nèi)涵。舟上有花窗四扇,精妙在于每扇還可以自由開關(guān)。除此之外,靜物的刻畫也十分到位,艙篷上雕有紋路,桅桿、帆、繩索一樣不差,船艙的桌上杯盤狼藉。人物刻畫神情各異。由此,技藝的精致細(xì)膩可見一斑,而難能可貴的是,陳祖章還力求創(chuàng)造出一種詩(shī)的意境,舟中人物的神情、動(dòng)作都能恰當(dāng)?shù)伢w現(xiàn)其身份、性情和心境。至于該核舟的底部,則刻有《后赤壁賦》全篇,以及“乾隆丁巳五月臣陳祖章制”款。這三百余字以楷體而鐫,端莊挺秀,細(xì)密井然,更是增加了作品的藝術(shù)品味。
而魏學(xué)洢《核舟記》里描寫的桃核舟為王叔遠(yuǎn)于1622年(天啟壬戌年)所刻、所贈(zèng),此舟的巧妙構(gòu)思是圍繞蘇東坡與友人月夜泛舟有赤壁展開的。根據(jù)《核舟記》所述,三個(gè)人的動(dòng)作、姿態(tài)、神情都被王叔遠(yuǎn)細(xì)致而生動(dòng)地呈現(xiàn)出來(lái)了。就連佛印手中的念珠都“歷歷可數(shù)”,足見其精細(xì)高超的技藝。
在1994年之前,人們只知道我國(guó)古代核雕實(shí)物是收藏于臺(tái)北故宮博物館的那枚陳祖章橄欖核舟。但1994年,寧波鎮(zhèn)海的一位老人在家中清理祖?zhèn)鬟z物時(shí),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枚桃核舟。經(jīng)過(guò)鑒定后,這一桃核舟被確認(rèn)為是王叔遠(yuǎn)在入清易名"叔明"后所刻的作品。因此,這枚核舟擊敗陳祖章的橄欖核舟,成功“上位”為《核舟記》的參考物。然而,現(xiàn)身寧波的這個(gè)桃核舟雖然在大小、雕刻人物、場(chǎng)景等都與魏學(xué)洢所持核舟基本吻合,不過(guò)卻并非原物。因?yàn)樵诖褚粋?cè)有一“明”字標(biāo)記,這是王叔遠(yuǎn)晚年所改的字。而且,不同于贈(zèng)與魏學(xué)洢的核舟在窗上刻“清風(fēng)徐來(lái),水波不興”、“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這新發(fā)現(xiàn)的核舟上,王叔遠(yuǎn)以“佛印侍弄盛開的菊花”的意象直接形象地暗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時(shí)間設(shè)定,也更好地呼應(yīng)了《赤壁賦》所蘊(yùn)含的人淡如菊,恬淡隱忍之意。這一點(diǎn)題方式凸顯出了他的匠心獨(dú)運(yùn)和作品所包含的藝術(shù)品位。自古以來(lái)民間一直把桃木奉為祛邪扶正,避兇趨吉的象征物。所以桃核舟的產(chǎn)量極其少,于是它便被列為宮廷藝術(shù)了。
古人對(duì)于核雕品的喜愛也有據(jù)可查,不僅上至九五之尊,蘇州杜士元所做桃核舟,在清乾時(shí)期已揚(yáng)名宮廷,“高宗(乾隆)聞其名,三召至啟祥宮”。上海嘉定的封錫祿也因善刻桃核舟被召為養(yǎng)心殿刻工[1]。就連修繕核舟,達(dá)官顯貴如江南巡撫宋公家也不惜重金聘請(qǐng)能人[2]。下至平民百姓,“雖以千金不能致(得到)也” [3]。2008年,這一手工藝術(shù)被列入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根據(jù)已有資料,最早記載在冊(cè)的核雕工匠是夏白眼。我們基本認(rèn)定核雕藝術(shù)始于明代。這和明代中晚期社會(huì)思潮的變遷密切相關(guān)的。彼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商人們“同欲而共趨之,如眾流赴壑,來(lái)往相續(xù),日夜不休,不至于橫溢泛濫,寧有止息……窮日夜之力,以逐錙銖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4],于是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由于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對(duì)外開放、西學(xué)傳入以及一批思想家出現(xiàn),思想禁錮也有所松動(dò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還引起人們社會(huì)心理、價(jià)值觀念的變化,人們開始追求塵世利益和現(xiàn)世人生。一些知識(shí)分子開始把注意力投入到了工藝美術(shù)領(lǐng)域,推崇高超的技巧,核雕藝術(shù)應(yīng)運(yùn)而生。
至于清代,宮廷里造辦處的細(xì)化分工,對(duì)工藝藝術(shù)的發(fā)展與繁榮起到了很大的推動(dòng)作用。而民間的流行,也直接影響到宮廷,因?yàn)樵燹k處的工匠都是來(lái)自于民間的藝術(shù)家。所以核雕工藝長(zhǎng)盛不衰,逐漸成為宮廷秘藏。
除了在形成時(shí)間上的特殊性,核雕藝術(shù)在空間上也呈現(xiàn)了對(duì)應(yīng)時(shí)間的特點(diǎn)。上文列舉的明清兩代著名核雕工匠幾乎都是江南人,正如高士奇所言“吳人以橄欖核為船,諸物俱備,且極工巧”[5]。一方面,這必然與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qū)的作坊里出現(xiàn)了雇傭關(guān)系,于是資本主義萌芽有關(guān)系。另外一方面,由于歷史與文化的積淀,江南人形成了靈秀穎慧的氣性,而這與核雕藝術(shù)要求的精雕細(xì)刻恰好契合。
雖然核雕的用材都是人們食用之物的廢核,然而核雕工匠們秉持著“天地間無(wú)棄物”[6]的原則,使這些果核煥發(fā)出新的生機(jī)。他們?cè)谶@方寸之物上雕出了詩(shī)情畫意的文境,不僅需要觀賞者用眼睛去捕捉,更要他們動(dòng)用自己的文學(xué)素養(yǎng)去體悟。
注釋:
[1]鄭建軍.《核舟記》與明代核桃舟.浙江工藝美術(shù). 2001年.
[2]紐琇.《觚剩桃核舫》.清.
[3]錢泳.《履園叢話.杜士元核雕》.清.
[4]張瀚.《松窗夢(mèng)語(yǔ)》卷四《商賈紀(jì)》.明.
[5]高士奇.《苑西集》卷四《欖核船》詩(shī)序.清.
[6]陸容.《阿留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