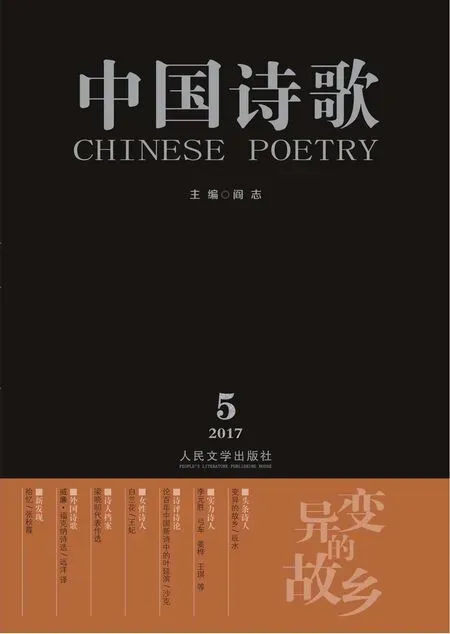變異的故鄉(xiāng)·組詩·
□辰水
變異的故鄉(xiāng)·組詩·
□辰水
變異的故鄉(xiāng)
1
風吹過城鎮(zhèn),也吹過田野。那時間的風
它像一匹脫韁的馬,
拉著一個又一個的村莊,奔馳……
在顛簸之中,它們變形,也變異
被折疊,也被扭曲。
一只光怪陸離的怪獸,
它在深夜跑出來,驚動數(shù)個村里的居民。
然而,他們誰也無法抓住
這只變幻的精靈。它是欲望,從人們的內(nèi)心里
跑出來——
在黑暗中,它身上的鬃毛,閃閃發(fā)亮。
夜晚。風吹過它
如同一只獅子的孤獨。
2
流過村鎮(zhèn)的河流,它再次被摻入工業(yè)的廢渣。
虛假的河水,
投射在它上面的倒影,也變得張牙舞爪。
一個流域的積怨,全被拋棄在里面
即便是再大的風雨也無法化解。
一個投河自盡的婦女,她的死因有若干個版本
但她肯定不是一個外星人。
當河流在一夜干涸之后,
淘金的異鄉(xiāng)人揚起的沙塵,遮蔽了半個村莊。
閃光的金子,
它的每一個棱面,都足以照亮
一個人逼仄的內(nèi)心。
3
更多的青山,被螞蟻搬走
卡車一樣大的螞蟻,它們瘋狂地吃掉一座座山頭。
在力量面前,連巨石也不得不
聽從于機械的命令。
在滿目瘡痍的山區(qū),那飛來的巨大深坑
像是宇宙的秘密符號。
作為故鄉(xiāng)人,我驚愕,并無法直視
無法追問,到底是誰
偷走了多少黑色的石頭?
——這些土中的鐵,大地的骨殖。
4
當雷聲從村落的上空滾過,
沐浴在雨水中的莊稼,再次復活,成為不同的父親。
一個歉收的田野,土地被分割成
不同的形狀,張望著天空。
鐮刀從空中掉下來,
收割茅草,也割刈看不見的電波。
從大地的深處,被挖掘出的遺骸
早已無人祭祀,
車輪碾壓之后,又重新融入土中。
而饑餓卻并不遙遠,
我像一只帶電的老鼠,貯藏著人間的糧食。
5
機器也取走了我體內(nèi)的骨骼,
那些泥土做的骨骼,有著農(nóng)業(yè)的氣息。
雨水從天空墜落,
可大地上早已沒有了一塊稻田。
一個期盼豐收的國度,卻注定要兩手空空。
在工業(yè)時代,大米和雞蛋
足以以假亂真。
那些流水線上的產(chǎn)品,再一次
讓貧瘠的胃,穿過黑暗的玻璃。
6
在星星失蹤之后,人們又重新裝飾了天空。
亙古的星宿,
它們在霓虹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旱之年,連天上的銀河
也接近干枯,
而人間一個火星的愿望,又怎么會輕易兌現(xiàn)?
死后的祖先,他們仿佛是藏匿的星星。
光從墓穴中發(fā)出,
那照亮我們彼此面容的光線,
是螢火,還是燭光?
時代的發(fā)電機,高速旋轉(zhuǎn)。
一個黑如白晝的故鄉(xiāng),鬼魅叢生。
7
拆遷后的廢墟,成了慶功的舞臺。
在紅地毯走過的地方,
澆筑上了黑色的瀝青。
傍晚,我一個人穿越廣場。表演者都長著
一張張夸張、修飾過的面孔。
我是沉默者。也是逃離者。
歡樂屬于眾人喧嘩的夜晚,孤獨卻如
清冷的燈盞。
在擁擠的人群深處,
復合的欲望像發(fā)臭了的鮑魚。我抽身而去
卻最終還要撞上一面游動的懸崖,
令自己靜止不動。
8
面對故鄉(xiāng)的問詢,
我們早已習慣彼此來虛構(gòu)自己的行蹤。
一個不斷修改著門牌號的人,
怎么能熱愛異鄉(xiāng)的山水?
在最低的草叢里,也藏有颶風一樣旋轉(zhuǎn)的夢想。
整個村莊的人,被簡化成編碼
藏進公文夾里。
他們沉睡,卻不知何時蘇醒。
而在田地里勞作的肉體,并非真實。
他們的體液成了地球的一部分,
卻無法進入紙上的故鄉(xiāng)。
9
書架之上,每一本書就是一個故鄉(xiāng)。
活動的冊頁,猶如奔跑的建筑
在鄉(xiāng)間積聚幽靈。
一個被挖掘機輕輕舉起的村莊,它砍斷的根須
已無法復活。
一截故鄉(xiāng)的臍帶,被輕易截斷。
那些注定無法返鄉(xiāng)的人,在異鄉(xiāng)埋下胎盤。
黃昏之后,我試著返回故鄉(xiāng)
可每一個故鄉(xiāng)都變得面目全非,越來越像是另一個異鄉(xiāng)。
破繭而出的蝴蝶,
它感受到了颶風的力量。
繭衣似的故鄉(xiāng),早已破碎。蝴蝶的子民,注定要尋找
另一片迭變的山谷。
一個村莊的四則運算
加法:繁衍
也許一個姓氏就是一個物種
那從明朝遷徙而來的李氏,便是從異鄉(xiāng)飛來
繁衍的一種蝴蝶。
永樂年間,一只僥幸逃脫厄運的菜青蟲
它夢見了未來的光榮。
六百年后,它將成為祖先被供奉在祠堂。
這無限的繁殖力,
比所有的戕害更偉大百倍!
它們統(tǒng)治這個世界,卻依然無法抵御天災(zāi)。
1960年,三十多歲的奶奶停經(jīng)了
饑餓讓繁衍暫時擱淺。
可當天降甘霖之后,
一個村莊的生殖力,像河水一樣暴漲。
我的降生,為逝去的祖先填補
一個嘈雜的靈魂。
中年病歿的書生魂魄,他在我的肉體上
成長為另一個自己。
我既是古代的,也是現(xiàn)代的
既是祖先,也是子孫
減法:遷徙
擇水而居的祖先,改變了一條河流的走向
從東南修訂為西南。
而一條河流,竟然也會在一夜之間
不明不白地消失……
難道,一條河流也會遷徙?
被迫遠走他鄉(xiāng)的人,帶走妻兒和取水的器皿。
他們相信地下藏著另一條奔跑的河流,
干凈、清澈,帶著微微的咸
像蓄在眼眶里的一滴淚水。
一個氏族,只剩下老人堅守著的村莊
如此安靜,如此肅穆。
而遷徙者的背景,是忙碌、無助、忐忑不安……
他們是民工、商販、貨車司機……
她們是保姆、導購、站街女、守夜人……
我終于成了他們中的一個。
村莊減少了我,我也把大片的土地扔在身后
把成熟的莊稼留給了長夜。
那些將我喂大的麥粒,
它在城市以另一種膨脹的方式來安慰我。
我成了被減少的單數(shù),
我可以被忽略,也可以被一個村莊遺忘。
乘法:爆炸
虛構(gòu)一個紙上的村莊,
需要調(diào)動三千多個漢字,甚至更多。
而爆炸是另一種虛構(gòu),
它讓一個村莊,天外飛來。
村莊以膨脹的方式完成自己,像一粒爆米花。
如果給予它熱鬧的溫度,
它還將,無限大。
從一座消失的山中爆炸而出的高樓,
它讓石頭以另一種方式矗立。
而我心中的那顆星,早已無法看見
它以一只白熾燈的形象來代替。
一百年后,我想象一個膨脹后的村莊
它會不會像一枚氣球,
面臨被爆破的命運。
在那“嘭”的一聲巨響之后,
我們是否還能找到滿地的碎屑。
我是最小的碎屑,
我將回到世界本初的樣子。
除法:消亡
一個村莊的影像,都被貯存在瞳孔里
成為晶體的一部分。
擦亮眼睛,看到村莊蕭條的影子
像一條孤獨的蛇。
那走著走著就消失的人,那站著站著就不見了蹤影的樹木……
那眾鳥已飛走的村莊,
它在一張地圖上也將丟失自己名字
成為新版圖上的棄兒。
越過一個朝代,它也將被自己的子孫遺忘
在一本縣志的夾頁之中。
好事者,似乎企圖能從泛黃的紙里
尋找到先祖驕傲的遺骨。
我也將屈服于這消亡的命運,
為一個村莊獻上自己的祭祀。
這微不足道的肉體,
——它那么小,那么輕!
我是死者,也是生者
我是歸來者,也是朝圣的人
伐木丁丁
下午,三點。
我又遇見了那個伐木人,和那閃亮的鋸子。
一個偶爾的鐘點工,
他對樹木有著天然的敵意。
一棵棵倒地的樹,它們的亡靈
早已游離于大地之外。
古老的秋天,再一次被演繹成頭顱落地,
或者是在手機上清掃一遍堆積的落葉。
一聲聲刺耳的尖叫,
似乎代替了古老的伐木之聲,
詩意戛然而止。
然而,他砍伐的并不是一片森林。
只是河堤邊的楊樹,一行速生的舶來品種。
幾個操著南方口音的異鄉(xiāng)人,
他們?yōu)檗Z然倒地的軀干買單。
一切生活的秩序,
并不因此而改變,或節(jié)外生枝。
河水依舊南流,
搬運木材的卡車交換著發(fā)酵的紙漿。
而我距離這一切并不遙遠,
在日益凋敝的鄉(xiāng)村,
我不停地砍伐自己的叢林,在一張紙上。
每一行字,都幾乎傾倒
都幾乎被連根拔出——
象形文字
1
在教授兒子寫字的時候,我恍惚
要變回三十年前的父親
過去的光從宣紙的背面,投射出來
照亮了房間
想起在一面墻的正面,父親把笨拙的字
寫在上頭
或者說是畫,一筆一畫
每一個字都好像是——
一位遠道而來的親戚,它們串門
并因此而碰壁
只上過半個學期小學的父親
他守候的字
還不到二十個,無法占滿整面墻壁
剩下大片空白之處
土墻的對面,睡著我的臉
那是一面芳香的墻
泥土由生變熟,直到
可以充饑
2
許多的字變成餅干模樣
變成動物的模樣
讓我們吃,讓我們吃……
直到最后,剩下了毛發(fā)
剩下了紙做的四肢
它們一個個分別在地上爬,慢慢地爬
分離是痛苦的——
而驅(qū)趕走一個字的偏旁和部首
像把大陸的一部分撕裂成海島
3
而更多的象形文字落在了地上
成了一棵青草
它最終的去處,像一股火焰
跑進了大地的深處
父親挑著一擔的象形文字
走向田野
夜色已深,它還沒有回來
每一個字都像是一座小小的墳塋
無規(guī)則地分布
我懷念一個可怕的死者
那,肯定是一個真理
4
逃跑,是一個虛張的借口
為了避開我們
父親把字一個個地從墻上抹掉,直到
只剩下雪白的墻
那孤零零的美,需要我們重新冷峻地面對
像信仰上帝
一年之后,我將會看到
許多的象形文字像蜥蜴,往墻上爬
那留下的痕跡
我認為是殘忍的,也是美的……
像漢字教會了直面生活,而作文卻讓我
迂回曲折,隱約中
看到了遠方的點點星火
另一個政府
我很難相信
在一個縣政府的樓下,還藏著
另一政府。
一個螻蟻的政府,它也有
十八層那么高。
但我在疏通管道的時候,
竟然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切。
在蟻穴的深處,
也藏有一把縣長的椅子。
即使是一紙過期的任命,
也會被咬成濾網(wǎng),
用來篩選天生的蟻卵。
突如其來的水流,
竟也能遣散一個非法的政府?
管理員是孤獨的,
他不斷操縱著流水,時斷時續(xù)。
瀕臨滅絕的王國,
水災(zāi)叢生。
我相信它的潰敗源于偶然,
而更多的政府,人去樓空。
用麥穗加冕
在鄉(xiāng)間,詩人給自己加冕。
統(tǒng)治的區(qū)域只有六百多個平方,僅有
一千零一條害蟲和逃竄到此的
三只螞蚱。
沒有一個可依仗的重臣,
沒有一只益蟲來替我消滅敵人。
我用一捧麥穗置于頭頂,
自己便成了孤王。
一個國家的律條,我既是制定者
也是遵守者;
對于草菅蟲命,只有自己審判自己。
如果轟隆的收割機碾過,
我的帝國瞬間崩坍了,
成了偏居一隅的皇帝。
只關(guān)心詩句,
不熱愛糧食。
秋日的暴政
秋日里,自己給自己施政。
孤獨就會發(fā)育成果實。垂下梢頭的瞬間,
所有的谷穗都為一只受傷的麻雀讓路。
應(yīng)該交還的銀兩,還在途中。
對一個思考者,征收其內(nèi)心里的田賦,僅僅只是為了
得到一張潦草的稿紙?
為了推翻自己的統(tǒng)治。
我在這秋天的日歷卡上,埋藏下火焰。
那燃燒的部分,不僅僅是紙……
我們埋葬下閃電
除了閃電,我們還有什么無法埋葬。
一個人就是一道閃電,他奔跑時,閃電也在跑。
昨夜的雨,直到今天還沒有滴完,
收藏它們的容器滿了,溢出的水變成了污垢。
沒有種植者,許多的木耳也會暗暗出生,
可是依然還無法稱量一根朽木的重量。
我躲在明亮的玻璃后面,閃電朝我襲來……
卻怎么也無法擊中我。
火焰
從遙遠的假期里退出來
我?guī)缀跸窨缟弦黄サ雇说鸟R,一直退回到
剛剛開始手淫的日子
那時,我多么像匹純種的馬
被驕傲地困在莊園里
在一匹馬的羞恥部位,里面似乎
埋下了許多火焰的種子
發(fā)芽的恐慌肯定纏住了我
我開始擔心,它會長大
甚至會噴射出火焰
多年以后,我也學會了鉆木取火的技藝
從肉體里取出的火
會燒燙一個隔夜的尿壺
沸騰之后
那些被冷卻的部分,始終還是
一副冰冷的骨架
而火焰也會彎曲
遇見巖石也一樣會逃進縫隙
在堅硬的花崗石內(nèi)部
一朵火焰的化石
它的里面往往藏住了一顆憂憤的心
六月的分行詩
總算是度過了屬于自己生日的五月
那是一個驚險的日子
如胚芽幾乎要接受太陽炙熱的烘烤,那烘烤
也是帶電的
可是只有閃電才屬于每一個貧窮的人
才可以平均地分享它的光亮
在雷霆的深處,它似乎總掩藏著什么
如同這小小的村落
蜘蛛網(wǎng)似的小巷里,布局
自己的童年
我們在草堂里相遇,與另一個杜甫
擦肩而過
貧寒像冬日的蚊蠅,堅守著一寸
溫暖的陽光。可現(xiàn)在是夏日
暴雨隨時將至
在暴漲的河流對岸,我們相互
張望。凝視……
剛剛過去的五月,猶如水面上的稻草
被輕輕地馱走——
蝸牛火車
再也沒有比這列火車更小的火車了
它在墻角下最潮濕的地方建設(shè)著軌道、車站、月臺……
連候車室也是袖珍的
容得下打盹瞌睡的螞蟻和不醉不歸的蜜蜂
抱頭鼠竄的永遠是那些潮蟲,把傷殘的大腿
一截一截地留在了站臺上
這樣的火車就要啟程了
需要十八只蝸牛的力量
需要十八只蝸牛同時發(fā)動它們的馬達
讓這列火車的速度達到每小時8米
讓這列火車一生也跑不出一座村莊
如果換作我,把一個童年的我塞進這樣的一列火車
一直要坐到兩鬢斑白
還是到不了自己的墓地
還是看不到自己把自己燒成一捧灰
那樣是不是有些悲傷
可我寧愿讓自己慢些,慢下來
把自己藏身于蝸牛的殼里
不管世界怎樣旋轉(zhuǎn),不管殼外風雨陰晴
我就這樣一生寄居在一只蝸牛的殼里
等待著一列蝸牛火車載著我回家
另一盞馬燈
已經(jīng)熄滅了二十三年的馬燈,如同我的
另一個父親
無論怎樣,都無法點燃它
它的底部,有著五厘米長的裂縫。足可以泄露出
無限的煤油,和數(shù)不清的靈魂
而另一盞馬燈,卻早已沒有了去向
它曾經(jīng)照亮的房間,被拆了
燈光下的容顏,也不見了
甚至,黑夜里一閃而過的白薯片
也要鉆入土里
馬燈是鐵的,還帶著火焰
可要熄滅它,也僅僅只需要
一捧微不足道的黃土
孤獨如斯的馬燈,我敲打它
會抖落一地的碎屑
那里面的每一個微笑的顆粒,都如同舊時光
被摻進了鹽
在舌尖上都是咸的
一公里的森林
在長約一公里的森林里,我?guī)缀豕铝o援
對于自由散步的樹木
惟有用揭皮的方式來對抗它的憤怒
在俗世上,所有的樹木都有著戴罪之身
讓砍伐有了正當?shù)慕杩?/p>
我是河岸邊上的臣民,也是森林里
孤獨的信使
一公里之內(nèi),需要安置多少個驛站,才能
讓脫殼的夜蟬,升到高處
所有聚集在一起的蟬鳴
它們的合奏,怎么也無法抵擋滂沱的大雨
逃跑的蜘蛛
一只蜘蛛停住了腳步。我看見了它
而它并不一定發(fā)現(xiàn)了我
它從殘損的網(wǎng)上后撤,像敗軍之將
帶著驚恐和膽怯一路逃亡
可是逃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天涯與海角”
這兩所避難之處,足足可以讓它跑上幾個世紀
我害怕它會再次發(fā)動引擎
再次逃進地球的縫隙里,從美國的廢墟里鉆出來
于是,我使用了外力
捉住它,讓它再次吐絲結(jié)網(wǎng)
可它,呆呆地停在那里
一動也不動
整整一個下午,它還是不動
有好幾次,我懷疑它死了
用手撓撓它的爪子
卻依然還很牢固地抓在一張破網(wǎng)上
雪人
為了重新塑造另一個雪人
我把那個殘損的雪人——解肢
這是它的頭,那是它的腿……
哦,這些折了的胳膊,這些折了的腿
這些被擰歪了的鼻子
這些被安置倒了的嘴
——它們都要被再次嫁接
重新復活過來
在冬天,只有天空布滿陰霾
只有冷風吹徹我們的骨頭
才會有閃亮的雪花從天上落下來
才會有一個個的雪人降生在大地上
而我為了一個雪人的美
殘忍地殺死了另一個丑陋的雪人
帽子下的雪
從前,我們都曾經(jīng)戴著一頂相同的帽子
火車頭的帽子
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慌亂地跑——
以至于有些東西都丟掉了,也渾然不知
直到最后,連青春的褲衩也要露出孤獨的窟窿
那時,我們都很破舊
像一只只灰不溜秋的壇子
在等待著從空中落下來的雪,將我們覆蓋
把我們埋葬
未來我們都跑回了屋里
熱氣騰騰的我們把整個世界都融化了
可春風還是沒有吹來,還在山的另一邊
我低頭找到了那個遺落的帽子
在它的下面竟藏著一小堆還沒有來得及融化的雪
那捧小小的雪,晶瑩的雪
多么可憐
我決定捂住它們,懷揣著它們悄悄地消失在黑夜里
一個人走向遙遠的南極
中年之后
把僅剩的蘿卜埋藏于地下,像是把一束光
種植在黑暗里。
在冬日的鄉(xiāng)間,一個挖坑的人
始終在挖著深深的坑。
他用鐵鍬的桿部來測量深度,也是用身體
與地球的表層來和解。
中年之后,棲身的洞穴出現(xiàn)了裂縫。
抖落身上的塵埃,
讓我感受到了泥土的重量。
與一片廢墟交談,在里面居住的諸神,注定要
退避三舍。
在內(nèi)心里建筑的樓房,
難道不需要一張準建的證書?
政府,幾乎無處不在。
而,生活——
這巨大的泥石流,甚至會摧毀堅硬的詩行。
地圖上的河流,
并不會因我的走向而修改。
我一個人背對著大河而走,越走越遠……
直到與另一粒沙礫重逢。
過街馬戲
多年前的一場馬戲,
常常會在記憶里失真,成為一面鏡子。
那年的夏天,吹來異鄉(xiāng)的人
一群瘦小的表演者,
仿佛來自另一個國度。
陌生的瞳孔,比所有的獸眼
更為驚悚。
沒有人告訴我,他們?yōu)槭裁磿淼竭@里,
會帶來病懨懨的野獸。
來到鄉(xiāng)村的那只獅子,鉆火圈的那只獅子
不抽打它,
它就不表演的那只。
一個孩子,他內(nèi)心的兇惡幾乎
與生俱來。
戳痛一只困進籠中的獅子,
居然成了游戲。
現(xiàn)實中,一個再兇殘的人,
也會成為籠中的另一只獅子。
當圍觀者如同藥片被溶解,消失而去——
馬路上空蕩蕩的,
幾根獅子的毫毛,被風吹走
記憶里再一次恢復了原來的地貌。
冬日里的世道人心
冬日里,我們往往耗盡了太多的氧氣
把身體也費盡了
整整一年的儲備。明年春天氣短,來不及呼吸
自由就變成了滯留
把我們纏倒在地
即便是再公正的世道,也有人樂意
做個乞討的流浪者
也有人要暴露出自己的鼻孔
吸走一腔的霧霾
我們常常過分地理解了這個世界
孤獨有多少
熱愛就有多少
而對于一個俗人的愛,它關(guān)乎良心
也像冬日里湖邊的冷風
它直指那冰層以下的部分
那溫暖的水里
難道,非要浸泡下一顆畜生的心
挖一挖,箭鏃
幾枚箭鏃被拋離地下,遇見了光。
那是陌生的光,
追逐著一千年前的自己。或者是親吻一下
隔著十多個朝代的泥土。
田地里的白薯,接近豐收。
一個北方的祖國,
帶不來南方的潮濕,和快速繁衍的電子。
在冷冽的寒風中,
父親為了挖掘一個地窖,磨損著
一把祖父遺留的鐵鍬。
兩種鐵的相遇,
注定是偶然的,類似于神諭。
對于日益凋敝的山區(qū)農(nóng)業(yè),一個村民的未來
幾乎清晰可見。
挖出的箭鏃,注定無用。
他毫不理會,還是一直在甩著土塊,
像固執(zhí)地與生活作對。
箭鏃又一次被發(fā)射出來,
但軟綿無力,無法射中誰。
在這個老套的冬日,與地球的一小塊土地作戰(zhàn),
竟也能取得小小的勝利。
其實又有何勝利可言,在歷史的
荒謬之處,
鋒利的箭鏃,也無法提供正義的答案。
地窖
那些被安置在鄉(xiāng)間的不規(guī)則地窖
沒有一個里面不埋藏著紅薯,不埋藏著白骨
奄奄死去的鐵門
把守著白雪皚皚的又一個冬天
讓一個地窖蘇醒
需要吹進一噸的空氣,甚至要
敲響十面鑼鼓
可這些并不能妨礙我們
依次跳進地窖
來測一測它的深度——
那深不見喉的黑暗,那撲滅一支燭火的黑手
往往瞬間就引領(lǐng)我們
集體上升
而下沉的永遠是熾熱的金屬
是不斷萎縮的肉體
多年前,為了獲取一日的食物
父親用一根火柴照亮了整個地窖
在隱約的光亮中,我看到了
他幽暗的頭部……
死亡的鐘
掛在墻上的鐘,它已經(jīng)死了。
無異于一具干尸。
它卻不肯輕易地掉下來,
砸碎地上的灰塵。
在墻的巨大陰影里面,三枚指針
組成的剪刀
輕易不會張開嘴巴。
父親是另一個鐘,
五十一年的發(fā)條,最終被自己擰斷。
腹腔中腫脹的電池,
流出了汁液——
那,仿佛是他一生中最神秘的部分。
一個鐘歸隱土中,一個鐘爆裂于火焰。
上帝收留它們的方式,
如同收割麥子。
在饑餓的人間,每個人都在大口地
吞咽著光陰,
都在給自己體內(nèi)的鐘
上緊發(f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