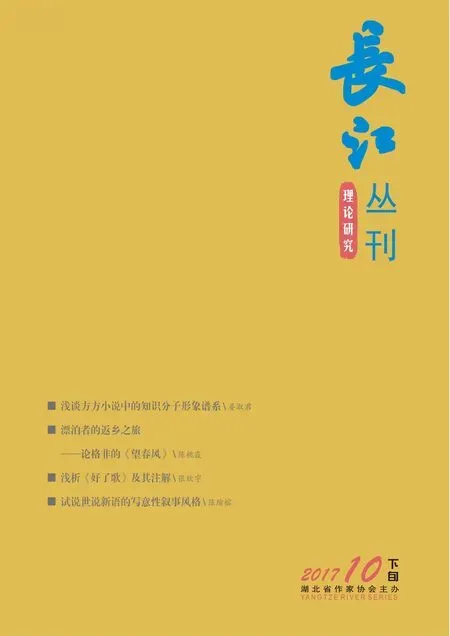新世紀臺灣文學獎之狀況
古遠清
新世紀臺灣文學獎之狀況
古遠清
在這個充滿欲望的時代,創作是一種欲望,作品出版同樣是欲望,得獎則是更大的欲望。
文學組織制度,本來不僅包括執政黨文藝政策的制定、文學團體的設置以及出版制度、教育制度,它還包括為滿足各種欲望而建立的文學獎制度。
在臺灣文學獎方面,上世紀50年代最具權威性的是官方設立的“中華文藝獎”,于1955年解散后仍有軍方、黨方和政府部門頒發的各種文藝獎。可這些官方文學獎的權威性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已被《聯合報》《中國時報》的文學獎所取代。到了政權輪替,隨著政治夜市熱鬧非凡,隨著選舉口水漫天飄灑,隨著“去中國化”思潮愈演愈烈,臺灣的文學評獎制度在新世紀發生了裂變。
新世紀文學獎和上世紀最大的不同是藍綠意識形態和多元共生現象全面滲透評獎體制、機構、出版策劃和讀者反應等方方面面。官辦的如“國家文藝獎”、“總統文化獎”、“金鼎獎”盡管還像過去那樣對文學發展起著所謂樣板作用,但大部分作家對其評獎標準均不認可。藍、綠兩派和消費市場無時無處不在建立各自的評價標準與機制。即使是標榜最客觀的評獎,也或明或暗受這種標準與機制的制約。這就是說,評獎制度是按照各自“政治正確”原則和藝術標準,“制造”自己的文學明星,推出自己認可的“優秀”作品,另一作用是讓作家們在簡歷中增添一條得獎資歷。
新世紀的臺灣文學獎之多,可稱得上是文學史上的另一個傳奇。且不說全球性的、全島性的、地方性的,還有屬于媒體、佛教、學校、基金會、行業會、工作室的。這些文學獎所從事的文學活動相互作用,共同參與了新世紀臺灣文學制度的建構。在新世紀臺灣文學場域中諸多評獎活動,不僅包括批評和創作中所運用的一般文學知識,也包括政治知識、社會常識、市場意識。正是這些知識的合力作用,決定了新世紀臺灣文學獎的基本形態。創辦雜志、舉辦會議、對獲獎作品進行評價,然后出版得獎者傳記,讓得獎者巡回演講,是影響新世紀臺灣文學獎的重要方式。因此,文學媒體、民間團體、臺灣文學館、地方文化單位成為新世紀文學獎變革的重要推手。
新世紀臺灣文學獎的權威性來源于政治權力及由此帶來的文學話語權。即是說,某些全島性的文學獎人們之所以看好,很大程度是因為主辦者和執政者有良好的合作關系,擁有充分的行政資源,否則光亮度就不大。如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于2001年創辦的“總統文化獎”,在民進黨統治時期被“綠化”,鐘肇政等綠營作家獲得了相當于終身成就獎的百合獎。
官辦獎為避免僵化和輿論的指責,也作過一些小修小補的改革,如“國家文藝獎”原稱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這里有舊制與新制之別,其差異就在于舊制“類別與項目”較為細密完整,比如文學部分,舊制細分小說、散文、兒童文學、新詩、舊詩、歌詞、傳記文學、新聞文學、戲劇、文藝理論、電影劇本等,每屆申請人夠水平則頒發,無則從缺。新制則較重視終身成就,這未必與當年成就有關,如文學類僅一人得獎,是為了推廣得獎者的創作經驗與成就。
在政治正確——審美標準——市場效應三元模式的新世紀文學評獎機制中,獲獎者的成分在走向年輕化。由最初為包括資深作家、傳播者和消費者在內的極具兼容性的話語,而隨著人們對文壇現狀及文學市場的深入把握,得獎者更多的是新一代作家。這些年輕作家從大學時就開始“征戰文學獎,從《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一路過關斬將,拿到三大報文學獎。大報文學獎對他們來說,有一點古代科舉的意味,又像是現代的國家證照考試——得了獎,就拿到進入文壇的通行證。”正是靠這種后來居上的新秀,潛在地影響著新世紀臺灣文學獎體制的變革。由《聯合報》系主辦的《聯合報》文學獎和《聯合文學》新人獎之所以未曾老化,不僅在于它的公開原則,還在于這個獎一直在突出新人,不被著名作家所壟斷,如2012年第34屆《聯合報》文學獎,剛大學畢業的舒貓(吳純)便榜上有名。
新世紀臺灣文學場域在弱化官辦文學獎向地方化傾斜的改革中,逐步確立了作家們相對于政治干預的獨立地位。“工作室”的加盟,也給通俗文學得獎開辟了新管道,而高校臺灣文學研究的開展,亦為文學論著進入評獎機制架起了橋梁。這方面的文學獎有由明日工作室于2005年創辦的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征文,由臺灣詩學社于2009年創辦的臺灣詩學研究獎和由臺灣文學館于2005年創辦的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
新世紀臺灣文學獎另一突出趨勢是綜合型的獎項在萎縮,而專門化的獎項越來越多。這專門化表現之一要么獲獎者是清一色本土作家,要么本土作家是專用母語創作。另從文體上分,有小說獎、散文獎、新詩獎、翻譯獎,還有長篇小說發展專案、九歌二百萬長篇小說獎、倪匡科幻獎、兒童文學獎等等。也有以作家命名的文學獎,如由個人出資設立、打破官方文學獎一統天下的“吳濁流文學獎”、“巫永福獎”、“吳三連獎”。另有為紀念散文兼翻譯大師梁實秋而設的梁實秋文學獎,它走過四分一世紀后由梁實秋生前執教多年的臺灣師范大學接辦,人們期盼它“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有些地方文藝獎雖然覆蓋面不廣,但在縣市起到了鼓勵創作和振興文運的作用,如由臺南縣政府創辦于2002年的玉山文學獎,由高雄市文化局創辦的“打狗(高雄的本名叫“打狗”)文學獎”,以及由臺中市創辦的大墩文學獎、臺北市創辦的臺北文學獎、臺北縣創辦的臺北縣文學獎。這些獎從征文到評審再到頒獎,差不多花一整年時間。可惜的是頒獎后作品的傳播陷入困境。主辦者極少考慮獲獎作品如何走向社會,走向大眾,進行被閱讀及評論。“作家生活的困窘、出版市場的‘冷清’與頒獎時的‘熱鬧’幾乎成了兩極的對比。”
文學獎本是作家的身外之物,但仍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不入流的作者對此趨之若騖,以讓文學獎證明自己的文學地位和身份。“上個世紀的作家多半是人生逼成了作家,這一世代卻是人生還沒有開始,便立志要當作家。他們少了上一代夜奔梁山的江湖氣,卻像十年寒窗的書生,一路按部就班地從學生文學獎拿到大報文學獎。好不容易金榜題名,卻偏偏遇上改朝換代——平面媒體式微,文學獎失去‘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光環。”為彌補這一不足,也為滿足這些作家的另類要求,各種部門均插手文學獎,為文學獎游戲另添了幾分“春色”,如性史2006征文、外籍勞工詩文比賽、基督教雄善文學獎,另有宗教文學獎、法律文學創作獎、臺北旅行文學獎、葉紅女性詩獎、世界華文文學獎、海翁臺語文學獎、臺灣閩客語文學獎、彭邦楨詩獎、臺灣詩學散文詩獎、林榮三文學獎、臺灣文學部落格獎、風起云涌青年文學獎……
有一部風行一時的草根電影叫《瘋狂的石頭》。套用這句話:“風起云涌”以至泛濫成災的新世紀以來的民間文學獎,也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這高達上百個的文學獎,共享著如下幾個特征:“真假難辨、反諷主義、黑色幽默。”不過,這多民間文學獎,畢竟說明非官方獎已成為左右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其特點是未經過藍綠兩黨意識形態的權威認證,另在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上,都談不上豐厚。一旦主辦單位“斷奶”,這些文學獎也就無疾而終。
文學獎本是寫作的競技場,可多如牛毛的新世紀臺灣文學獎項,如果不是病入膏肓,恐怕也是問題重重,急需下猛藥診治:
1、獎項相似,造成一稿多投,重復發獎。許多作家光靠參加各類的文學獎,據說一年就可以有六位數的獎金進賬。
2、不少獎項不僅資金欠缺,稿源也嚴重不足。
3、許多征文作者均以上次得獎作品為樣板進行炮制,有獨創性的不多。
4、文類不平衡,許多文學獎偏向小說、新詩、散文三大類,劇本的征集常常被忽略。
5、隨著副刊向文化方面轉型,能登較長的短篇小說的副刊越來越少,因而征文時對短篇小說的數字要求越來越短,這不利于這種文體的發展。
6、評審團隊與機制未能及時刷新,評審委員長期老面孔居多,得獎者也差不多是固定那幾位。正如鍾怡雯所說:“文學獎多到可以產生專業參賽者,或者所謂收割部隊。”
7、某些征文獎已成了投機分子進入文壇的敲門磚。
更重要的問題是兩黨政治滲透其中,如黃凡的小說《反對者》,因書中有對國民黨強烈不滿的內容,在《自立晚報》設立的百萬大獎評審時,支持國民黨的評委馬森、司馬中原投反對票,而不滿國民黨的評委看了后覺得正中下懷投了贊成票,可最終未超過半數而落選。又如呂正惠的一本評論集曾被出版社上報去評金鼎獎,可因為他“左統”立場太鮮明了,故一些評委就以另一本書作為跟他對抗的資本。2011年在臺北頒發的“國家文藝獎”也有小插曲:親自到場的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馬英九特別上臺致贈五位得獎者小禮物,唯獨歌劇藝術家曾道雄不愿上臺,他表示這是藝術的場合,不應扯上政治。不過,馬英九事后仍走下臺親自向這位綠營藝術家握手道賀。
在眾多不滿和反對聲音的背后,隱藏著臺灣文學界一直不敢面對的事實:文學評獎受到這種黨派及輿論、商風、社團制約的因素,越來越多外在勢力在干預它們,這些勢力扼殺了評獎是為了再現典范乃至發現經典的可能性,使既定的美學立場無法堅守,最終導致了某些文學獎評獎者就是獲獎者,或者總是把獎項頒給那些熟面孔和圈內人,成了小圈子“排排坐,分果果”的吊詭,這造成評獎在社會上影響甚微,即便在文學界也少有人問津。這種把評獎蛻變為人情的游戲、資本的游戲、娛樂的游戲的做法,造就了一批“獎棍”或曰“得獎專業戶”。這些人寫自己的文學小傳時,光得獎經歷就有洋洋灑灑幾百字,形成臺灣文壇獨有的最詭異現象。盡管臺灣文學獎主要是鼓勵新人的征文比賽,不像大陸多獎勵出過許多著作的成名作家,但就其缺陷來說,正和南京大學王彬彬評某些大陸文學獎一樣:所謂文學獎,不過“是組織者、評委和獲獎者的一次自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