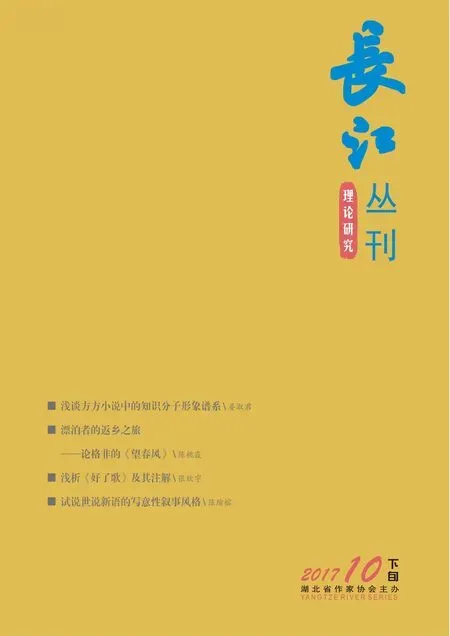漂泊者的返鄉之旅
——論格非的《望春風》
陳桃霞
漂泊者的返鄉之旅
——論格非的《望春風》
陳桃霞
格非以善于設置“敘述空缺”與“迷宮”而聞名于先鋒作家群。他汲汲于藝術探索,并在近年來的創作中頻頻表現出回歸古典的趨向。在格非的思想譜系中,對人類精神狀況的勘探貫穿始終,它一方面延續了上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思考,一方面也顯示了作者智性寫作的特征。
鄉土文學 鄉土性 格非 《望春風》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這一對中國社會的判斷早已為世所公認。數千年的農業社會傳統孕育了中國文學中的重要一脈——鄉土文學。關于鄉土的美學表達,以魯迅與沈從文為代表,主要有啟蒙、審美或烏托邦的不同表現形態。《望春風》首次將背景置于鄉村,成為格非完全意義上的一部鄉村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也涉筆鄉村,但鄉村未能構成小說的整體背景,且它在一定程度上還帶有較強的烏托邦色彩)。不同于沈從文浪漫的鄉土想象與近乎固執的城鄉二元書寫,賈平凹對傳統敘事資源與民間藝術傳統的悄然整合,張煒“融入野地”與對道德理想主義一如既往的持守,閻連科的寓言敘事和苦難敘事,格非在一種開放的藝術眼光下創造出了異質性的鄉村景觀。他沒有回望現代化進程下百年中國鄉土的野心,也不如賈平凹那樣秉持著細致描摹鄉土日常的耐心,而只將目光聚焦于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儒里趙村,展現其中流失的鄉村圖景與整體性潰敗的命運,表達對“故國山川的悲情”[2]。《望春風》營構了多重審美空間,美學特質豐富,是一部含義復雜的文本。
一、對現代性的反思與重返烏托邦的沖動
“在古典社會學大師那里,現代性的負面效應雖被指認,但總體而言,一種關于歷史進步的樂觀信念占據著主導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性建構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和所造成的痛苦與不幸,愈益充分地暴露出來。”[3]現代早已成為一種宰制性話語,一種對文化與文學實踐具有相當左右力量的話語,這一話語方式影響了對于中國經驗的表達。按照謝有順對《老生》話語的解讀方式,《望春風》中的現代話語也可分為前期的革命話語與后期的經濟話語。現代性造成了鄉村的精神危機與倫理沖突。無孔不入的革命理性雖已侵蝕了儒里趙村的原始生態,作者卻于波詭云譎的革命話語下展現出了鄉土文化的恒定性。原本劍拔弩張的批斗會在他筆下呈現出溫情脈脈的一面。革命干部嚴政委趕赴舊式文人趙孟舒的大殮儀式,為其自戕而落淚。
這些有情的文字,既是古老鄉村倫理傳統的延續,也從側面展現了新舊交替時期獨特的政治生態。盡管鄉村同樣有著權力異變的殘酷,但趙德正、高定邦兩代村干部延續了儒里趙村的儒家文化傳統。作者以寫村史的方式展示村莊的文化傳統時,也不動聲色地展示了鄉村日常倫理。先鋒作家作品“秉承‘五四’的啟蒙文學傳統,在歷史批判和民族想象中,盡展其濃郁魅人的家國情懷”[4]。格非早年追慕博爾赫斯關于“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的表述,從《江南三部曲》開始,《隱身衣》預示著他創作的新變,《望春風》再次顯示出作者突破自身限度,觀照社會現實與探勘人性的熱情。現代性很大程度上被時間化和現在化。《望春風》涉筆土改、文革、改革開放與新世紀以來愈演愈烈的城鎮化進程。小說展現了在失落的鄉村傳統背后作者的復雜心境。當魯迅筆下的“我”成為“五四”知識分子返鄉形象的代表,伴隨著現代性的是知識分子群體對鄉土中國的隔膜。格非沒有如沈從文那樣創造出難以為繼的鄉土幻夢,而是展示了溫情、質樸卻不乏憂傷的鄉村圖景,在展示人性幽光的同時不回避其中的粗糲、暴力與陰暗。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我相信人類不但會茍且地生存下去,他們還能蓬勃發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惟獨他留下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出這些東西。”[5]儒里趙村某種程度上顯現出本雅明“靈光消逝的時代”的意義,在靈魂掛空的現代社會,當鄉村倫理日漸消亡,“我”所完成的只可能是一場無法實現的返鄉之旅。《望春風》與《喧囂與衰敗》、《我彌留之際》都狀寫了鄉村的荒原景象。與福克納一樣,格非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下,回望了鄉村文化傳統,表現出無奈與感傷,但福克納在摹寫南方傳統的失落時,于冷靜的反思中,更多地思索了人類的生存困境。與格非對人類前景的樂觀主義相比,前者顯得更為深沉博大。
二、傳統敘事資源與先鋒小說筆法
格非藝術視野廣闊,其“小說敘事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喜歡馳騁于想象空間,也擁有可靠的寫實能力;他擅長狡猾的虛構,也諳熟傳統的常規技法;他深愛飄忽不定的常規意象,也認同明暢如水的語言;他借鑒博爾赫斯的詭秘,也從中國古代文論的‘空白’、‘沖淡’、‘含蓄’中吸取營養。”[6]從《江南三部曲》開始,格非回歸到以《紅樓夢》、《金瓶梅》為代表的中國敘事傳統。“當我們斷言格非在靠攏一種中國敘事傳統的時候,并不僅僅是在強調一種小說藝術,而更是在強調一種作家的世界觀,強調作家理解看待世界、社會以及人性的一種方式。”[7]《紅樓夢》中,賈雨村寄居于葫蘆廟中,賈府事敗后,王熙鳳和賈寶玉被關入獄神廟,《浮生六記》中的蕓娘落魄時也是寄居于廟中。《望春風》描述了半塘寺和便通庵。“我”父親趙云仙在變通庵自縊,而“我”和春琴在歷盡生活的種種坎坷后,也在此寄居落戶。這種靠攏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模仿,而具有更為深層的意義。艾略特從南美作家的寫作中受到啟發,格非也認為,回歸傳統寫作不等于與先鋒寫作絕緣,好的小說一定是對傳統的回應。小說中有“說書人”傳統,作者對人倫世俗的強調延續的正是明清白話小說一脈。春琴兒媳夏桂秋與《紅樓夢》薛姨媽兒媳夏金桂相似,二者都為庶務夾纏,性格跋扈驕悍,潑辣、善妒、狠毒。至于人物對話方面,這里不再贅述。《望春風》還采用了《史記》“本紀”和“列傳”的結構方法。“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傳統小說筆法也在小說中得到體現。
作者自言,在《望春風》中增加了陌生元素。這表現為對西方現代藝術手法的巧妙設置,先鋒筆法在歷經歲月的沉淀后以更為圓融的形態得到復現。現實主義小說往往遵循日常生活經驗的直線式時間觀。新時期以來,以馬原、格非為代表的先鋒小說家對西方小說技巧進行探索。如果說賈平凹的鄉土小說延續了五四作家鄉土寫作的現實主義精神,《望春風》則在與傳統敘事資源對話的同時,精心設置了多重先鋒手法。西方現代敘事技巧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感應”、“心物交融”的哲學觀照有著共通之處。博爾赫斯認為“世界是一個謎”,格非被稱為中國的“博爾赫斯”,命運之謎與欲望之謎是格非早期小說的主題。博爾赫斯的文學游戲論對中國先鋒作家有著深遠影響,他們在創作中注入哲學本體論思考。博爾赫斯的小說在整體上呈現出圓形結構的特征。維柯在《新科學》中首次提出“詩性智慧”的概念,認為這是早期人類認識自然萬物的一種方式。《新科學》闡釋了時間的循環性,從而形成了一種圓形結構。時間可以交叉、往返,結尾意味著開端,有限蘊含著無限,顯示了作家們對中國天人合一思想與宗教中的輪回與因果觀等東方哲學的靠近。《望春風》中,趙德正的人生軌跡從看守宗祠始,到看守宗祠終。高定國作為村里的會計,“以七十高齡,又獲重聘,重新擔任會計一職。他的一生,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起點。”而我“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帶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會離老家更近一些。”
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講述了一個奧德修斯式的返鄉故事,《望春風》嵌入了希臘史詩《奧德修斯》的寓言結構。《奧德修斯》中的主人公在克服重重險阻返鄉之際,重新開啟新的征程。“我”在經歷了人生的種種坎坷后,在家鄉開始了新的生命循環。相比于父親因政治撥亂與命運荒誕而埋骨故鄉,母親終老一生難回自己心心念念的家鄉,“我”在一次次的自我放逐中,雖然離家鄉越來越近,卻在鄉村的整體性潰敗中已無法魂歸自己原初意義上的家鄉了。
小說中,本雅明的“說故事人”(storyteller)從最早唐文寬對話本小說的講述置換為同彬自身走南闖北的經歷,最后堂哥趙禮平的電視機徹底改變了村人的聽故事傳統。這些細節顯示了格非與西方文論對話的熱情。《望春風》依然有著作者所擅長的“敘述空缺”,小說最后也未明確指出“我”父親離奇死亡的真相,這只能解釋為冥冥中不可預測的命運。敘述空白也為后文“我”對母親的自由追憶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三、抒情傳統與現代中國
格非是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作家,不然,他不會積十年之功孜孜于烏托邦世界的營構(創作《江南三部曲》)。任何時候,審美追求與勘測人性永遠都應成為文學之首義。格非認為,文學是失敗者的事業。從《欲望的旗幟》中的曾山、賈蘭坡,《江南三部曲》中的陸秀米、譚功達、譚端午,《隱身衣》中的崔師傅,一直到《望春風》中的趙孟舒,趙伯渝,這些主人公無論身份、地位如何,一律有著濃郁的知識分子氣息,表現出對時代主題的自覺疏離,對歷史本質的深度懷疑。格非無意于對文化、民族和歷史作整體性審視,他只是從事一種個體化時代的敘事。
本雅明在《普魯斯特的形象》里談了“意愿性回憶”和“非意愿性回憶”,在寫作中也不斷地召喚經驗。《望春風》是一部對鄉村的追憶與告別之作。“《望春風》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大規模地描寫鄉村生活。鄉村已邊緣到連根端掉,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我的家鄉僅存在于我記憶之中。”現代化進程下的鄉村呈現出艾略特的荒原特征,格非沒有止于為鄉村挽歌一曲。他筆下的鄉間日常顯示出作者自覺騰挪于《紅樓夢》、《金瓶梅》、《浮生六記》等傳統敘事資源之中。清代憶語體小說盛行,《浮生六記》是這一類自傳體敘事方式的代表作,它記述了夫妻之間的平凡瑣事,展現了日常生活的雋永與真情,《望春風》對平凡日常生活細膩、深情記述頗能體現“憶語體筆記”的特征。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認為,“憶語”即是通過對材料的選擇和編排,復現某些不完滿和未盡完善的東西,是對生活中某些意猶未盡之處的瘢痕的展露,對那些從未獲得成功,也從未有過結局的東西的不滿足。可見,憶語體也是一種創傷性書寫。作者希望用文字復現過去,或是召喚失去的親人,或是憑智力戰勝某種不可避免的結局,如死亡、愛與死的永恒矛盾。《浮生六記》開卷寫道:“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茍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望春風》中,“我之所以決定寫下這個故事,就像春琴所說的,僅僅是為了讓那些頭腦中活生生的人物不會隨著故鄉的消失而一同湮沒無聞,如此而已。”小說也顯示了格非的一種出走與回歸,回歸鄉土,回歸傳統。相比于賈平凹與鄉土的難分難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格非暌違鄉土多年,也獲得了一種更為達觀的視角。在詩意的筆調下,文本顯得平和沖淡,這與他研究廢名,浸淫于沈從文、汪曾祺這一脈有著濃厚審美趣味與人性情感內涵的小說傳統有關。
這種抒情性還表現在小說的情感飽和度上。格非一改早期先鋒作家的零度敘事模式,小說情感飽滿,感人至深。小說中關于母親的追憶,對回歸桃花源的深情書寫,都體現了這一點。
《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是格非思想與藝術的集成之作,它以深刻獨到的歷史眼光與豐厚的古典文化素養重構了百年中國的革命歷史版圖,讓人重新思考烏托邦這一中國語境下含義復雜的元話語。作為一部意蘊深度、內涵豐富的文本,《望春風》還有很多解讀的空間。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
[2]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M].北京:三聯書店,2010:8.
[3]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9.
[4]葉立文.家國情懷與極地之思——論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思想主脈[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1):148.
[5]福克納中短篇小說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85:605.
[6]方克強.跋涉與超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213.
[7]王春林.長篇小說文體多樣化景觀的打造與構建——2016年長篇小說創作一個側面的理解與分析[J].小說評論,2017(1).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