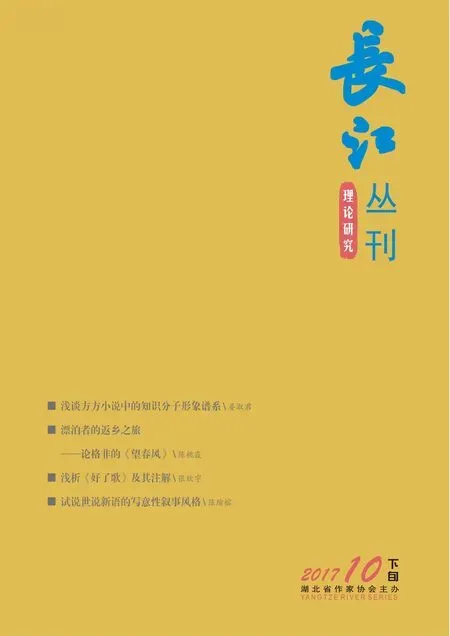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演化、困境及動向
宋曉琴 海 敬
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演化、困境及動向
宋曉琴1海 敬2
文化與科技均對學術范式產生重要影響,起源于古希臘的理性精神是科學與文化整合的集中體現,但并沒有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面臨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與價值理性的持續式微的困境。科學與文化的統一,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融合,將是未來學術界開展學術研究的前提與必由之路。
學術范式 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
文化與科技均對學術范式產生重要影響,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是學術范式發展的必需。文化與科技的融合不是單向度的主客體關系,科技影響文化層面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人的思維等,文化又反過來是科技得以發展的土壤。科技與文化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的文明成果,既牽涉面向手段與目的的工具理性,又涉及精神與意義的價值理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工具理性在改造大自然中扮演了中堅角色,而價值理性則顯得日漸式微,使人類在獲得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陷入嚴重的生態與人文危機。在學術研究領域,同樣也出現過度依賴科技,過度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視價值理性的風氣。反思目前科技與文化割裂的困境,促進兩者之間的融合,構建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意義重大。
一、文化與科技融合學術范式的演化
理性是學術研究所遵循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個發展中的歷史范疇。在古希臘時期,先哲們面對浩瀚的宇宙就展開對自然奧秘的理性探索。他們透過紛繁的自然現象,去探索隱藏在現象背后的世界統一性認識。泰勒斯提出的“萬物源于水”,阿那克西美尼認為的“萬物的本原是氣”等都是早期人們關于世界本原的認識。這些觀點是西方思想開始擺脫神的束縛走向理性思考的肇始,他們用一種或若干種基礎物質取代了宗教神話中超自然的主宰力量,認為世界的本原是物質,這是人類認識的一次重大飛躍,第一次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性世界觀,這正是科學精神最需要的因素。[1]同時,希臘人把數學提高到哲學的層次,譬如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萬物皆數”,借助數學去認識世界,這也是科學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為科學精神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科學精神產生于古希臘的自然哲學當中,人文精神則主要體現在古希臘神話和先期文學作品中。著名的荷馬史詩、伊索寓言等古希臘著作里,人們可以感悟到希臘人關于道德的思考,并可以體會到這些道德對于人的行為與思想的規范訴求。普羅泰戈拉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該觀點把人的認識看作是衡量萬物的尺度,也就是把人置于哲學思維的中心。蘇格拉底提出的“認識你自己”、“道德即知識”一方面體現了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則使這一精神具有了思辨理性的色彩。他把人從傳統的權威當中解放出來,通過反思自己的狀態來認識本質的人。
因此,起源于古希臘的理性精神是科學與文化整合的集中體現。科學精神是在質疑自然與本性合理性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人文精神是在對人的習俗、倫理、存在和價值進行探尋的過程中產生的。科學與文化的分離、沖突和對立并不是與生俱來的。相反,在早期的人類文化樣態中,科學和文化是充分整合與內在統一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都是人類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理性的兩翼,他們相互作用,彼此影響。但是,由于融合科學與文化的理性在此時還處在初級階段,其本身或多或少地仍帶有神秘色彩,并沒有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到了中世紀,理性之光就被頑固并強大的基督教神學所遮蔽,社會處于宗教統治之下,人們的精神再一次滑入無知和迷信之中。
二、文化與科技融合學術范式的困境
(一)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
工具理性也被稱為技術理性,源起于韋伯的合理性概念,是為了達到特定的實踐目的而運用的中介方法,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和效益性等特征。[2]工具理性是西方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結合,主要指向主導工業文明的意識形態。在功能方面,科學技術確實是人類實現改造自然,增加社會財富的中介手段,具有很強的使命感和逐利性。工具理性是科學技術文化的主導力量,是科學技術改造物質世界的重要載體。然而,隨著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斷加深,它逐漸成為人們信賴的不二選擇,受到非理智的頂禮膜拜,從而出現了科學是萬能的思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工具理性開始蔓延和擴增,已經在人類活動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在人們看來,行為的有用性和有效性是最為關鍵的,任何可以獲得“成功”或“效益”的短期行為成為了人們追逐的目標。如此,科學技術的方法與功能被人為地片面化、絕對化,人慢慢地喪失主體性而淪為工具的奴隸,科學技術的應用失去了應有的價值規范。
對于自然的態度方面,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使人們以符號化、形式邏輯和公理化為標準判斷一切,慣于采取總體控制的原則,追求人類利益的最大化,過度攫取自然資源。理性本身固有其合理的價值,但如果理性的形式僅表現為“對自然的控制”,那么這種思維將會扭曲,必然會使人們誤解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片面強調邏輯與規則的重要性,忽視現象的差異與特殊性,把現象的復雜性、情境性、豐富性片面解讀為數學符號、邏輯的規范性,使雙向互動的主客體關系歸結為單一的邏輯關系,導致奴役自然意識的生發。自然變為人類掠奪和征服的對象,科學技術慢慢失去了原本對自然所具有的人文關懷。以工具理性為核心,會讓人們熱衷于滿足短期的物質需求,追求經濟利益和生產力最大化,而忽視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如果工具性思維傳播到社會各個行業的每一個角落,影響自然界生態系統的每一個單位,人類將面臨更大的人文危機與生態危機,將使人類瀕臨全球災難的邊緣。目前全球變暖,各種極端天氣頻頻出現,人類已多次嘗到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的苦果。在學術研究領域,過度追求工具理性的后果也顯而易見,使得學術研究成果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關注表面現象,忽視內在的人文基礎,使得研究成果缺乏對于客觀實踐的解釋與應用,背離了學術研究求真、求實的價值規范。
(二)價值理性的式微與萎縮
由于受到工具理性的影響,學術研究的價值理性漸漸式微,在學術研究領域普遍存在科學精神喪失,甚至走向失范和混亂的現象。更進一步,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在很多研究中漠視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人被技術與符號所刻畫,淪為“單向度”的人。[3]學術研究領域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關系的錯位導致學術精神缺失,學術不端、學術功利化等混亂與失序,對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需要依靠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來改變落后于西方國家的現狀。學術研究同時是促進人類文明前進和知識積累的動力,如果學術研究領域缺乏理性精神,不能做到客觀公正、求真務實的價值取向,勢必導致學術不端、學術混亂的現象,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失序與混亂。
從人文精神層面來看,科學技術進步的初衷是為了使人的個性與主觀能動性得到解放,使人擁有自由和尊嚴,提升人類社會的福祉。但在現代社會中充斥著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有用性、效益性成為一切活動的行動指南。反觀人的思想,人們更注重短期利益,關注當前利益,忽視科技對人與社會發展的價值理性,也忽視對人本身的價值、目的和意義的反思,人成為工具理性的奴役和控制對象。價值理性的式微加強了工具理性對人與社會發展的異化力量,進一步導致工具理性的擴張,使價值理性越發萎縮,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發展陷入扭曲的怪圈,社會發展陷入嚴重的困境。
三、文化與科技融合學術范式的動向
人類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雙重屬性,人類文化同時包括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人類理性也可分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在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來逐漸取得優勢地位,成為盛行一時的哲學思潮,其特征是片面夸大自然科學的效用與適用性,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理解自然科學,把自然科學異化為人類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這使得人類更多地看重眼前利益而不加節制地使用科學,使科學促進人類發展的初衷發生改變,給整個人類社會與環境生態帶來嚴重挑戰。面對這些困難,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采取反工具理性、反自然科學的態度。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它在造福人類社會、改造自然的同時也會給人類社會帶來諸如核危機、破壞生態環境等負面影響。科學如何造福人類,改善環境,關鍵在人類自身。[4]首先,價值理性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它更加關注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追溯人之為人的存在意義,崇尚人的行為要符合價值觀,倡導熱愛自然、保護生態、改善環境,對自然采取友善的人道主義態度。只有把價值理性放在與工具理性同等重要的地位,才能消除偏執一端的科學萬能論,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泥潭,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處于和諧狀態。其次,科學技術的負效應背離了人類追求科技進步的初衷和人類的道德理想。因此,在科技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時代里,任何一個科技工作者都不能獨善其身,把自己置身于科學的社會問題之外,也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地看待自己研究的成果給人類可能帶來的危害,而必須懷著一顆崇高的為人類造福的心態開展工作,要樹立堅定的社會責任感與主人翁意識,在科學與文化融合的范式下開展學術研究。再次,把握高技術與高情感的平衡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撰文指出,今天的社會正處在從強迫性技術向高技術與高情感的平衡的轉變時期,我們周圍的高技術越多,越需要人的情感。實現科學與文化的有機融合,可以使人進一步了解人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關系,加深人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情感,從而實現人與自然、與社會關系的和諧,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近期,學術界主張將文化與科學融合起來開展研究的傾向愈來愈強烈,并且在工具理性思潮中日益表現出對價值理性的重視。科學和文化的融合將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創造出更為豐富的人類文化成果。科學與文化的統一,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融合,將是未來學術界開展學術研究的前提,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將是每一位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必由之路。
[1]苗壯,鄭克嶺.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裂與融合[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2):25~28.
[2]張華夏.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3]鄧環.科技文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及融合[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19):25~28.
[4]高劍平,唐咸來,曲用心.論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相互整合[J].求索,2003(04):154~156.
1.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決策咨詢研究所;2.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
本文系甘肅省社會科學院一般項目《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學術范式與理論框架研究》(項目編號:YB201712)。
宋曉琴(1980-),女,漢族,甘肅靖遠人,碩士,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決策咨詢研究所館員,研究方向:事情報、信息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