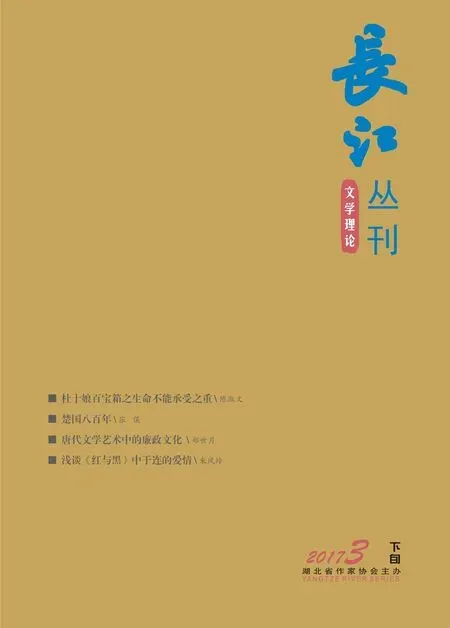公意的表達與實現
——從盧梭《社會契約論》視閾談
赫意夫
公意的表達與實現
——從盧梭《社會契約論》視閾談
赫意夫
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之中,為我們詳盡闡釋了其國家權力理論之中,政府權力來源的內容,同時也為我們闡述了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和政府職能行使方式。而在盧梭視閾之中,作為主權最高意志的“公意”,是如何能夠被人們提出和表達,又怎樣通過政府權力行使得以實現?筆者在這里將結合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對“公意”之表達和實現所面臨的問題進行討論,探究這些問題出現的淵源,尋求盧梭社會契約政治思想的當代意義。
盧梭 《社會契約論》 權力社會 公意
一、契約——從自然走向文明
通覽盧梭之《社會契約論》,我們可以發現其四卷之中有著非常清晰且簡明的內在邏輯,首先第一卷是在告訴我們社會契約之必要性問題,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與盧梭另一部著作《論人類不平等起源和基礎》相結合,預設了一個人類的純粹狀態——無政府之自然態,人們在自然狀態中自得其所,有各自本有的天然權利,但是在生產水平和人際交往上很慘淡。盧梭的自然狀態是一個和諧態:他認為自然狀態下的野蠻人不會有掠奪和統治他人的欲望等積極的利己主義,而只會有平和、寧靜甚至不與其他“人”維持聯系的消極利己主義。“因為人類生存于原始獨立狀態的時候彼此之間絕不存在經常性的關系,所以他們天然地絕不會是仇敵。”很多學者認為盧梭的自然觀點是從批判霍布斯開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洛克的思想進行了發展補充,但其在形式和論證體系上,還是沒有跳出霍布斯等人的范圍。
《社會契約論》首卷之中,先提出自然狀態的人類擁有基本權利:生存權、自由權、平等權和基于“最先占有”的財產保有權。強調強力強權、戰爭結果和出身都不能成為對他人基本權利剝奪的理由。而當人類必須要通過改變初始的自然狀態來維持其生存生產之時,就逐漸建立起了社會,也由于社會之中,需要區別個人財產出現私有制,從而要開始考量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創建一種能以全部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的結合形式,使每一個在這種結合形式下與全體相聯合的人所服從的只不過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樣的自由。”盧梭認為這就是社會契約的意義所在,而人類也就此進入了文明狀態,走出了自然狀態。人們需要在聽從先天本能的驅使之前,首先詢問自己的理性,人類由于社會契約所損失自己的天然自由——企圖可以得到一切的無限權利,而得到社會的自由和對他們所擁有一切的所有權。人們放棄自然自由而獲得道德自由,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
這就是第一卷要告訴我們的:人類是怎樣從自然走向文明社會,以及社會契約的意義所在。
二、公意——政治活動的基礎
組成社會契約之后的人們,在政治意義上就成為了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有多面性也是多維度的:“…………現在成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成員稱它為‘國家’;當它是主動時,則稱它為‘主權者’;把它的同類相比較時,則稱它為‘政權;至于結合者,合起來就稱為‘人民’……· ·’”當它作為主動的主權者時,我們可以將之視之為一個具有人格意義的整體,而這個整體的一切行為活動,是要有一定依據的,因為其中包含的所有個體,所以其行為要代表其中個體之最高意義。
在此意義上,“公意”就被盧梭提出,作為一個主權者(也可以說一個國家、一個政體)之中的最高意志而存在。公意整合了人民之中每一個個體的個別意志,卻又嚴格區分。公意總是傾向于平等,個人意志總是傾向于個人利益實現;公意總是傾向于公正,而個人意志總是傾向于偏私。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公意不等于眾意,不等于所有個人個別意志之和。
盧梭對此有論述:“眾意和公意之間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公意只考慮共同的利益,而眾意考慮的則是個人的利益;它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從眾意中出去互相抵消的最多數和最少數以后,則剩下的差數仍然是公意。”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探討,代表主權者意志的公意,是如何可以對政府(權力機構)、公職機構發揮作用和約束行為的呢?政府、公職機構,又是如何保障公意的實現呢?
三、政府和權力——如何使公意成為可能
每提及政府,我們就將之與其所行使的權力緊密關聯。在盧梭語境之下,公意——權力——政府(或說行政權執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首先盧梭闡述了政府形成的原因:當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在條件的阻礙下已經不能獨自生存而必須進行聯合,也就是把眾多個體力量結合起來,去實現單個個體不能成就和滿足的事情,這時的人們就出讓了作為單個個人的權力而收獲了在群體里才可以獲得的權利,也出讓了所有個人的自由,使這些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利益共同體之中得以保全和被認可,就如同最早先的家庭之中,子女對父權、母權的尊崇。這種認同和尊崇是建立在對自我自由和權利以及所有品之保障的前提下的。
而人們讓出自己的一切權利和自由意志,去成全公意的達成,是一種消除多元意見并且推崇同一思維、同一價值的思想,而這種同一則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礎上的整個政治共同體的規范。所以相應的,社會道德就是同化思想價值追求之后的一致性,是一種對人民的強制自由。而公意在主動的外化之后,就成為主權者,主權者不是某個或某些人,體現在人們對主權的擁有之上,則必須要將立法權牢牢掌握在主權者手中,這是至高的權力,而政府不能夠擁有立法權,政府屬于執行機構,其行政權是要受到立法者——主權者的監督和控制的。這是保證主權不會被掌握在部分人手中,從而對主權進行傷害,不能實現公意。
另外,公意在立法上的體現,是要靠民主投票來保證的,每個公民都要通過投票來表達意見,最終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公民中一些人在投票時成了少數派,只能證明此些人的觀點錯了。就此而言,盧梭在技術上、制度上并沒有提出更為令人滿意和絕對信服的意見提出方式,票數的絕對數量多少,表達的不是一個意見、決策的正確與否,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公意。這樣就很容易造成所謂“多數派的暴力”。但是如果改變盧梭的意見,建立一種間接地民主——人民代表或投票代表、議員的形式,實則就是對公意表達和實現的保障的破壞。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社會契約論》之時所要繼續爭論的問題之一。盧梭在其書中第四卷“論投票”一章之中,明確提出此種多數原則其實是一種前提:“公意的一切特征始終存在于多數之中。”所以我們看到盧梭對代議制的態度也不是十分明確:代議制的民主是否能夠表達真正的多數意見,這也是我們當今世界之中,多種政體都在討論的問題。
四、《社會契約論》論域下當前社會的一些問題
針對前文提及的公意之意義、表達和實現,結合當前我們所處的社會時代,我們確實需要對一些有關政府權力、國家領導機構的問題進行反思。
首先是對契約的理解,從古至今一直以來的中國社會思想之中,似乎并不認為整個有機社會的建立,是基于一種人與人的原始的、本有的契約,我們在長久的封建社會之中,所擁有的思想長期是強調社會分級分層的,并且統治階級掌握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
這便引入第二個問題:中國當今的代議制,及其代表的代表性問題——我們在各級選舉之中選舉產生的立法代表,與人民的聯系程度如何,以及是否能夠基本代表其所代表群眾的“公意”,并把這些“公意”提出到更高層的立法部門,最終形成一個真正的“公意”。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我們的執政黨派的問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中并沒有對黨派進行詳細論述,但是我們需要看到,當今的中國,無論是產生公意,還是立法,或是行政,都是在一個執政黨派的領導和引領之下進行的。
第四則是關于思維同一性的問題的討論:盧梭強調用同一來消除差異,講求整體性,前提是人民內部的差異消除和形成統一公意。但我們當今社會,是否要由執政黨或者權力政府,來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見、價值進行同一化處理?
《社會契約論》語境之下的公意,在當今我國社會之中,無論是形成過程還是形成結果,都似乎不能達到盧梭意義上理想化的目標,這也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雖然盧梭的觀點之中,尤其時代局限和技術層面的缺陷,但其對民主社會、人民主權的基礎性意義依然值得我們學習,并作為一面鏡子來反思我們的社會現狀。其公意表達和實現的思想更是對我們這種差異問題明顯的人口大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陜西:陜西出版社,2012.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