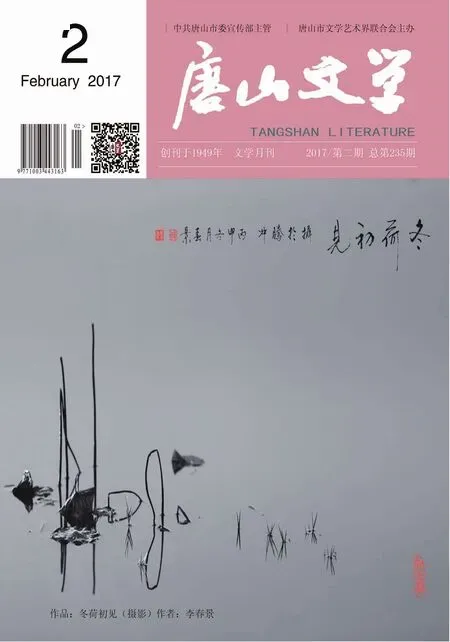小人物”的悲傷
——契訶夫短篇小說中“旋匠”的形象分析
趙群
小人物”的悲傷
——契訶夫短篇小說中“旋匠”的形象分析
趙群
契訶夫(1860-1904)是俄國小說家、戲劇家,是十九世紀末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最后一個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以精煉的語言,獨特的視角,反映了在黑暗現實下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每每讀到這類有關“小人物”的小說,不禁要贊嘆契訶夫精湛的藝術手法及情感的細膩,以小小的題材卻讓人真實地感受到這類人物的生活氣息,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生活的艱辛、無奈與悲慘。這些 “小人物”的悲傷也引起了我們對生活的無限思考。
《哀傷》是契訶夫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的經典之作,小說中的旋匠格里戈里·彼得羅夫就是這類 “小人物”的典型。《哀傷》的主人公旋匠混混噩噩地度過一生,甚至老婆死去才感嘆他四十年像煙霧一般的過去,只有酗酒、吵鬧和貧窮,簡直沒有人生的樂趣,四十年的功夫就這樣浪費了。整篇小說作者筆調嚴肅冷靜,猶如一幅樸素的單色素描畫。從這冷靜筆調中折射出的抒情來看又猶如一曲幽默的詠嘆調,可稱為:“一支詠嘆我們悲苦的小曲”。
故事的環境氣氛是哀傷的。季節是在冬天,空氣中刮來陣陣刺骨的寒風,雪花在各方面團團亂轉,這樣的環境下,一匹軟弱敗壞的小馬拉著雪橇慢慢地爬著前進。旋匠用盡力氣在雪地里拔著腳走,路面崎嶇不平,又下著雪,一切籠罩在灰色的霧霾之中,單調而又冷峻,這樣的畫面是讓人哀傷的。
故事的場景是讓人哀傷的。旋匠一路上嘀嘀咕咕,可以說是在喃喃自語,只為減輕心中的痛苦和煩惱。他設想他向醫生求情給老伴治病時的情景,他自言自語道:“梅朱娜,不要哭……耐著性子一點兒,上帝保佑我們趕快走到醫院,一會兒你就可以有救了……白夫爾要給你一點藥水,或者叫助手替你放血,或者他要親自動手,用酒精來替你揉擦——就是這樣……你把病狀告訴他,白夫爾要盡力替你醫治,他要亂喊亂跺腳,但要盡力替你醫治。”他設想了醫生對他斥罵的情景:我們到了那兒,他一定要從房間里沖出來,喊著我的名字,他要這樣喊道:“怎么?為什么?你怎么不在診治時間跑來呢?我又不是狗,整天等著你們這些鬼。你為什么早晨不來呢?滾開些!不要讓我看見你,明天再來。”
想象完了醫生的斥罵,他繼續在想象著他自己在祈求諒解時該說的話:“老爺!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發誓……天沒亮我就爬起來……偏偏上帝圣母……發怒,降下大雪,你叫我怎么能夠按時來到呢?你自己替我設想一下罷……就連頭號的馬也跑不快,我的馬你也看見的,哪里是馬,簡直是丟人。”然后,他想象著醫生最終答應給他老伴治病,老伴最終可以把病治好。寒風依然凜冽,大雪依舊在空氣中轉著圈圈,無情地打落在旋匠和他老伴身上,這嚴酷的現實和旋匠美好的設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得旋匠的命運可憐而又可悲。他幻想著最終醫生會答應給老伴治病,老伴的病會好,可最終的結果是怎樣的,誰又知道呢?他開始跟老伴叮嚀和保證,求老伴在醫生面前替他掩飾過錯:“要是巴威爾·伊凡內奇問你我打你沒有,你就說沒有,你就說壓根沒打過!往后我再也不打你了。”然后他自責和勸哄:“我疼你,換了是別人就不肯這么費勁,可是,我就送你去……盡我的力。”他還對老伴自夸:“我,老伴,知道該如何應對那些老爺。”旋匠的這些話,蘊含著他身上的喜劇性因素。但這喜劇性卻被現實無情的打敗了——老伴已經無聲地病故在雪橇上。他問老伴:“怎么樣,你腰痛嗎?我問你腰痛嗎?”但是這些美好的話語卻沒有人回答。這樣的情景帶給讀者的是悲傷而復雜的感情。老伴無聲的走了,旋匠既不能送老伴到醫院治療以盡他對老伴最后的關愛,老伴也不能安詳地死在床上,與旋匠說點最后告別的話,卻在這寒冷的大雪天里死去,死在一個雪橇上。不幸的旋匠和他的老伴,命運都是悲劇性的。這樣一幅冷峻的畫面充滿的都是凄涼感,只有旋匠一個人看著死去的老伴,摸著老伴冷冰冰的手,聽老伴手落下來像木頭一樣的聲音,一人在那里慟哭,在那里悲傷。
旋匠的人生是悲哀的。當作者描述到旋匠發現老伴已經無聲地病故在雪橇上時,作者不再著力去描述旋匠有多么悲痛多么傷心,而是立即把冷靜的筆調直接指向人物的內心世界:“他想,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過去的多么快啊!他的煩惱剛剛起頭,最后的災害又已經來臨了。他在她死以前,竟不能與她快快樂樂地同居,告訴她他是可憐她的。他還沒有表明心跡,她就死了。
他與她同居的這四十年,這四十年像煙霧一般的過去。只有酗酒、吵鬧和貧窮,簡直沒有人生的樂趣。他剛要可憐他的老妻,偏偏她就死了。”作者保持敘述語調的冷靜,沒有過多的抒情和描寫,卻恰恰做到了為旋匠:“回味和放大已感到的悲痛”。旋匠自從結婚后,整天昏昏沉沉地睡在床上,一直到現在都還不算清醒。他對于婚后的事,一點也不記得,只記得喝酒,醉倒,吵鬧之類的事。四十年的功夫就這樣浪費了。“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進行得多么快啊!他的哀傷還剛剛開始,不料結局就到了。”這是作者從深入探索社會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哲理性的抒情語言,他不同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般意義上的感嘆,它是作家通過對主人公特殊命運的冷靜思考,以嚴峻的語調概括出來的,容易引起我們對人物深深的同情。在旋匠這四十年里,他沒有意識,他回憶不起他有開心,也回憶不起他有憂愁,他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不禁要思考人活著究竟是為了什么?這是個亙古不變的文學主題。我們應該讓生命活得有意義。幸福的時候盡情感受幸福,哀傷的時候全力體味哀傷,試讓生命的每一刻都有存在的意義。旋匠的一生,他什么也沒做,什么意識也沒有,這無疑是哀傷的人生。終于在老伴死了的時候,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恐懼。他的恐懼并不僅僅只是因為老伴的死去,而是因為他日夜喝酒營造出的混混噩噩的日常因此而被打破。他不斷地自言自語,希望盡快不必思考日常的生活。但紊亂的思緒不斷侵蝕他的意識,他最后終于在風雪中放棄了抵抗。最后,旋匠調轉馬頭,準備去下葬妻子。但這個時候他卻生出了一個糊涂可怕的念頭:睡一會兒。他任憑小馬在冰天雪地中本能地前行,自己卻睡著了。最后,這位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愧對妻子,決定要一改前非,重新過生活的旋匠被凍死在風雪中。旋匠是社會中的底層人物,他在自己狹小的圈子里愚鈍麻木,混混噩噩地生活著,沒有意識,沒有情感,最后悄無聲息地結束了一生,像貓狗一樣死去。對旋匠的一生,也暗示了他生活的環境是混混噩噩,毫無生機的。若周圍的生活是生機盎然,有人情味兒,快活的生活,旋匠又怎會不記得這樣的過去?人一生本該有意義的過,記得生命里的悲與苦,歡與樂,可旋匠至死也不記得他悲在哪里,樂在哪里。他懊惱,他悔恨,卻于事無補。在旋匠的身上,彌漫的都是深深的哀傷。不知在他的周圍,有多少個同他一樣的“旋匠”,有多少“旋匠”是混混噩噩地度過這一生。
當然,這與他們生活的時代有關,他們所處的時代是麻木、冷漠,毫無生機的,將他們的理想,快樂,生命的意義都淹沒在那里。19世紀80年代是俄國歷史上極端黑暗的時期,反動勢力十分猖獗,社會氣氛令人窒息。等級制度的確立,使他們的精神受到壓抑,在社會上得不到尊重,喪失了生活的信念和人格尊嚴,正是因為等級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他們的悲慘命運成為必然。黑暗的專制制度,封建思想的禁錮,使“小人物”們心靈深處根本意識不到人性的尊嚴。下層人民只為那一口面包而生存,混混噩噩、毫無意義的在黑暗的社會中掙扎。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缺乏溫暖和愛。
旋匠,就是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小人物,他的命運同普希金《驛站長》中的維林,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窮人》中的杰符什金,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一樣,都是充滿悲劇性的。他們“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勞動者,對社會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們的致命弱點是屈辱退讓,逆來順受,對強者、對黑暗勢力的襲擊或欺凌缺乏自衛能力,因而在時代的風云激蕩、社會上各階級較量的時刻彷徨不前、拿不出行動的力量,聽任命運的擺布而不敢扼住命運的咽喉”。他們活著就為了那一口面包,僅僅只是為了生存,為了活下去。他們沒有精神追求,沒有精神享受,沒有自由的靈魂,只能在黑暗的令人窒息的社會環境里艱難地生存下去。
《哀傷》這篇小說充滿哲理,除了讓人讀后對旋匠格里戈里·彼得羅夫產生深深的憐憫之外,更多的是讓人陷入沉思:人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也許旋匠時代的悲傷在于不能有“自我”的生活,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自我”的時代,我們又都是普通的“小人物”,最大的悲傷可能就是沒有目標,沒有追求!如果你在最能學習的時候選擇玩樂,在最能吃苦的時候選擇安逸,錯過了人生最為難得的學習、積累、用功的經歷,那你的生活也許就像旋匠般憂傷,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現代學院710130
趙群(1986.09-),女,漢族,陜西西安人,學歷:本科,漢語言文學專業,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