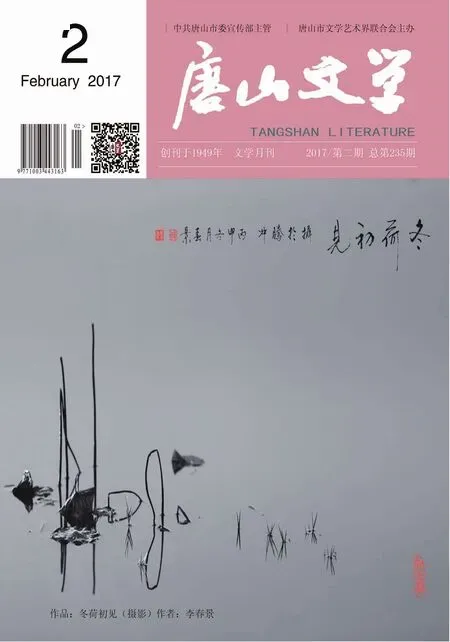論陸機《文賦》所體現的創作理念
郭慶如
論陸機《文賦》所體現的創作理念
郭慶如
西晉時期文學精神總體的特點,表現為傳統政教精神的弱化和對文學創作技巧的重視。陸機作為當時代表性文人,深受文壇上這種風氣的影響,但他“自幼伏膺儒術”,又無法擺脫儒家思想影響,其復雜矛盾的創作思想主要體現在《文賦》一文中。作為一篇創作論,《文賦》中系統論述了關于文學創作的許多問題。
正始時期文人的生活環境危機四伏,政治理想難以實現,連個體的生存都難以保證,社會上彌漫著幻滅感和危機感。建安時期積極昂揚的精神已經消亡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對人生的思考和對個體憂憤的抒發。彼時,儒家思想已經不能再籠絡人心,更關注生命個體的玄學理論成為文士的關注重點,文學服務于儒家思想的道德倫理教化作用逐漸弱化,文人的政治道德觀也越來越淡薄。
時代的文學精神和陸機個人身世共同影響下,催生出了“太康之英”,而陸機的思想及創作又推動了整體文學精神的發展。
作為一篇中國文論史上的重要文章,《文賦》開創了創作論的新模式,并系統而詳細地論述了文學創作的許多問題。
首先自述了《文賦》的創作動機是“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目的在于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從中可以看出陸機對于“盛藻”的重視,以下論述部分可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佇中區以玄覽”到“聊宣之乎斯文”。論述文思的來源,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玄覽萬物;二是頤情志于典墳。玄覽萬物符合感物起興的詩學傳統,頤情志于典墳則強調才學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三墳》、《五典》都是儒家經典,可見陸機心里始終將儒學經典作為文學創作的源泉。
第二部分從“其始也,皆收視反聽”到“郁云起乎翰林”,這部分主要講如何構思及行文。創作主體首先要“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對古今中外世間萬物進行廣泛而普遍的把握,而后“沉辭”“浮藻”才能聯翩而出。這里還強調了“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群言”指的是諸子百家,“六藝”指的是六經,這兩句的意思是要將六經以及諸子百家的言辭都了悟于心,而后可供行文驅遣。謀篇之始,要“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而后行文則有多種方式及形態。這里強調了辭與義的關系,先定“義”,而后“考辭就班”,也突出了對辭采的重視。
第三部分從“體有萬殊”到“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這部分是文體論。之前曹丕《典論·論文》中也曾論述過文體問題,“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把文體從四類擴展到十類,并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觀點,這并不與儒家傳統詩論中的“詩言志”背道而馳,相反,兩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情”和“志”都是指作品內在的思想感情。而各種文體的總體要求則是“禁邪而制放”,這里的“邪”“放”指的是不符合規制的內容。《論語》中有子曰:“詩無邪。”“要辭達而理舉”則與孔子所說“辭達而已矣”一脈相承,但陸機的“詩緣情”目的在于“綺靡”,而非教化衛道,從這一點上來說,又是背離了儒學傳統。
第四部分從“其為物也多姿”到“吾亦濟夫所偉”,這一部分主要論述文章的理想境界,也就是“作文之利害所由”。內容及體制應該多姿多彩,會意尚巧,遣言貴妍,也注意到聲律方面要音聲迭代、五色相宣。這些是從具體方面論述了如何進行文學創作,充分表現出陸機創作理念中重視物象上的豐富多樣、語言上的豐贍華美、聲律上的音韻和諧這些技巧和形式上的問題。而且,“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表明他提倡創新,反對因襲。
最后是第五部分,論述了五種文病,分別是“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以及“雅而不艷”,這五種文病實際上是呈遞進關系的,是在陸機眼中文章好壞的五個層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應”,即文章結構完整;進而要求“和”,即言義的和諧;達到和諧的境界之后就要追求“悲”,文學創作總是以“悲”為美,《詩品》評古詩十九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可見中國古代總是將 “悲”看作文學作品的一種評價標準,只有達到“悲”,才感人至深;感情上做到“意悲而遠”,還要追求“雅”,不能傷于淫侈,品調要雅正;最高追求則是“艷”,“艷”字的本義是“豐大而有色彩”,這里則是指鋪陳及辭采華美。可見陸機對于文學創作最高要求還是要歸于語言美,也就是創作的技巧和形式美。
從《文賦》中可以看出陸機的文學創作思想是矛盾而復雜的,雖然有些脫離儒教傳統,但總體上仍時時露出儒家思想的痕跡。“詩緣情”實際上是對“風騷”確立的詩歌抒情傳統的繼承,而儒家思想所受的沖擊,表現在陸機身上,實際上是他所追求的“志”已經變質了,不再關注民生疾苦,只是單純地追逐奢靡生活、“身名俱泰”,但他自幼學習的圣賢書仍然是他創作的土壤。實際上他既繼承了儒家思想,又拋棄了儒學傳統,在西晉這樣一個復雜紛亂的時代,陸機的創作理念實際上是當時文人矛盾心態的代表。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110000
郭慶如(1993—),女,遼寧大連人。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