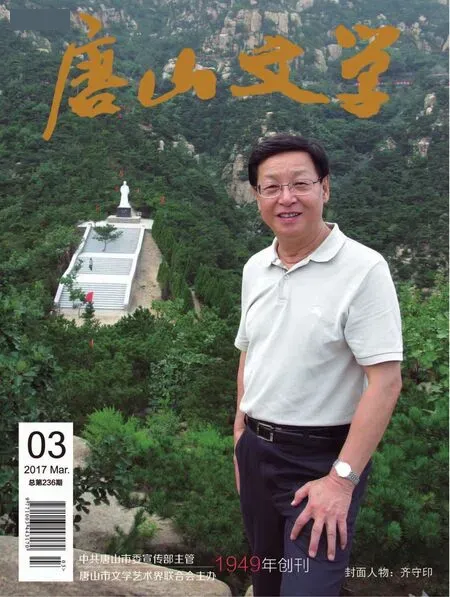散文作家馬硯田
張學新
散文作家馬硯田
張學新
“我用一棵又一棵的文字,在自己所屬的那一角心田凈土,栽植成一片森林,編織著新農村完善的、合理的、科學的、人性的沃野,讓它托舉起心靈的一片心空。”這些語言出自散文作家馬硯田的筆下。多年來,他用自己精心喂養的這一棵棵文字,傾心構筑起屬于自己的那塊文學高地。
我在文學方面是“門外漢”,而真正領我邁入文學門檻的,正是作家馬硯田。幾年前的一天,我拿著幾篇寫好的散文初稿送硯田審正,他認認真真地看過后,從中挑選了兩篇,經過他畫龍點睛的修改,先后發表在《唐山勞動日報》和《開灤日報》上。從那以后,我始終堅持散文創作,至今從未間斷。后來,我見到硯田時,便尊敬地稱他為我的“文學老師”,而他卻象猴子一樣抓耳撓腮地說:“老兄,不敢當,不敢當啊。”
其實,我和硯田是相識20多年的老朋友,又是與我私交甚密的鄉黨。他的人品和文品,他的睿智和才華,我早已耳聞目染,且受益良多,一直對他仰慕有加,是我心中的文學偶像。硯田是享譽冀東大地、渤海之濱的軍旅詩人、散文作家,并被收入《解放軍文藝名人錄》。多年來,他在文學這片熱土上辛勤耕耘,筆耕不輟,先后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詩刊》、《文友》等刊物上發表作品500多篇,近百萬字之多。面對如此顯赫的文學成就,他卻從不張揚,總是低調做人,老實做事,潛心作文。我曾幾次問他,你發表了那么多文學作品,為何不集印成書?你早已具備了會員條件,為何不申請加入省作協和中國作協?而他卻總是淡淡一笑,然后太過謙虛地說:“在文字上,我是拙人。拙,包括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和態度。拙,也是浮淺的一種推脫。而浮淺,是我至今即不成書又不成家的主觀因素。”對此,他還自我解嘲:“無名好,無家好;不為名累,不為線牽。”這,就是馬硯田特有的性格,也是他的作家風骨所在。
人們都說“醫者仁心”,這話沒錯。但“文者仁心”者也不在少數,馬硯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默默無聞,樂于奉獻,為寫作者做嫁衣裳,為成名者當鋪路石,為文學大廈添磚瓦,甘愿把自己當作別人腳下的一粒石子,卻總是無怨無悔。他就象一根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朋友急待出書,請他作序,他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辭。甚至與他素不相識的業余作者找他寫論,也是滿口答應,認真完成。他不僅有一顆純樸的仁者之心,而且還有一顆炙熱的孝子之心。他80多歲的老母因病臥床不起,為了侍奉老人,他拋妻舍子,放棄城市舒適的生活,只身來到鄉下,在簡陋的農舍奔鍋奔灶,求醫熬藥,精心伺候老母長達12年之久,一直到去年老母離世。他這種恪盡孝道的超人之舉,凡熟悉他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有人曾問他,何以如此堅守?他答曰:父母傳承,祖訓家風。
馬硯田在文學創作上嘔心瀝血,歷盡艱辛,精雕細刻,如醉如癡。現在,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夠達到信手拈來、爐火純青的程度,這與他長期的刻苦努力是分不開的。他的散文早已被廣大讀者所認可,所接受,每當《讀樂亭》發表他的作品時,總有不少人為他點贊。他的語言,令人叫絕;他的語境,讓人折服。讀他寫作的散文是一種美的享受,如同品嚐美味的文學大餐。正如著名文學評論家楊立元先生所說:“馬硯田的散文寫得像詩歌一樣精美,他是用詩的語言、詩的意境來寫散文的,因此,他的散文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而形成了散文獨有的審美個性。”比如,在《我的綠地》中,他這樣寫道:“性急的三月,頂著冰凌,就擠進了我的菜園,匆忙地布置著早春的景色。當第一聲翠鳥,來給菜園里的雛菊、豆苗、韭菜問安,這清亮的鳥聲,是春天帶給我們的第一句諾言。自然,對田埂上,那些不請自來的蔓草,我也沒有輕視和疏離,對綠色,我從來不懷敵意。就連抬腳,也是輕輕復輕輕,生怕踩傷了春天的本意。”很顯然,在對綠地的描繪中,他是用詩化的語言來表達的,舒情性、詩意性明顯地體現在他的散文中。但更多的是表現出作家那種對生活對人生的理解和感懷,表現出一種深刻的、完美的理性思維和創意。
馬硯田是農民的兒子,是土生土長的鄉土作家,所以,在他的文學生涯和日常生活中,永遠都不會離開一個“土”字。走土路,睡土炕,說土話,吃土飯,交土友。他秉承家父基因,以土為榮,以土為樂,以土為本,不忘初心。他始終牢記鄉愁,難舍故土,情系親朋,行善積德,圖報知恩。正因為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間散發著濃濃的鄉土氣息,字字句句彌漫著清香的草根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草根作家。
我曾多次向馬硯田討教如何寫好散文的秘訣,他先是一笑了之,然后輕聲甩出一句話:“哪有什么秘訣,只不過是用心寫罷了”。若再問,他便用作家所特有的語言說,散文貴在形散神不散。關鍵是把握好兩個要素:一是要有含蓄、凝練的語言,二是要有鮮活、豐滿的意境,而意境之外就是生活的積累了。我牢牢記住了他說過的話,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
愿散文作家馬硯田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