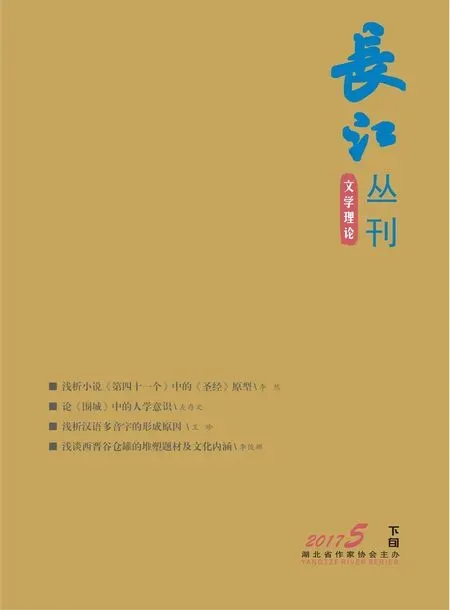淺析小說《第四十一個》中的《圣經》原型
李 然
作品欣賞
淺析小說《第四十一個》中的《圣經》原型
李 然1、2
從原型-批評理論觀點看,小說《第四十一個》具有顯著的《圣經》意象。紅軍女戰士與白匪中尉乘坐的帆船以及海上的風暴是方舟與洪水的隱喻,象征著從失樂園到復樂園的救贖過程。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亞當與夏娃,他們生活的小島的原型是伊甸園。小說結尾二人發生沖突,女戰士將中尉擊斃這一情節則是啟示錄的現代版。
原型 《圣經》 精神分析 基督教
原型-批評是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理論,其理論淵源是榮格的精神分析學說和弗雷澤的人類學理論,該理論方法致力于發現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各種意象、敘事結構和人物類型。該理論認為,神話是最基本的原型,是后世歷代的文學作品的藍本,而《圣經》文本可謂是歐美基督教國家文學的文化基因。《圣經》文本及其宗教哲學思想對西方文學史的影響不言而喻,許多作品的原型正是取自《圣經》。此外,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文學作品中的意象與夢境的形成具有相同的機制。由于作家的潛意識長期受到社會現實及道德倫理的壓抑,只能以扭曲變形的形式表達出來,這就形成了夢境與文學作品。夢有顯義與隱義之分,其中隱義就是隱喻義。因此,將文學作品視為夢境,分析其中的意象的隱喻義是一種精神分析理論方法。
《第四十一個》(Сорок первый)是前蘇聯作家拉甫列涅夫(Б.А.Лавренев,1891—1959)的中篇小說,發表于1924年,講述的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位紅軍女戰士與一名白匪中尉的愛情故事。女戰士瑪琉特卡是一位神槍手,已經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近衛軍中尉戈沃魯赫-奧特洛克是一名俘虜,瑪琉特卡負責看押他。在尋找大部隊的途中,二人漂流到一座荒無人煙的小島上,久而久之產生了跨越階級的愛情。在小說的結尾,一艘白匪的帆船駛進近小島,為了阻止中尉逃跑,瑪琉特卡開槍將其擊斃,她的愛人成為她槍下的第四十一個亡魂。筆者認為,從原型-批評的角度看,小說《第四十一個》的原型見于《圣經》文本,其中的方舟與洪水、亞當與夏娃、伊甸園以及啟示錄意象均十分明顯。本論文擬以精神分析相關理論對小說中出現的這些意象逐一進行分析,證明這些意象與《圣經》中的相關意象具有相同的隱喻義及文化內涵。
一、方舟與洪水意象
小說中,葉甫秀可夫政委帶領二十余名紅軍戰士經過艱苦戰斗,俘虜了白匪中尉戈沃魯赫-奧特洛克,然后打算乘坐一艘帆船渡過咸海,以直達司令部。在渡海過程中,暴風雨驟起。“滾滾的海浪從后面追逐著木船,浪濤又高又黑,像無數蛟龍的脊背,而一張張咝咝吼著的大口正竭力想咬住船舷。”[1]風暴越來越大,“一股旋風似的冰浪呼嘯著從后面撞到船上,把船沖得完全倒向一側。冰浪像沉重的肉凍子似的,從船面上滾滾而過。當帆船恢復平穩時,里面的水幾乎平了船舷。”[1]當帆船漂到一座孤島時,船上只剩下女戰士瑪琉特卡和中尉兩人,其余人都已葬身大海。于是二人在這座孤島上開始了全新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如果把整個小說看作是一個夢幻,二人乘坐小船在驚濤駭浪中前往一座小島,隱喻暫時告別充滿流血與斗爭的世界,遠離世俗的紛擾,從失樂園的狀態進入復樂園的狀態。在此,小船隱喻人類的內心,狂暴的大海象征著一種洗禮,或者是一種救贖的過程。
如果同意以上分析的話,我們就會自然想到,西方文學史中,上述內涵的意象最早見于《圣經》。據《圣經…創世紀》記載,人類原本過著相親相愛的生活,但后來,“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2]耶和華看見人類在地上罪惡很大,決定沖洗掉人間的一切骯臟與污垢。他說,“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毀滅天下。”[2]發洪水前,耶和華告訴諾亞帶上自己的全家,躲進方舟。于是,“洪水泛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從地上漂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漲,方舟在水面上漂來漂去。”[2]洪水過后,世界上的罪惡被清洗干凈,人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據研究,《圣經…舊約》與古代世界尤其是中東、埃及的神話有著淵源關系,而神話多源于原始社會時期巫師的夢幻[3]。如果將《圣經…創世紀》中的大洪水與方舟的故事視為一個夢境的話,這個夢境隱喻人類犯下罪行,后贖罪的過程。自《圣經》誕生以后的兩千年中,西方文藝界不斷地創作出包涵狂暴的大海、大洪水與方舟意象的作品,如近年來的歐美電影中,《后天》、《2012》、《星際穿越》等都含有方舟與洪水意象,這都是文藝創作者建構的關于人類命運的夢幻式隱喻,《第四十一個》中的洪水意象也是如此。
二、亞當與夏娃意象
二人被狂暴的海浪沖到一座小島上后,出現了小說中的另一個關鍵意象,即赤身裸體意象。登島后,二人衣服都被打得濕透,被凍得瑟瑟發抖,于是他們升起篝火,準備取暖并烤干衣服。瑪琉特卡提議脫下衣服,但中尉感到十分難為情。心直口快的瑪琉特卡見狀說道,“人都是肉長的。有多大區別呀!……脫光了吧,你這木頭人!看你冷得牙都咯咯打戰,放機關槍似的。我跟你在一起,簡直是活受罪呦!”[1]于是,二人脫下衣服,“中尉和瑪琉特卡隔火對坐,心滿意足地不斷調轉身子,就著熊熊的篝火烤著。”[1]此時“中尉滿臉通紅,轉過頭來想說點什么。可是他迎面看到的卻是瑪琉特卡圓潤高聳的乳房,乳峰上正晃動著黃色火焰的亮光。”[1]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出發,將這一片段視為夢境來分析可從心理層面揭示其創作的深層機制。弗洛伊德認為,赤身裸體夢源于人類童年期的經歷,每個人在童年期都有在眾人面前光著身子而毫無顧忌的經歷,成年后的赤身裸體夢多是源于潛意識中童年的記憶。童年是絕對美好、單純的,這一時代的突出特點是正是赤身裸體。因此夢境中赤身裸體的意象隱喻人類最為單純,彼此之間毫無猜忌的時期。弗洛伊德還援引《皇帝的新裝》中皇帝赤身裸體在眾人面前展示“新裝”的例子,指出這一童話可視為皇帝的一個夢境,他夢見自己赤身裸體,隱喻他內心有原始純潔的一面。[4]《第四十一個》中,拉甫列涅夫刻畫出的赤身裸體意象隱喻瑪琉特卡與中尉將“人之初”的一面展現出來,同時暗示他們即將成為彼此相愛的戀人。
赤身裸體的意象在《圣經…創世紀》中盡人皆知。亞當和夏娃起初生活在伊甸園里,赤身裸體,但并不以此為恥。后來,他們在蛇的引誘下偷吃了禁果。于是,“他們二人的眼睛就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體,便拿無花果來作葉子,作為自己編作裙子。”[2]《圣經…創世紀》中一男一女赤身裸體的意象隱喻人類單純的童年期。赤身裸體的單純時代,是人類原本應有的面貌,后來人類走向墮落,便成為有罪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夢境中的意象大多與性有關,那么蛇與禁果的意象當是性器官的隱喻。偷吃了禁果后人類不再赤身裸體,意味著人類不再單純,有了罪。《圣經…創世紀》中赤身裸體的亞當與夏娃的意象,其最早版本或許是遠古時期中東某位巫師的性夢。基督教傳入歐洲后,中世紀的教父哲學賦予這一“性夢”以宗教哲學內涵,即人類至善的狀態。因此,《第四十一個》中赤身裸體的一男一女這一意象也并非拉甫列涅夫的“專利”,其原型是《圣經…創世紀》的亞當與夏娃,且二者具有相同的文化內涵。
三、伊甸園意象
二人登島后,發現有一個漁民的房子,里面有足夠的食物與淡水,還有鍋、碗等生活用品。于是,二人開始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彼此互相了解,漸生情愫。瑪琉特卡喜歡聽中尉講故事,于是,每天“黃昏時分,當吝嗇的太陽從微露春意的天際徐徐滑落后,瑪琉特卡就爬到床上自己那個角落,蜷縮在中尉身旁,親熱地依偎在他的肩上,靜靜地聽著。”[1]天長日久,他們忘記了彼此曾是出身不同的階級敵人,逐漸產生了愛情。他們已然忘記了一切,互相依偎在一起。有一次,“瑪琉特卡又一次抬起手來,滿腹柔情地摸弄著中尉的頭發。中尉驚詫地抬起頭來碧藍碧藍的眸子凝視著瑪琉特卡。碧藍的眼睛里流露著一股愛撫之情,徑直沖進了瑪琉特卡的心窩。瑪琉特卡如醉如癡的俯身相就,湊近中尉消瘦的面頰,把自己又干又粗的雙唇緊緊地壓在他沒有刮過的硬胡子茬上。”[1]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原本是互相仇視的敵人,轉眼間變成了難以離分的愛人,在一座小島上過著相親相愛的生活。可以認定,小說中的這一小島正是伊甸園的隱喻。弗洛伊德認為,天堂本身就是人在童年期的一組幻想。[4]小說中的小島是人類集體潛意識中的天堂,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理想。
《圣經…創世紀》中記載,“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出了亞當。后來認為“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2],于是用亞當的一條肋骨造出了一個女人。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于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在一個沒有殺戮與流血的樂園,這就是伊甸園。伊甸園里沒有任何罪惡與紛爭,人們除了相愛再無其他想法。《圣經》中的伊甸園意象可以視為一個白日夢,這個夢境是對美好愛情以及人類大同的向往,是人類童年期的夢想。伊甸園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城,是西方文化中的烏托邦,代表著基督教文明的社會理想。在后來兩千余年的西方文化史中,知識分子不斷地創造出伊甸園意象,《第四十一個》中的小島只是作家創作的另一個伊甸園而已。
四、啟示錄意象
隨著彼此的了解越來越深,二人之間在階級出身、意識形態方面的鴻溝顯現了出來。戈沃魯赫-奧特洛克中尉認為,人類學知識的增長、科學技術的發展并沒有給人類帶來益處。他說:“從前地球年輕,物產豐富,缺乏考察。新發現的國土,無窮的財富具有極大的誘惑力。現在一切全完了。在沒有什么可發現的了。人們類的全部機智都花費在如何保存積累上,千方百計茍且偷生......技術,死板的數字,連被束縛得喪失創造力的思想也一心一意地探討滅絕人類的問題,想辦法消滅更多的人,以便活來的人能更多地填滿他們的肚皮和腰包。”[1]在這里,人類知識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是一種啟示錄的景象。啟示錄是《圣經》中的末世預言,講的是人類受到“獸”的迷惑,忘記了應有的善行,開始互相仇殺。于是一場末世景象降臨了:“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①縱觀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史,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同時,人們紛紛利用高科技研制現今的殺人武器,不斷地彼此殺戮,破壞原有的美好生活。《圣經》中的啟示錄是對人類命運的警示。
關于啟示錄中的末世論意象,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學說來解釋。這種學說認為每個人的身上有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本能,因為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靜。生命由無機物演化而成,人從溫暖、平靜的子宮而來,所以生命一旦開始,一種意欲返回無機狀態的傾向隨之而生,這就是死亡本能的來源。弗洛伊德認為,死亡是生命的終結,是生命的最后穩定狀態,生命只有在這時才不再需要為滿足生理欲望而斗爭。只有在此時,生命不再有焦慮和抑郁,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終目標是死亡。攻擊、破壞、戰爭等一切毀滅行為都是出自死亡本能。當它轉向機體內部時,導致個體的自責,甚至自傷自殺,當它轉向外部世界時,導致對他人的攻擊、仇恨、謀殺等。
在小說中,二人得話越來越不投機,開始激烈的爭論。瑪琉特卡認為,應該進行一場革命,重新分配土地。但中尉痛恨戰爭,痛恨布爾什維克。他反駁:“假如我們現在就埋頭讀書,把土地交給你們全權支配,你們可能鬧到我五代子孫都要哭天撞地血淚橫流哩!不行啊,我的傻丫頭。既然是兩種文化之爭,就只好干到底啦......”原本是相親相愛的人,頃刻之間動起刀槍,這正是《圣經》中的啟示錄場景的隱喻。《圣經》記載,世界末日到來之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憎惡……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②人類原本是單純的、無罪的,但自從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后,此時,人的死亡本能被激活,人類罪惡的歷史就開始了。按照基督教的觀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從第一樁殺人案——該隱殺害亞伯開始,整個人類歷史就是在互相殘殺、互相攻打的歷史。在小說末尾,瑪琉特卡將中尉一槍打死的場景,似乎正應驗了《圣經》中的這一預言。
五、結語
榮格認為,文學作品體現了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一部藝術作品被創造出來后,也就包含著那種可以說是世代相傳的信息。”[5]這種世代相傳的信息就是原型。《第四十一個》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小說,但其中的《圣經》原型十分明顯。究其原因,是基督教文化在俄羅斯的深刻影響。眾所周知,俄羅斯民族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民族之一,俄羅斯文學的根本屬性正是其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盡管小說創作于十月革命勝利后,但仍其固有的基督教背景是難以消除的。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有宗教內涵的文學是偉大的文學。也許正因如此,這部小說至今具有重大的意義與永恒的價值。
注釋:
①圣經[M].圣經…馬太福音.
② 同上.
[1]拉甫列涅夫.第四十一個[M].王庚年,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
[2]圣經[M].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14.
[3]約瑟夫…坎貝爾.千面英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4]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高申春,譯.北京:中華書局,2013.
[5]卡爾…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馮川,蘇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作者單位:1.西安外國語大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空軍工程大學)
本文系西安外國語大學博士后科研課題“自由的隱喻:扎米亞京《我們》的文化闡釋”,合作導師為溫玉霞教授。空軍工程大學博士基金啟動項目“舊禮儀派與俄羅斯近現代思想史”。論文若有舛誤,所產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論文作者本人承擔。
李然(1978-),空軍工程大學講師,俄語語言文學博士,研究方向:俄羅斯語言文化及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