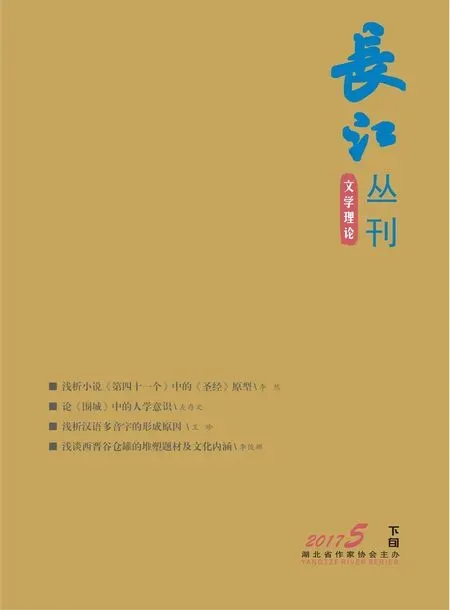韋伯和馬克思現(xiàn)代性理論及其異同
石紅玉
韋伯和馬克思現(xiàn)代性理論及其異同
石紅玉
馬克思和韋伯作為不同時代的社會思想家,對當(dāng)時各自所處的社會均有非常精彩的論述。然而無論是對未來發(fā)展持樂觀態(tài)度的馬克思還是秉持著悲觀態(tài)度的韋伯,都不約而同的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進(jìn)行了政治經(jīng)濟(jì)視角的批判。本文從二者現(xiàn)代性理論的切入點(diǎn)出發(fā),對兩位思想家在關(guān)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軌跡和未來走向上的理論進(jìn)行了梳理和比較,得出二者在理論上的分歧和原因。
現(xiàn)代性 馬克思 異化 韋伯 理性化
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是19世紀(jì)中葉到20世紀(jì)中葉出現(xiàn)在德國的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在他們所屬的時代對社會的解讀和預(yù)測放到當(dāng)下還是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在對現(xiàn)代性的探討上,二者的思想一直是后世的思想家繞不過去的,要么拓展、要么批判,也有綜合二者思想以求在對現(xiàn)代社會的分析中做到完全和完善的學(xué)者。韋伯在現(xiàn)代性問題上有對馬克思的繼承,但更多的是分歧,韋伯以“理性化”吊詭為切入點(diǎn),而馬克思則用“異化”和“物化”來斷言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軌跡,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我們都可以看到當(dāng)時的思想家在對待社會的變化時的謹(jǐn)慎和細(xì)致。
一、對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性的解讀
馬克思和韋伯對現(xiàn)代社會的解讀都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范例的,二者表現(xiàn)出兩種不同的對待資本主義的情緒和取向。馬克思認(rèn)為生產(chǎn)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chǎn)力狀況的變化是引發(fā)整個社會形態(tài)變化的最終決定因素。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資源的私人占有狀況愈加嚴(yán)重,一個階級面對另一個階級的戰(zhàn)爭從未停止,商品拜物教充斥整個社會,生產(chǎn)剩余價值或賺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絕對規(guī)律。這導(dǎo)致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者一切痛苦和不幸的根源”馬克思從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出發(fā),在對資本主義進(jìn)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礎(chǔ)上提出社會形態(tài)必將走向更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chǎn)主義社會是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展望。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人的否定和對剩余價值的絕對追求在馬克思看來是絕對不合理的,他在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運(yùn)行規(guī)律探討的基礎(chǔ)上找出了其中不可避免的矛盾,認(rèn)為資本主義最終會走向滅亡。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xiàn)代社會應(yīng)該是無階級的、資源共享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chǎn)主義社會。
韋伯把現(xiàn)代性特征定義為“祛魅”,即理性化,這也是其現(xiàn)代性理論的總出發(fā)點(diǎn)。韋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jīng)濟(jì)行動的一系列考察,加之對文化價值(宗教)的社會意義的分析,得出現(xiàn)代資本主義是合理化的結(jié)果。韋伯心目中的理性是使一切事情成為可計(jì)算的、具有高效率的、以制度為依據(jù)來實(shí)現(xiàn)的,而資本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存在,它使每個人都成為構(gòu)成社會最基本的原子,這些原子也被禁錮在某個位置上不能輕易改變,社會位置的設(shè)置要大于人的需求,這樣的社會具有高效率和高執(zhí)行力。但這也成為現(xiàn)代社會理性化最大的悖論——韋伯稱之為工具合理性——正是這種禁錮著人們的工具理性使人們難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也意識到這種合理性實(shí)質(zhì)上是非理性的,因此他用“鐵籠”來隱喻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圖景。
二、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
從《哲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手稿》開始,馬克思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進(jìn)行理論批判。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中,馬克思認(rèn)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呈現(xiàn)出其所說的一種“對象化”的扭曲。這時,異化現(xiàn)象就產(chǎn)生了。馬克思主要從四個維度來討論異化的問題:(1)工人無權(quán)處置其生產(chǎn)出來的產(chǎn)品,由于他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都為別人所占有,他自己也就無從受益。(2)工人在工作本身中異化:工作是作為達(dá)成某種目標(biāo)的手段而強(qiáng)制發(fā)生的,并不會使工人產(chǎn)生內(nèi)在的滿足感。(3)既然所有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同時是社會關(guān)系,那么勞動的異化也就必然會帶來直接的社會后果。但這也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際關(guān)系與市場機(jī)制具有了趨同性。(4)人類是生活在一個與自然界交互活動的社會中,人與動物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技術(shù)和文化,但是異化勞動將人類的生產(chǎn)活動降格為一種機(jī)械的適應(yīng)性行為,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征服。這是馬克思早期思想中關(guān)于“異化”的論述。
韋伯從現(xiàn)代社會的“理性化”出發(fā),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是一種形式合理性社會,實(shí)質(zhì)上卻是非理性的。這也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即現(xiàn)代人在經(jīng)濟(jì)行動上以利益(貨幣)為取向的做法是理性的,而價值理性被忽視了,這造就了現(xiàn)代生活中價值取向的非理性。韋伯在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多方面(市場經(jīng)濟(jì)、社會分工、現(xiàn)代企業(yè)和國家以及宗教)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了合理化所帶來的悖論:在現(xiàn)代社會合理化的過程中,統(tǒng)一的世界觀不復(fù)存在,在任何理性的選擇中都充斥著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沖突,且這種沖突是不可調(diào)和的,“價值合理性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是實(shí)質(zhì)非理性的,它們彼此之間處于一種永遠(yuǎn)無法消解的緊張對立關(guān)系之中”在經(jīng)濟(jì)行為上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現(xiàn)代人對貨幣的狂熱追求,這種狂熱使本來屬于達(dá)成某種目的的手段(貨幣),當(dāng)成工具本身來追求,貨幣本來是作為一種交換媒介而存在的,但是現(xiàn)代人卻將其作為終極目標(biāo)來追求,“為賺錢而賺錢”成為現(xiàn)代社會商業(yè)行為的準(zhǔn)則。其他還表現(xiàn)在市場經(jīng)濟(jì)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所存在的沖突,“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場經(jīng)濟(jì)在實(shí)質(zhì)上是非理性的,而在實(shí)質(zhì)上具有合理性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在形式上卻是非理性的。不僅在經(jīng)濟(jì)行為上市場經(jīng)濟(jì)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沖突,而且在政治領(lǐng)域也產(chǎn)生了相應(yīng)的沖突:科層制的吊詭。科層制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行政管理組織具有高效、穩(wěn)定、紀(jì)律嚴(yán)明的特點(diǎn),它摧毀了傳統(tǒng)社會中世襲的特權(quán)與不平等統(tǒng)治,順應(yīng)了民主制發(fā)展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科層制的發(fā)展卻使官員們的權(quán)力得不到限制,反而阻礙了權(quán)力的合理擴(kuò)散,而且科層制中占據(jù)支配地位的形式規(guī)則使每個人被禁錮在其所處的位置上,無法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喜好來行動,所關(guān)心的只有利益,人的自由實(shí)際上被剝奪了。因此,韋伯認(rèn)為現(xiàn)代西方社會理性化一個悖論性的后果是,世界從新教徒暫時居住的異鄉(xiāng)變成了難以逃離的“鐵籠”,暗示了現(xiàn)代社會人雖然相對擺脫了宗教的枷鎖,但又陷入了物質(zhì)的、金錢的羈絆之中,對效率、金錢、商品的崇拜形成了新的拜物教,它對人的限制不僅在身體上,更在靈魂上禁錮人們,使現(xiàn)實(shí)變?yōu)閷?shí)質(zhì)上的非理性。
三、二者現(xiàn)代性理論的異同
馬克思認(rèn)為, 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使機(jī)器大工業(yè)在促進(jìn)生產(chǎn)發(fā)展和人類生活方面的能力得不到應(yīng)有的利用和開發(fā),導(dǎo)致了工人勞動的異化。而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秩序周期性地被破壞明確地意味著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jīng)成為一種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生產(chǎn)形式。韋伯指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逐漸凌駕于“實(shí)質(zhì)理性”或“價值理性”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從經(jīng)濟(jì)行為還是政府組織方面來看,現(xiàn)代社會的形式合理性都超越于實(shí)質(zhì)合理性而存在,這是韋伯所謂的“理性化悖論”,同時他也將現(xiàn)代社會隱喻為一座無法逃離的“鐵籠”,思想和身體都是被禁錮的。這種分析可以說是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從經(jīng)濟(jì)和政治的視角來分析現(xiàn)代社會,同時認(rèn)識到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在運(yùn)行和發(fā)展中的不合理趨勢,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追求利益和只追求利益的價值取向持反對態(tài)度,都清楚認(rèn)識到現(xiàn)代社會對人的桎梏來源于對金錢和商品的追求,這是二者在現(xiàn)代性理論中相同的認(rèn)知。但相同的效果不代表相同的表述和意志,馬克思和韋伯的現(xiàn)代性理論的不同點(diǎn)還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是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界定。韋伯認(rèn)為現(xiàn)代統(tǒng)治的合理性問題是研究現(xiàn)代性問題的出發(fā)點(diǎn),而馬克思卻將現(xiàn)代性問題的解剖放在對勞動異化和資本對勞動的壓榨上面;雖然兩人都把現(xiàn)代性界定為資本主義,但其中的內(nèi)涵卻是大不相同的:馬克思認(rèn)為資本主義體現(xiàn)于不合理的商品崇拜和金錢崇拜,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爭奪使社會成為一個非理性的集合體。在具體的形態(tài)批判上則是從人與勞動的異化入手,對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jì)政治進(jìn)行理性分析,看到了現(xiàn)代資本對勞動的奴役和壓榨,從經(jīng)濟(jì)延伸到政治,證明了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內(nèi)部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并斷言資本主義社會終將被自身內(nèi)部所固有的矛盾而毀滅,取而代之的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在韋伯那里現(xiàn)代性始于傳統(tǒng)的消亡,“祛魅”的過程是將虛無的神現(xiàn)實(shí)化,人們不再信仰那個唯一的神,轉(zhuǎn)而開始接受多元的價值和真理,這是一個“多神論”顯現(xiàn)的過程。資本主義的體現(xiàn)就是在其形式合理性基礎(chǔ)上對現(xiàn)代社會的金錢和效率的追求,但也將每個社會人限制在其位置上,無法按照自己的喜好的信仰來做事,這就是韋伯所謂的“鐵籠”,以強(qiáng)大的控制使社會成為一個合理性系統(tǒng),無法逃離、無法擺脫。可以看出韋伯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一種暗含的批判,工具理性使價值理性受到輕視,進(jìn)而被忽視。二者在現(xiàn)代性內(nèi)涵解釋上的不同直接導(dǎo)致了對現(xiàn)代性反思的不同:韋伯從文化價值的合理性來闡述資本主義的秩序,從制度性的角度來開始現(xiàn)代性的揭示、診斷與批判;馬克思從資本和勞動的關(guān)系入手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關(guān)系的非理性,揭示了在商品、貨幣和資本之間所出現(xiàn)的理性的悖論。而對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預(yù)想這個問題上,兩人的不同是最明顯的。我們可以把這種預(yù)想看作是馬克思和韋伯對現(xiàn)代性的出路的解答。韋伯作為唯名論的代表,將尋求個人尊嚴(yán)當(dāng)作解決現(xiàn)代社會實(shí)質(zhì)非理性的終極辦法,而且現(xiàn)代性作為現(xiàn)代人不可擺脫的“天命”,人們只能是在現(xiàn)代性即合理性之中尋找自我的發(fā)生,換句話說就是要首先拯救人權(quán)。社會越是發(fā)展,合理性悖論帶給人的苦果就越多且越嚴(yán)重,而韋伯認(rèn)為要擺脫這些苦果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不難從韋伯對現(xiàn)代社會的展望中看出一種悲觀的態(tài)度。而馬克思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則具有一種明朗的樂觀態(tài)度:他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運(yùn)行規(guī)律進(jìn)行了嚴(yán)謹(jǐn)而縝密的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內(nèi)部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在種矛盾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的滅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即資本主義的內(nèi)部矛盾會使資產(chǎn)階級成為自己的掘墓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興起是理所當(dāng)然的,是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內(nèi)部矛盾和沖突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二者基于對現(xiàn)代性出路的不同認(rèn)識,最終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不是說馬克思和韋伯的思想就是相互不兼容的,相反,這恰恰說明二者的思想是相互補(bǔ)充和彼此包容的。
四、結(jié)語
在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和韋伯各有各的見地,二者的思想有相容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馬克思一直秉持樂觀態(tài)度,認(rèn)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帶來的是人與勞動的異化,這種異化是資本主義制度悲劇性結(jié)局的根源。而韋伯讀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持另一種看法,他認(rèn)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充滿了形式合理性,實(shí)質(zhì)合理性被忽略了,但形式合理性卻帶來了社會經(jīng)濟(jì)和政治的有秩序運(yùn)行,這是現(xiàn)代理性的悖論。在這種悖論下,韋伯看到的是現(xiàn)代社會像一個“鐵籠”一樣禁錮著人們,人們也被其中暫時的利益推動著而無法擺脫。因此,韋伯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制度持一種悲觀態(tài)度。在對二者現(xiàn)代性理論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過程中,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的斗爭,而對于道路的選擇,不同時代的學(xué)者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與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世界時政背景相關(guān)聯(lián)的。
[1]付瓊.馬克思與韋伯社會沖突思想的比較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03):65~68.
[2]唐愛軍.現(xiàn)代性批判的問題域:韋伯與馬克思[J].理論與現(xiàn)代化,2011(05):11~17.
[3]劉新華,劉欣.試比較馬克思與韋伯關(guān)于資本主義本質(zhì)的思想[J].前沿,2008(03):20~22.
[4]陽勇.馬克斯…韋伯現(xiàn)代性的重構(gòu)[J].遼寧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123~125.
[5]尹樹廣.現(xiàn)代性理論的批判維度及其問題[J].山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15~20.
[6]楊善華,謝立中.西方社會學(xué)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2).
[7]文軍.西方社會學(xué)經(jīng)典命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5).
[8]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xiàn)代社會理論:對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4).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xué)社會發(fā)展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石紅玉(1989-),女,漢族,甘肅瑪曲人,西北師范大學(xué)社會發(fā)展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研究方向:民族社會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