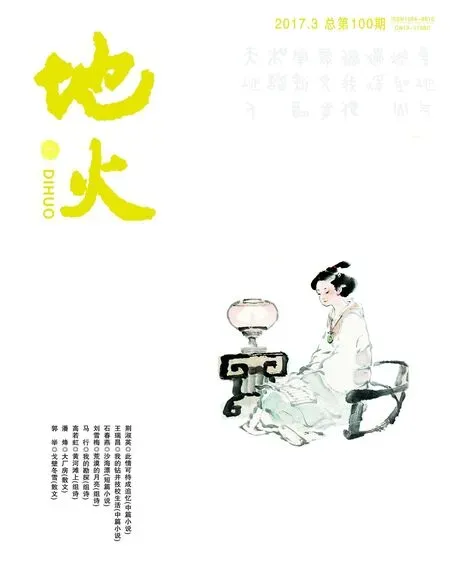趙鈞海寫人散文芻議
■ 張展華
趙鈞海寫人散文芻議
■ 張展華
人是生活的主體,也是各種文學作品主要的反映對象。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寫人是散文的重要任務。人在散文園里徜徉,留下各自的腳印。趙鈞海先生在“人”的最美風景里,在所描繪的人物中,有勤苦慈善的母親,有年高德劭的父親,有功勛卓著的科學家,有農場知青,有身邊同事,有兒時玩伴,家國事,兒女情,無巨無細,盡攬筆下,皆成麗章。熟讀趙鈞海寫人散文會產生許多聯想。
一
顧愷之 《魏晉勝流畫贊》中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散文同樣,寫人是作家最難、最為困惑的活兒。然而,難點和困惑克服之后,就自然顯露出作者的特點。所以,有經驗的作家,正如謝榛所言:“凡構思當于難處用功,艱澀一通,新意迭出。”趙鈞海寫人散文就是 “于難處用功”的。
以 《陪母親逛街》為例。作者的“初衷”是“兒子陪母親逛街”,而其后的“結果”反倒成了“母親陪兒子買書”。這樣的大“反轉”,盡顯“新奇”,其難點也正在這里。質言之,這樣的“大反轉”,是很難做到的,作者必須巧做構想,既散得開,又收得攏,遂使“新意迭出”,沒有功力是不行的。
斗膽認為,文學作品的特點是從難點來的,唯其有難點才有特點,難點在哪里特點就在哪里。對各種文學樣式來說,難點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散文寫作尤其是一種“設難”與“破難”的斗爭過程。
大批評家王國維說:“散文易學而難工。”難工何在?著名學者林非先生這樣作答:一是真實和真誠,因為是留給后代看的,不能說假話;二是難在駕馭一手好的文字。這里所說的“文字”,是指語法修辭和文采,乃至于章法之構思。趙鈞海具有代表性的力作 《陪母親逛街》,之所以廣受贊譽、屢屢獲獎,正由于上述兩點。
這篇散文所記的是一個真實的生活場景,一些真實的細節,作者慈母的一個側面——
在書店里,兒子專注地選書找書,竟忘了母親的存在,而母親卻目不轉睛地關注著眼前的兒子。作為作家的兒子,聚精會神地瀏覽,僅識一個 “王”字的母親卻小心翼翼地為兒子拿書、往家里帶書。兒子眼中的余光發現母親無言的欣慰,母親的欣慰卻引起兒子心中無限的酸楚……
另有,在《享受回家》中又一次寫到母親:做過軍人家屬隊隊長并參加過全師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母親,隨父轉業回鄉后就再也沒有工作了,等他回家探望時,老人家已跟著火車賣了5年冰棍。但,一個在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工作過20多年的老先進工作者 “卻沒有任何埋怨”。
兩文互讀,就依稀可知母親的概況。
《陪母親逛街》一文在選材、構思、表達、行文上的特點,像是“易學”,不就是通過記敘有關的一些事情來表達對所記人物的情感嗎?實則 “難工”,難在材料要真實,而且選哪些材料,如何有特質地進行構思,還有選擇何種色彩的語言來表述。細想起來,作者把握好了一個 “度”:記事不求全、雜,就是寫了一個買書的簡短場景,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選擇。反過來看,如果初看這篇文章題目,很可能以為把陪母親逛街的全過程一并寫了出來,結果則蕪雜無主,不能成佳文。作者正是憑著這種精到的選材,巧妙的構思,疏放靈動的筆致,給讀者留白出足夠寬闊的想象空間,深刻地記住了母親的形象。
再就是,其為文也,不事雕琢,平實自然,真心誠情,筆下的文字正符合兒子說給母親的口吻,這是又一個成功的關鍵。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認為:文學作品,語言最重要。林非教授更認為:作為一個散文家,文字要超過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的文字應是最好的。他還說過,散文是適于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來看的,不同于通俗小說。
二
散文大家李廣田說:“我常想用一種最簡單的方法記述一個人。但是每當我提起筆時,就覺得這是一件難事。起初,我認為我可以用一個故事作中心,來說明這人的性格和行為,但計劃了很久,卻依然構不出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物。”
我對這段話的理解是,李廣田一方面用散文寫人,一方面用散文講散文寫作的 “理論”。人在社會中生活,和周圍的事物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最渺小的人,卻很難說是 “一個沒有故事的人”。不能這么說卻要這么說,唯一的原因是李廣田要用散文寫人。散文寫人,與其他文學作品不同,文學作品如小說,寫人,當然可以 “用一個故事作中心,來說明這人的性格和行為”,但真這樣做了,人也許被寫好了,可是卻完成的是小說,斷送了散文。作為散文作家的李廣田,他要用散文寫人,不屑于羅織故事,并不是因為 “這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散文因了受其特質和篇幅之限,決定了不可能徹底地展開一個人。散文中可以直抒胸臆,批評,贊揚,甚至于詛咒,卻無須完整地集中地講述作品中人物的故事,因而在他的散文文本中,所載之事,毫無曲里拐彎、絮絮叨叨之嫌,都是那么簡練和單純。這一特點,在趙鈞海的寫人散文中同樣得以充分體現,可以說篇篇皆是,無須一一列舉。
散文寫人,必然要寫到事。事是具體的,作者對人物的感受是抽象的,有賴于事的證明和補充。因此,散文寫人的藝術,集中到一點,就是寫事如何從屬于作者的感受的藝術。趙鈞海嫻熟于這種藝術的運用。表現在運用和組織材料的方法上,最大的特點是靈活分散,不以人物生平事跡的客觀順序為順序,而以自己的主觀感受為中心。不受時空限制,凡可用之事,可前置,可后移,可冬來,可夏往。其間的穿插變化,過渡銜接,靈活自然,變化多端。讀趙鈞海的散文,使讀者感到人在他經營的散文園地里徜徉,真是閑散自如到了極點!
由此我想到,散文和小說這兩種不同的寫人文學樣式,各有自身的特點和難點。小說寫人越是曲折復雜越好,而散文寫人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作者的感受直接寫所要寫的人,不像小說那樣作者必須躲在幕后,把自己對人物的感受隱藏起來。這是散文的通則,寫過小說和散文的趙鈞海深諳其理,于是寫出了一篇篇膾炙人口的好散文。
三
親情無疑是最貼心徹骨的感情。如,《蟄伏在舊片上的父親》等篇章中他寫自己的父親:一位參加過解放戰爭,負過傷,立過功,繼而帶兵戍邊的老軍人。轉業后,突發腦血栓,“英雄遲暮”,步履蹣跚,卻始終不渝地堅守著心中的“主旋律”。作者寫道,“多少年我一直試圖寫出一點關于我的父親作為一個革命者革命歷程或者生存經歷的得與失。但每每問及父親時,我都覺得我的設想過于幼稚,過于淺薄,過于蒼白無力。父親抑揚頓挫的講述,常常會蘊含著精深的哲理,總是一次次擊碎我天真爛漫的夢想。”
這種自我解剖,也是側筆的運用,讀后,使人倍感父親的崇高。敘述,是寫人記事散文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現手段。對于親情的表述,在寫人散文中占據著重要部分。誰都熱愛自己的父母,常言道,“叫一聲媽媽,我就淚流滿面。”趙鈞海寫了母親寫父親,寫得都很精彩,簡直可稱為妙筆,讀之使人熱淚盈眶。
說到親情,應是最特殊的抒寫。一般初學寫作的人寫自己的父母親總是帶有褒獎的味道,而趙鈞海寫的親情,不是一味地褒揚自己的親人。他寫父母親則是從一個中年人對雙親的理解這一手法下筆,重在揭示他們的性格特點,發覺雙親那種性格在生命中的存在,而不是刻意評定這種性格的褒貶。他是側重于寫特定時代背景下親人的性格和親人的命運。如寫母親的勤勞、善良、堅韌,不因環境和身份的改變而改變,當年是軍中勞模,回鄉后跟火車賣冰棍。作者的母親十分善良,在 《陪母親逛街》中,對母親的性格以及母親對自己的影響,進行了多方面的敘述,極其感人。如寫軍人父親,即用“我”對父親舊片的印象來鋪展自己的父親情結。在 《父親》一文中,趙鈞海散文藝術的側筆調用很到位,寫得很從容,很細膩,也很動人,把父親不平凡的人生表現得淋漓盡致。——側筆抒寫,可謂其文字語言敘述的一大優勢。
還有白描的運用。趙鈞海的白描語言總能完成對一個個筆下人物的鮮活刻畫。《飛翔在白堊紀的翼龍》是一篇記 “魏氏準噶爾翼龍”的發現者魏景明先生的紀實文字。魏先生有 “中國翼龍之父”的稱號。事業成就之大,是舉世有名的。但大概如老子所倡導的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緣故吧,作者寫道:“魏景明始終過著低調淡泊的普通人的生活。年復一年,魏景明更像一個落魄的舊時秀才,眼鏡上泛著那種寒酸的顫顫巍巍的幽光,身上浮動著的那種內斂矜持的柔和之氣。”還有,“進入市場愈發通暢的21世紀之后,翼龍風箏、翼龍食品、翼龍瀝青、翼龍酒店、翼龍租賃公司、翼龍集團等等,撥弄著那些鮮為人知的銹跡斑斑又撲朔迷離的化石。那化石銹紅銹紅,頗像一堆被遺忘的荒野的排泄物。”——其實,經過作者這樣描寫和對比,科學家魏景明的人格魅力就一下子凸顯出來了。
寫人自然要涉及一個人的優缺點。趙鈞海重友情。發小“劉白毛”和他一起長大,是個淳樸的工人,個人生活中也有一點兒小“不檢點”。在敘寫與劉白毛的友誼的散文中,對其缺點并不正面數說,而是從捎帶的委婉的稍似批判的敘述中得以體現。這種和風細雨的心態并由此而產生的語言風格,只要細細琢磨,類似的地方并不鮮見。
用器物寫意或人體的一部分來借代和寄托對人物的表情達意,是趙鈞海散文的另一特點。寫同事情,如《走路:嫣紅的帽子》中的妻子女友的“帽子”,《凄婉中,一抹玫紅》中小琴凄婉的“玫紅”,作為借代,直接敘述。還有間接敘述的,如,《彼得大帝的手》,借一張魔“手”來記敘和揭發一位殖民者的歷史罪惡。等等。
敘述沉穩,頗具個性,在反映外在事物或內心情感方面具有形象性和抒情性,顯示了趙鈞海扎實的表現功力。
四
明代哲人王陽明說:“作文需大開心目”,若能“放膽下筆,始能縱橫出沒,詞氣條暢”。有經驗的作家說,要使散文空靈與松動,作者必須要處于精神放松的寫作狀態。太緊了,寫不出好散文。讀趙鈞海的寫人散文,我總覺得有一種無意為之,妙手偶得的感覺。我曾就 《陪母親逛街》和作者談過創作經過。他說,和母親發生的事情是完全真實的,從老家歸來,在賓館里只用了兩個鐘頭就基本寫成了。當時只是為了記下那難忘的一瞬,就 “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對于普通人,小人物,也許由于心無顧忌,更無需拔高,無需“貼金”,于是本著真誠,放開去寫,倒造成了一種十分真實而又輕松自然的藝術效果。
要達到這種效果,就必須寫最熟悉的,屬于自己的東西,那些在自己心中揮之不去而且不與別人雷同的東西。
在人們的習慣思維中,都有崇拜 “大人物”的心理定勢。但孰不知在我們生活中存在著許多最為熟悉的 “小人物”,他們不偉大,很平凡,卻都是真人、好人。在他們的身上能發現許多閃光的 “景點”。
說人是最美的風景,倒不如說,身邊的好人,才是最美的風景。然而,怎么樣的人才是好人?這對一些人來說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雷鋒是好人,但他離開我們太久了,郭明義是好人,但他離我們太遠了。好人在哪里?讀了趙鈞海的文章,就會發現好人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是外表平平、職業普通、生活平凡的一群人,但他們卻都有一顆金子般真善美的心。見賢思齊,向他們學習,就可以成為好人。趙鈞海寫人散文的社會意義就在于,點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凝聚正能量,帶動一群人。一群人帶動一群人,就能長成一派郁郁蔥蔥的向善、向上的道德生態。請看以下幾個普通人物——
“玫紅”的小琴,是一個失去右手的殘疾人。她樂觀上進,精明能干,善良清純,漂亮得人見人愛。然而命運一輩子都和她作對。職業不好且不說,克拉瑪依那場災難中失去了9歲的愛子,后來不幸又得了白血病。但她堅韌的秉性卻美麗依舊,就如那“玫紅的手套”,“凄婉”中透著鮮亮。
金梅是“我的”妻子的“閨中好友”。一個公私分明、兢兢業業、堅定硬朗的女職工。是癌癥催她早走了,“她一步一步地走著,嫣紅的帽子在夜燈下反射著熠亮的光,如一盞嫣紅的燈。”她帶著人生的遺憾,帶著她的抗爭,走了。讀后熱淚潸然。
劉白毛是作者幼年好伙伴兒,在油田當運輸工人,當炊事員。后來竟因 “沒結婚就發生關系”而“下放了”,“去遙遠的沙漠輸油泵站了”,“與周邊一個農村女青年結了婚”。他單純善良,忠誠厚道,比那些“心比比干多一竅”的人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他平凡得像一粒沙,卻不卑微;溫暖得如一堆幽火,實在得令人感動,而他本人就是一道風景。
《敦煌》中那個叫敦煌的油田美工,四川苗人,身懷才藝,為油田各種展覽,殫精竭慮,做出貢獻,也走了,是肝病奪走了他42歲的生命,令人扼腕。
還有《尋常人物》之一的《同學吳老二》是“我的”發小、同學。從小一起長大,后又各奔東西,忙著各自的工作,邂逅一逢,俶爾遠去,長相思念。然,突發絕癥,已是晚期。一次“終極會面”,使自己“懊悔莫及”。之二的《朋友歐陽》,是一位寫過《大巴山的孩子——致楊牧》等詩歌的詩人,是自己知根知底的大哥。積勞成疾,頑固失眠。對于病中的歐陽,“我”給與無比的關懷和慰藉。作者寫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雖然不能天天看你,但我會把你裝到心窩窩里——有人想到你,你就成功了。你看,這個世界多么美好啊!”
在作者的寫人散文中,父母、同學、朋友、愛人以及許多和他相識的人,無一例外地都顯露著各自的優點和價值。親情、友情、愛情、同志情、石油情,情溢于海,情滿于山。原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一句話,“只有用勞動創造過美的時候,美才能使人的情操更高尚。”不同方式的勞動,陶冶著情操,創造了和諧,更創造了美麗。人,才是風景中之最美麗者。須知,美化人,贊美人,是極其有益的事。它有助于發展人的創造力,也可以增強自尊心。
贊美人是因為世間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是由好人創造出來的。
五
趙鈞海的寫人散文有著不亞于一般小說寫人的特殊效果。在題材的處理與境界的開拓方面都展示了自己的特點,表現了人性的深度。
劉再復談文學的人性深度時指出:“我們所說的人性深處包括兩層意思:一、寫出人性深處形而上和形而下雙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 ‘人情’的波瀾和各種心理圖景。二、寫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識層次的情感內容。非意識的東西潛伏在人性的深層,它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才會流露出來。”趙鈞海正是通過人的生物層次和社會層次兩個方面來表現人性的善與惡、美與丑的。在 《隱現的疤痕》之 《同學迷華力》中的華力,是作者少時同學。同學間的友情是最純真的,發自內心最深處,無任何功利色彩和利用關系,一起學習一起玩,真的親如兄弟。這里包含了人類最原始最純潔的情誼。“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這種情誼可以保持終生。華力就是一個最重友情的 “同學迷”。所謂形而上者,簡言之,就是內心的不流露于外的思維活動;形而下者,簡言之,就是外在的具體的言談舉止。“非意識的東西”,就是人的本質中原本存在的東西。我們看作者是如何在作品中展現人性深度的——
作品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 “華力熱衷于搜集同學信息”。幾十年了,誰這樣,誰那樣,他都了然于心,津津樂道。為籌辦同學聚會親力親為,精誠之至。同學會上,“少年時的光景復現了,溫馨中帶著眼淚,回溯中飄著純真亢奮,余音裊裊,數年不散。沒有參加的同學都悔斷了腸子。”——這就是發自內心的人的本性。那次聚會,華力被推選為同學會副主席,“但由于這樣那樣的事務,同學會沒有弄成。”后來由于單位改制,取締,華力成了“邊緣人”,“如一個游手好閑的浪子”。然而,如此人生打擊并未使華力消沉,“從未聽說過在寫書”的 “他”,竟編寫了一本關于奧林匹克的資料匯集,而且囑我推銷。——這是他后天經過學習得來的為信仰而奮斗并付諸行動的人生信念,也是發自內心之舉。已出版了一本小說集的“我”,“毫不客氣地說,這類書誰買?”于是堆在辦公室的墻角,任灰塵壓了一層。接著寫我 “……骨子里是不潔的嫉妒”。可是,半年后,那些被我遺忘了的書竟然賣完了,華力還托人給“我”留了一本。“我很內疚,覺得無顏面對華力。”至此,作者調動起自己最擅長的側筆手法,通過描寫、議論、抒情,對比著、反襯著,敘寫華力獨有的高尚人格——
“那大約是1995年。那一年距北京奧運會還有十三年。那時,我根本沒有什么奧運意識或奧運知識,我只是隱隱約約知道,中國已經加入申奧行列。我想,奧運會肯定離我還十分遙遠——我是一個狹隘而低級趣味的人。這就是我一個奧林匹克盲的真實內心,齷齪的內心。其實華力是一個超前的人,一個有著博大愛心的人。華力的奧運意識和奧運夢想要比我早二十年。渺小而卑瑣的我,沒法理解當年的華力……”
華力說話結巴,不善辭令,英年早逝,卻在彌留之際還念叨著同窗好友,不忘初心。我覺得,只有深入通讀全篇,才能感覺到作者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外在美到內在美,把華力這個 “普通人”刻畫得十分光彩而可愛,為讀者奉獻出一連串“人性的波瀾”和各種各樣的“心理圖景”。
趙鈞海的寫人散文,都是對真人真事的記憶和抒情。由此我又想到,形象記憶和感情積累對寫人散文的創作是多么之重要。散文創作,沒有詩情觀念,沒有藝術思想,沒有形象和情感,便沒有藝術靈魂,藝術生命。
散文創作,是在作家的情感支配下驚醒的。情感支配著作家的整個寫作過程,決定著作品的成敗優劣。如果在生活中只注意事件的前后始末,忽視感情體驗,感情積累,到頭來只能是離奇曲折的故事。縱然是情節真真實實,人物有名有姓,但無人物的思想感情,沒有與人物同歡樂,共悲愁,沒有用“心”理解、評價人和事,這樣的作者,充其量只是一個旁觀者、記錄者,因此他也無法在感情的支配下表現生活。感情可以賦予作品以生命,以靈魂,有生命有靈魂有感情的作品才能算作藝術。——我的這段感想是源于熟讀了趙鈞海的寫人散文后而生發的。
我感佩于趙鈞海對人物的形象記憶和感情的投入。
六
陸游八十四歲時給他的兒子陸遹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自古流傳:“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這也可視為放翁先生留給后世的一份文學遺囑。
對于 “詩外功夫”,人們一般的理解是,一個作家作品的優劣高下,其決定因素有三:其一是經驗或曰閱歷;其二是學養、操守、才智等等形而上的東西;其三是身體力行的寫作實踐,徹心透骨的感應以及砥礪淬磨的歷練。關于“其二”,學養可以積累,操守可以浸染,才智可以增進,當然這里并不排除稟賦的與生俱來。但唯物主義者則更強調真知出于實踐。作家能力的獲得,或可簡而言之曰:閱歷、閱讀和磨練。古今中外所有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如此,不勝枚舉,概莫例外。
先說閱歷。趙鈞海出生在一個革命軍人家庭。雖生長在遙遠的邊關,但兵營是無圍墻的大學校,兒時的他,視野并不狹窄。上中學期間他親歷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形形色色。他下過鄉,當過知青,進過農場,當過工人,很早就轉干提職。攝影、繪畫、寫字、歌唱、寫詩、作文,從當報刊通訊員到有影響力的作家,從出版小說集到專攻散文創作,尤以寫人見長——可見其經歷之豐富。不久前因年齡到限,從克拉瑪依市文聯主席位置退下,在文化宣傳領域里一路走來。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因工作緊需,他失去了進高校進修的機會,履歷表上的文化程度一欄迄今赫然填著 “高中”二字。他是我們親眼見到的“自學成才”的鮮活典范。他的成功,再一次證明了陸游的“功夫詩外”說。
再說讀書。說趙鈞海是 “書癡”毫不為過。通讀過他的文章的人所感到的,除了撲面而來的書香之外,再就是他的令人景慕的閱讀海量。在伊犁,他潛研過清代史料,寫成了《古爾圖,那個熄滅的驛站》;面對阿爾泰山,他懷古情幽,寫下了 《唐朝渠:隨風遠去的拓印》;在俄羅斯彼得堡,在冬宮,他目睹了彼得大帝——“青銅騎士”的雕像,寫成了《彼得大帝的手》等等歷史文化散文。在《潛藏在收存的舊書中》,他讀過古詩詞,讀過文史考據,他還讀過國學大師黎錦熙先生的 《新著國語文法》《國語運動史綱》《國語辭典》《漢字新部首》等書,這都是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必讀書,但又是許多學習寫作的人或忽略,或望而卻步,甚至不屑一顧的書。殊不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的載體,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至于眼下的文學書刊,他更是到了手不釋卷的程度。“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然之理也。
古人說:“讀書,為明理也;明理,為做人也。”看來,明理、做人,這才是閱讀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目的。明理做人之后,才能談到作文,才能把文章做好。明理、做人而不作文,并不要緊。但要作文或將文章做好,卻必須明理,必須做人。正因為趙鈞海好讀書、讀好書,所以既會做人,又能識人,才造就了他的寫人散文的新特點,新高度。
后說磨礪。作為作家,只讀不寫不行,只寫不讀也不行。通過閱讀、觀察和體悟,將別人精彩的內容化為己有。“化”,就是消化;消化,就要咀嚼和蠕磨。這說的還是閱讀吸收階段。進入創作階段,就更需要賈島和孟郊的 “苦吟”精神了。賈島作詩曾自敘甘苦:“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孟郊有一首《老恨》:“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床,枕席不解聽。”這句話是他自己說的,其可靠性自然很大。所以說,一篇好作品的產生談何容易。據我所知,趙鈞海的“苦吟”精神大著呢!一篇作品寫好后置于案頭反復推敲琢磨,有時長達數月,未達圓滿絕不示人。有一次,他告訴我又寫成一篇文章,我要試著看,他連說“還不行,還要改”,幾個月過去了,他還在琢磨。艱苦卓絕,玉汝于成。所以正如董立勃所說的,近些年趙鈞海所發表的作品,“篇篇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反響和關注,克拉瑪依好像目前也只有他了。”
七
寫人,是為了給更多的人看,感染人,教育人。考察趙鈞海的散文,觸目的幾乎全是回憶人,敘述人,抒寫人,研究人,欣賞人,“看人”,這幾乎涵蓋了他的全部作品。
在他眼里,每個 “人”都是風景,他不是餐菊的隱士、吐霞的詩人,對人文的興趣大過自然。他關注人的差異與雷同,人的外貌與內心,人的適應與抗爭,熔鑄完美的人格,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使生命的意義得到充分發揮。這是一種多么積極健康的態度呀!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傳誦面很廣,僅以 《陪母親逛街》為例,曾被 《中國實力派美文金典·感恩卷》《中國散文大系·抒情卷》《中外書摘》《散文選刊》《文學譯叢》等48種書刊及媒體轉載和入選,獲中國散文學會 “當代最佳散文創作獎”“全國第六屆冰心散文獎”等獎項。
趙鈞海的寫人散文之所以引人入勝,不僅因為構思精妙,還因為它顯示了作者的審美個性和豐富的美學素養。作者有著對于人的欣賞、鑒別、評判美丑的特殊能力。趙鈞海文章中的勤勞善良的人們為社會釀造著最甜美的生活,詮釋著傳統的美德,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精神,給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啟迪,美的熏陶。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生動形象的、有血有肉的“風景”。而這些,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很值得讀者認識和欣賞。
趙鈞海的許多散文頗具詩味,這不是幾句話能說完的,需仔細體味。在此,我想引用著名散文家、陜西師大侯雁北教授的一段話:“散文,你是怎樣的女神呢?你被詩的姊妹趕出家門,拋棄了她們的外衣,只跳動著一顆詩心;你和詩永遠結緣,不愿離開這個家族。你把人和事藏在幕后,讓作者站出來,隨心隨意地說他們的話。”
近年來,趙鈞海接連出版了包括 《隱現的疤痕》在內的5本散文集。董立勃為《隱現的疤痕》作序,題為《厚積厚發》——文中這樣寫道:“不了解趙鈞海的人,看到他這個樣子,可能會多少有點搞不明白,想不通怎么突然冒出來的他,怎么這么厲害。不過,在我看來,他一下子能寫出這么多,并不會覺得奇怪。每個人一輩子能寫多少東西,是命中注定的。鈞海十幾年沒有寫,不是沒有東西寫,是沒有時間寫。現在有了機會,那些多年積累的生活素材,那些一直不能忘記的事情,不用再壓著了,藏著了,憋著了。想寫的東西,像水一樣全蓄到了水庫里,現在提起來閘門,水就馬上像大河一樣奔涌了出來。”——對此,我們熱切地期待著。
期待中,我們最想看到作者今后多創作一些更令讀者喜聞樂見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作者的中、短篇散文寫得很好,如代表作《陪母親逛街》等。固然當前一些刊物,對長篇散文情有獨鐘,但忙碌的上班族還是愛看能在報上發表的1500字以內的短散文和3000字左右的中篇散文中的較短者。如,魯迅的《一件小事》、賈平凹的《丑石》《我的小桃樹》等不太長的、不太張揚的一些文字,深深地刻在讀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