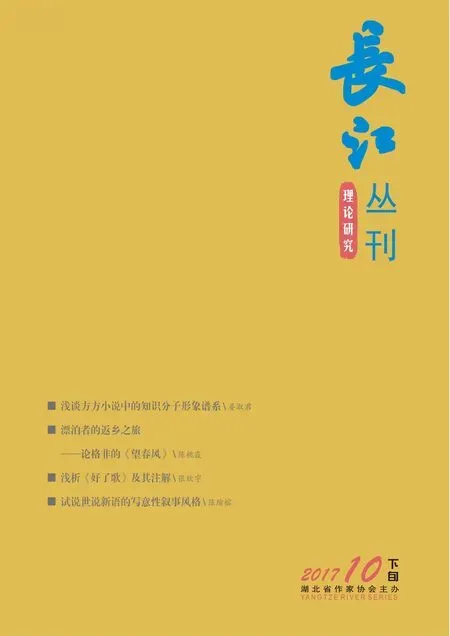法律解釋客觀性之考究
——有感于《法學方法論》
孫宇翔
法律解釋客觀性之考究
——有感于《法學方法論》
孫宇翔
法學方法論是貫穿于理論與實踐間的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的存在。其中提倡的不拘泥于法律概念、邏輯推理的機械適用而發揮法官在辦案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挪活”法律規范深深地影響著一代人的法學思維。
自從拜讀楊老先生的《法學方法論》以來,深深沉醉于他關乎法律解釋客觀性的真知灼見,閱讀中在佩服其法學思維廣度、深度之大的同時,對于法律解釋客觀性的考量有一些自己的觀點,在現實生活中法學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交叉運用邏輯分析方法和經驗事實驗證方法來尋求法律解釋之客觀性,但往往難以避免的會融入一些主觀因素。本文著重論述如何在多種法律解釋方法下尋求一條合乎法律解釋客觀性的道路,才疏學淺,不周之處還望原諒。
法學方法論 法律解釋 客觀性 邏輯分析
當拿到楊老先生的《法學方法論》一書時,“什么是法學方法論?”“法學方法和法學方法論之間有何種關系?”諸如此類之問題涌上心頭。研習之下,發現其深度廣度并非一遍所能通透,帶著自己的一些小小問題,又經歷了痛并快樂著的漫長讀書歷程。重讀之后,收益頗豐。
在《法學方法論》這本書中楊老先生給我們介紹了事實認識之客觀性,邏輯推導印證了法學認識也具有客觀性,在實踐論方面提出法律解釋之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客觀性[1]。在法官看來,適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映射出不同法官的價值評判標準,單就此方面來看,價值判斷的客觀性與法律解釋之客觀性存在互通面。而在實踐操作下,法官隱隱之中受限于各種方法之約束,更由于有各種法源之框架存在,進而加大了價值判斷漸趨客觀的難度。在卡多佐先生的《論司法過程的性質》中也提到了法官解釋時會有一些重大的影響因素——潛意識因素的存在,諸如內心信仰、不同喜好、心情好壞、不同出生,不同教育背景以及不同價值觀念等都有可能影響法律解釋、價值判斷的結果使之偏離客觀性的方向[2]。
筆者認為這些是無從避免的,從眾人出生之時這個社會就不存在圣人一說,現實的生存狀態之下會有諸多的影響因素在我們潛意識里形成一個觀念與價值的判斷體系,在遇到不同的情況下我們的第一反應是一種潛意識里的對號入座,雖然我們不想發生這個過程但是這無從避免,所以沒有絕對的客觀性正如沒有一個一塵不染的圣人一樣。那么怎樣從紛繁的影響因素中保持一個相對而言客觀中立的價值判斷與法律解釋呢?
從狹義的法律解釋方面來說,這點做到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說在既定的法律條文限制下要做到法律解釋謹遵客觀性之道路還是不難的,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法律解釋的方法,諸如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擴張解釋、限縮解釋、目的解釋、等等。法官只要在這個過程中遵照合適的法律解釋的方法,一般而言都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而在實踐當中,這部分爭議也不是最大的。
對于價值補充和漏洞填補方面如何保證法律解釋之客觀性這部分是有所爭議的。在歐美法系國家,因為判例法體系的法律傳統以及支持法官造法環節的存在,在漏洞補充方面法官有較為體系化的經驗方法,卡多佐法官把這個過程稱為“司法過程的最高境界”。這就要求在法官做出漏洞補充時,需要考量多方因素衡量多方利益,本持著一個客觀中立的立場去做出一些價值判斷,他們認為法律所要實現的正義是受制于社會福利終極目標指導之下的。因此如果遇到多方價值沖突的情況下,需要按照價值位階原則進行衡量比較,再通過哲學的方法也就是邏輯三段論的演繹推導或者借鑒習慣的思想因素作為判決結果以上升為新的判例。
在漏洞補充上確保法律解釋客觀性的手法主要是類比推理、目的性限縮(擴張)、創造性補充三種。類推適用是基于平等原則之理念,而普遍為法院所使用,“相類似之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的法理,為類推適用之基本原理。目的性限縮與目的性擴張在楊老先生看來是不可或缺的保證法律解釋客觀性的手法之一,前文中也論述過,法律解釋的目的往往在于確保司法與立法之目的性相符合,而解釋過程中,需要保證解釋結果的“合理性”,確保合理性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并且不會違背立法之目的,那么這個結果相對而言就是客觀的存在。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在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指導,在法律解釋上更多的不是在漏洞填補方面,而更多的是停留在狹義的法律解釋和價值補充上,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法官造法的法律傳統或者司法實踐,更多的法律解釋是在狹義的層面上完成亦或是上升一個層次,在價值補充的層面上完成,這兩部分的法律解釋如何保證客觀性就成為了關鍵所在。楊仁壽先生在《法學方法論》中提到,不管法善惡與否,法官都不可以拒絕適用,而是要在一定立法目的考量的基礎之下,通過一定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去解釋合乎立法目的意思。
[1]楊仁壽.法學方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2][美]本杰明·內森·卡多佐.論司法過程的性質[M].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中央民族大學)
孫宇翔(1993-),男,漢族,安徽宿州人,碩士,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