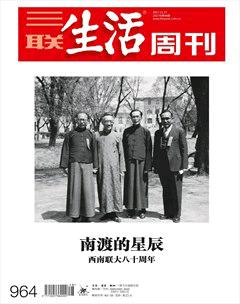莫言:在深海里響亮沉重地呼吸(6)
2017-11-25 15:27:50朱偉
三聯生活周刊
2017年48期
關鍵詞:小說
朱偉
《酒國》是莫言的第三部長篇,從1989年那個多事之秋后,拖了兩年才寫完。這不是莫言唯一一部非一氣呵成的長篇,他自己的說法,《蛙》也是寫了幾萬字就放下,然后另起爐灶再寫成的。優秀作家的預知力真是了不得。我記得1997年《三聯生活周刊》才做了一期《酒神瘋了》的封面故事,說山東瘋狂的釀酒業;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個億》,深度報道全國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說,莫言在90年代初就銳利地割到了十年后才讓我們都感觸到的黑色腫瘤。更令人驚奇的是,小說中種種五花八門的吃法,被象征為侏儒的“余一尺”與各種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被披露的貪官丑聞。這叫什么樣的批判現實主義呢?——我感覺是,莫言寫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用極其鋒利的手段,提前撕開了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很難用概念對他的創作形態作一個歸結。我只能說,莫言的批判現實主義超越了以往我們熟悉的概念,說它“魔幻”其實不準確,因為他只不過習慣了夸張,令你感覺到荒誕。他憎惡分明,嫉惡如仇,他的心在流血,他超脫不了,冷酷不了,刻骨著嬉笑怒罵,心卻是軟的,暖的,多情的。這強烈的愛憎、冷暖交織的態度,爆發出奪目的,令人震撼的色彩迸濺。
如他自己所說,這部小說的構思,其實只因一篇隨意讀到的文章《我曾是個陪酒員》而產生的觸動。牛的是它的套裝結構——外面包的故事是由小說中人物“莫言”,根據“酒國釀造學院勾兌專業”博士“李一斗”寄給他的小說,產生靈感而創作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