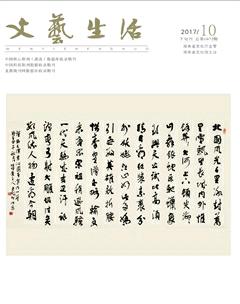文化包容在二十世紀現代藝術中的表現
劉金儒
摘 要:我們的文明,應當屬于人類文明,是一個整體文明,因此,文化包容就顯得很重要,本文對文化包容在二十世紀現代藝術中的表現進行討論。
關鍵詞:文明沖突;中國禪宗;現代藝術;文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30-0264-01
泰勒-考思在《創(chuàng)造性破壞》一書中分析到,在當今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像孫悟空一樣一下子從石頭中蹦出來的,泰勒說:“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之上的,即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國際交易基礎之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的主要人口和語言來自歐洲,西方文化哲學繼承古希臘的哲學傳統,宗教傳自中東,則科學基礎來源于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泰勒的理論至少可以說明一點,西方文明有相當一部分是借鑒于中華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在大洋西岸的開花結果。
一、中國禪宗對美國現代藝術的影響
美國現代藝術有繼續(xù)沿歐洲現代藝術發(fā)展的抽象表現主義、精確派藝術、大色域等扔保留繪畫和雕塑風格的藝術,也有新世紀新視覺語言的表演藝術、環(huán)境藝術等,但是好在藝術歷史學家和藝術評論家們都注意到了一個事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藝術的方向得益于兩個人的影響,一個是杜尚,顛覆了西方藝術觀念的藝術家,一個是音樂家約翰-凱琪,雖說凱琪不是畫家,但他對美國藝術界的影響卻相當重要,特別是60年代的藝術創(chuàng)作方式都得益于凱琪的影響,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凱琪的思想完全來自于中國的禪宗,這種文化現象頗值得我們研究。
禪宗是在二十世紀初由一個名叫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師傳入美國的,鈴木大拙精通佛理,對禪宗具有超高的研究熱情,在他青年時代就進入寺院學禪,在禪寺八年時間與世隔絕,徹悟禪的真義,并于十九世紀末由宗演禪師推薦到達美國,與當時的美國學者共同翻譯老子的《道德經》和佛教經典,在禪宗的這個題目上他稱得上是西方的第一位老師。
鈴木大拙對凱琪的影響巨大,凱琪自己稱:“鈴木大拙的思想幫我建立了一種無分別心、順其自然的觀念,對我的藝術觀與人生觀有了重大的貢獻,之后我把這種觀念融入到我的音樂中,就是這種創(chuàng)新,改革了西方音樂,也改革了藝術和生活的位置,讓藝術等于生活甚至高于生活”。
這種藝術等于生活的思想被西方民主社會所接受,并以這種意識為主導勞申伯格和約翰斯發(fā)展了波普藝術,使美國的藝術從六十年代的抽象表現主義轉向了以生活為題材的具象藝術,抹煞了生活與藝術的界限,五十年代后期,卡普洛受凱琪的影響創(chuàng)造了偶發(fā)藝術,倡導讓藝術創(chuàng)作擴展到行為和環(huán)境中去,使人們重視生活,活得充滿創(chuàng)意,隨后卡普洛在拉特格斯大學任教,在這期間又把他的思想傳給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弟子中許多人成為了六七十年代美國先鋒派的中流砥柱,從偶發(fā)藝術衍生出的行為藝術、環(huán)境藝術、表演藝術等構成了美國現代藝術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
凱琪源自于中國禪宗的思想成為了美國后現代藝術的發(fā)展源泉,可見西方并沒有抵御外來文化,而是選擇了包容,包容外來文化創(chuàng)造新的文明。
二、為文明而擔責
之前在鳳凰網上看到一則新聞,原標題是:“文化包容就是一種文化自信”。對于這一點我不以為然。中國文化因自強不息,代代相傳,因厚德載物,發(fā)展壯大,中國文化本身是很包容的,走向世界也是相當的自信。不包容的只不過是這群“文化人”罷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出現過這么一個行為藝術:“藝術家”把畫廊改造成一個“豬圈”,豬圈四周有二百多名觀眾,正在觀看一只身上寫有英文字母的公豬強奸一只寫有中國漢字的母豬,其寓意就是文化“入侵”這一命題。在此的一切行為和文化象征都只不過是藝術家們的一廂情愿,他們用隱喻的手法將文明沖突走向極端。
如果我們不帶有色眼鏡去看待人類文明的話,它們之間相處的還是非常和諧的,比如汽車牌號,算得上是融合了世界幾大文明的經典范例了,首先開頭的中文漢字“京滬遼黑”等,屬于中華文明代表東方,英文字母“ABCDE”等來自大洋西岸應屬西方,阿拉伯數字“12345”等,來自印度和伊斯蘭文明,屬于中東,它們之間相處的不是很和諧嗎?如果沒有“文化人”們去挑撥它們,它們就會相安無事并和睦相處。
無論是西方文明,還是東方傳統,它們既關乎國家,也關乎個人更關乎全人類,需要每一個人為人類文明而擔責,繼承傳統以連接過去,包容外來文化去面向未來。
古往今來東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例子比比皆是,充分說明了人類的文明只有一個,即人類文明,中國傳統也好西方文明也罷,只不過是整體中的支流,非要說沖突那也是人狹隘格局所造成的不文明沖突,就好比切西瓜一樣,一分為二,如果真有“文明沖突”那也是發(fā)生在西瓜與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間,因為詛咒人類命運的只有人類本身。
文章結尾,我想借用熊培云先生的一句話:“人世間最真實而永恒的沖突只在人的生與死之間,而絕不是文明之間”。
參考文獻:
[1]鈴木大拙,佛洛姆.禪與心理分析[M].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2] Mary Lynn Kotz.勞申伯格–藝術和生活[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