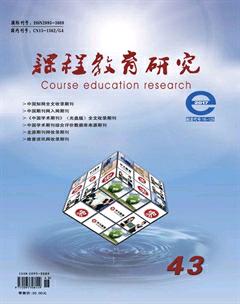唐詩宋詞中雨的描寫藝術
洪菊芬
【摘要】雨作為詩人傳達情感的途徑,成為了極為雅致的人生意境。在文學海洋中的細雨綿綿,成為呈現在詩人內心的恬淡和愜意。詩人的內心沉浸于細雨中,展現出脫離喧囂的崇高和詩意。
【關鍵詞】唐詩宋詞 雨 描寫 藝術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43-0101-02
在中國古典詩詞中,通過無數意象打造的藝術,特別對于唐詩宋詞的高峰時期,成為詩詞描繪最為鼎盛的階段。對于唐詩宋詞的意象中,讓人描繪不盡的則為“雨”的意象。詩詞意象的結合,通常通過情感的銜接融合而成。在創作當中涌現出來的意象較為凌亂,不具備章法,不具備活力,應當通過情趣給予感化,才可以令其更加鮮活,具備完整的形象。所以,使人們通過情感將雨的意象和其他意象相融合,打造成具備生命的良好形象,從而追尋各類特殊的藝術傳達效應。
一、傳達情意
意象需要通過物象給予表達,物象在詩人的審美經驗選擇后,符合詩人的審美理念及情趣,并且通過詩人思想情感的融合與感化,融入人格及趣味,從而滲透到文學作品中變成意象。在意象中融入了主觀情意的物象,或者是通過客觀物象體現的主觀情意。因此,詩詞中的雨,已經不只是自然現象,還是通過表達主觀情感與意趣的一個符號。崔道融在《溪上遇雨》中寫道:“坐看黑云銜猛雨,噴灑山前此獨晴。忽驚云雨在頭上,卻是山前晚照明。”展現出既歡喜又驚訝的情緒,真正體會到夏雨的樂趣所在。蘇軾分別在《望湖樓醉書》以及《有美堂暴雨》中瀟灑自如地描繪出暴雨的態勢:“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然而陸游則在《南定樓遇雨》中寫出觀暴雨的心情:“風雨縱橫亂入樓”,令人身處在狂風暴雨中深感凄迷。如果是綿綿細雨,則會是另一番心境。宋代的劉敞說過這樣一句:“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比如寒雨一詞傳達的是內心的寒寂,王昌齡在《芙蓉樓送辛漸》中:“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天孤。”愁雨一詞傳達的是看雨時表露的愁思,例如周邦彥在《瑣窗寒》中寫道:“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亂雨一詞體現著情思的紛繁,在周邦彥的《憶舊游》中這樣描述:“墜葉驚離思,聽寒螀夜泣,亂雨瀟瀟。”好雨一詞充滿著春天的喜悅,例如在杜甫的《春夜喜雨》中描繪:“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而暖雨則體現出情懷的慵懶,則能夠通過李清照的《鷓鴣天》所體現:“暖雨清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
充滿藝術性的雨的意象,均可以通過客觀的“象”表達主觀的“意”在何景明的《與李空同論詩書》談論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視“意”和“象”區間具有是否契合的關聯,或相關相合。“合”則為詩歌想要表述的主觀情意與這一情意給予展現的客觀物象相互間的統一和諧。不然,則是脫離了意和象的結合。因此,詩人們在打造“雨”的意象時,大多處在意和象的結合而不趨向疏離,也就是追尋通過雨“象”有效地表述雨“意”,比如張孝祥在《滿江紅·聽雨》中寫出:斗帳高眠,寒窗靜,瀟瀟雨意。南樓近,更移三鼓,漏傳一水。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里。也不管,滴破故鄉心,愁人耳。
寧靜的夜晚,寒窗雨聲激發出詞人對家鄉濃濃的思念,而家鄉和州已經淪陷,變成兵戈搶奪之地,所以雨聲不斷敲打人的內心,令人心碎。這思鄉之情飽含著沉痛的亡國之痛,令這首詞實現了主、客觀融合,“雨意”透過雨象獲得了深刻的表達。唐宋詞中的“雨”意象,屬于一種心靈化、主觀化的感性狀態,其身為詩人的主觀情感以及審美想象的介質,表達出的正是詩人在主觀方面的內心。
杜甫在《大雨》的“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及曾幾在《蘇秀道中》的“不愁屋漏床床濕,且喜溪流岸岸深。”均傳達出作者為了百姓的利益不顧自己的崇高品德。陳與義的《觀雨》中“不限屋漏無干處,正要群龍洗甲兵”通過相同的心境傳達出抵抗金人,期盼獲勝的心情。可是如果久下不停,詩人則會迸發出無法抑制的憤怒,比如在杜甫的《九日寄岑參》中寫道:“安得誅云師,疇能補天漏。”唐代李約的《觀祈雨》則充滿了諷刺的意味:“桑條無葉柳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透過這兩個迥異的心態進行對比,批判了任意玩樂,罔顧黎明百姓死活的統治階級,跌宕曲折,意味深長[1]。
二、烘托氛圍
為了規避正面描寫的直露,通過“雨”的意象打造一種氛圍而進行烘托,從而實現含蓄且不張揚的藝術成效,屬于唐詩中普遍運用的一個抒情方式。在許渾的《謝亭送別》中寫道:“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城風雨下西樓。”在這首詩中,并未寫“愁”字,卻通過漫天風雨襯托出送別的氣氛,自行傳達出神傷之愁。
通過“雨”展現出凄冷的氣氛,從而展現出輾轉反側的離愁,莫過于描繪靜夜的“雨”聲。在夜幕降臨后,雨在視覺方面的形象逐漸退去,人們反而在聽覺方面更加敏銳,在聽覺方面更加敏銳,而雨聲則極為具備穿透力,能夠直擊深夜未眠中人的內心,形成悲凄的情感氛圍。為了追尋夜雨更為了然的聲響效果,古代詩人通常通過梧桐樹葉描寫雨聲,比如在晚唐中溫庭筠的《更漏子》中寫出:“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通過三更時分的梧桐冷雨中的一葉葉、一聲聲而傳達出閨中女子的哀愁之情。溫庭筠的詞,將“梧桐雨聲”變成特定的意象,不斷出現在之后的宋詞創作中,從個體的意象變為公共的意象,具備展現離愁情懷的特殊色彩。比如在張輯的《疏簾淡月》中描繪的:“梧桐雨細,漸滴作秋聲,被風驚碎。”李清照在《聲聲慢》中寫道:“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可是到了宋曾幾的聽覺中則為“五更桐葉更佳音”。又比如李義山在《宿駱氏亭寄崔雍崔袞》中寫道:“留得殘荷聽雨聲”,猶如讓人體會到雨打殘荷、有條不紊、極具情韻之感。周紫芝在《鷓鴣天》中這樣描述:“梧桐葉上三更雨,葉葉聲聲是別離。”這些隨時在冷風中經受吹打的梧桐葉,與雨聲、夜晚、相思愁客融匯在一起,令人無法安眠,更增添了一絲煩憂[2]。endprint
三、飽含韻味之雨
1.喜雨
喜雨通常和滋潤萬物、煥發生機相結合。喜雨詩大多鮮明歡快,體現出生命的期盼。比如在韓愈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寫出:“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在天街中的細雨滋潤如酥,隔著雨絲望向草色,猶如一片十分淺淡的青色。透過它,讓人們看到了歡快、清香、生命、喜悅。對于喜雨的詩流傳最廣的則為杜甫的《春夜喜雨》,其中寫道:“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好雨知曉人意,當大地需要雨時,它降臨了,在寂靜的夜晚,安靜地、緩緩地下著,輕柔地滲透到大地中,化成生命的光芒。雨不但是春雨,還是好雨,其了解人意,能夠感受到人的內心。詩中雖然未寫出“喜”字,可是卻充滿了喜意。
2.苦雨
苦雨通常與悲、怨、愁相融合。季節大多為春和秋兩個季節,時間大多為黃昏和夜晚。綿綿的春雨,霏霏的秋雨。在無數的落紅、春去匆匆、夜深人靜中,雨猶如了解人的情感一般,點滴降落,也聲聲扣人心弦。詩人感慨萬千,淚水和哀愁一同涌現,在讀的過程中讓人肝腸寸斷。比如在李煜的《浪淘沙》當中:“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春雨曉寒道盡了李煜作為臣虜的悲凄境地,滿懷悲情意在言外。
3.雅雨
中國文人不但有推崇喜雨的情感表述所需,還有的文人推崇雅致人生的意境。在文學當中的細雨,是展現在詩人深情中的恬淡與舒適。詩人的內心通過細雨的浸染,展現出世外桃源的典雅與寧靜。比如在韋應物的《滁州西澗》中寫道:“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在山澗簇生著的美麗的芳草,在叢林中悠然鳴叫的黃鸝鳥。在夜幕降臨時,春雨落下,潮水暴急,野渡無人,孤舟自橫,只有茫然。通過詩人對野生自然之物的喜愛與欣賞,展現出文雅瀟灑的人生觀,讓人傾心。
4.禪雨
雨洗禮的是空間世界,也屬于人內心的世界。詩人通過雨水的清涼沖洗了權利與欲望,詩人通過雨沉淀自己,感悟人生,以此感受雨的禪家韻味。生命和宇宙相融合,所有均為隨緣,自然舒適,恬淡深遠,充滿生機,將空與靈相融合。比如在蘇軾的《定風波》中:“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仗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詩人被貶到黃州,通過途中遇到的雨抒發出不平常的人生哲理。不論作為自然界的陰晴風雨,還是實際人生的榮辱起伏,均可以平淡看待,無需在意。此處正是通過雨的實際意象把人生融入到忘記得失、超然脫俗的禪意當中。唐詩宋詞的雨屬于詩人在主觀情意和客觀物象中的結合體,其蘊含了充足的人生意蘊。雨中飽含著歡喜、凄涼、雅致、禪意[3]。
總而言之,在唐詩宋詞中具有諸多描繪雨的詩句,通過雨打造意境,表達情意,展現氣氛,感受人生百態。其不但在內容上極為豐富深遠,還極為感人,藝術方法尤為多元化,令人回味悠長,讓人們去欣賞,去感受,從而體會迎面而來的人文氣韻。
參考文獻:
[1]劉磊.類選詳析 深入淺出——評劉懷榮等著《唐詩宋詞名篇導讀》[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1):93.
[2]田小勇.唐詩宋詞聽秋雨[J].審計月刊.2011.(10):51.
[3]孫文輝.《雨巷》教學的詩歌史意識[J].名作欣賞.2010.(13):56-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