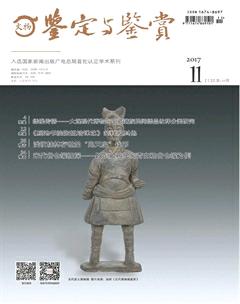關于遼代翰魯朵的看法
趙運富
【摘 要】本文主要講述了1980年于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蘇木烏蘇圖山前,遼碑一通,碑文的內容表述了遼代翰魯朵的有關事情以及人名和寨名等問題。
【關鍵詞】遼代 碑文 翰魯朵 人名 寨名
1980年于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蘇木烏蘇圖山前,遼碑一通,碑已殘破,碑額僅存27字,碑身四周也殘缺不全。碑兩面均刻有文字,向上的一面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不能辨認。向下的一面文字清晰,全系漢文,楷書,字體工整,內容都是人名,在人名中列有莊寨等地名。文字從上到下分為四段,段與段之間留有間隔。每段行數和字數不等,第一段共37行653字;第二段共30行682字;第三段43行736字;第四段44行721字。從文字內容看,段與段之間并無含義上的區別。人名中有男有女,有夫妻、父子、祖孫、兄弟同列者。有僧尼、殿直、督監、校尉等官職,多數是漢人,間有少數契丹人。除州、莊、寨等地名外,還有反映社會分工和職能意義的名稱,如六院司、八作司、窯坊寨、教房寨、糧谷務、柳作務、南灰寨、上、下麥務、上、下后妃寨、菓園寨等。碑額殘文中有“崇善”“跡長存”“不其偉歟”等字,或許是為了某種善舉而樹立的。這一點無關緊要,而碑文本身卻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生產、生活、社會結構、被俘漢人的身份地位等許多問題,是遼代封建性質莊園的一個縮影,是研究遼代社會經濟史上少有的珍貴資料。
從碑文中反映出來的情況,完全可以肯定是一個規模很大的莊園。它不同于遼代盛行的頭下城,碑中有上、下后妃寨、教坊寨、六院司等可證。而且這碑的所在地西北方向距遼代慶洲約25千米,東距遼代有名黑山上的天池約10千米,位于黑山的南麓。東距遼上京也不過75千米,屬于遼內地的中心地帶。地點如此重要,所列姓氏如此眾多,莊寨規模又如此齊全,應該是某個帝王的翰魯朵是毫無疑問的。如前所述立碑的年代是道宗時期,當然這個翰魯朵就是道宗的阿斯翰魯朵即太和宮。按《遼史·營衛志》載:“阿斯翰魯朵,道宗置。是為太和宮。寬大曰“阿思”。以諸斡魯朵御前承應人及興中府戶置。其斡魯朵在好水濼,陵寢在上京慶州。正戶一萬,蕃漢轉戶二萬,出騎軍一萬五千。”好水濼的地點遼史未載,殘碑所在地點現在名叫烏蘇圖,烏蘇蒙語意為水,圖為有或眾多之意,兩者含義相同,遼代的好水源或許就是現在的烏蘇圖。附近就是查干沐淪河及遼代黑河的發源地,主要源頭是由這里順流而下,水草豐茂,是一個宜農宜牧的好地方。從遼史的片斷記載,似乎遼圣宗的興圣宮和世宗的積慶宮均設在這一帶地方。《道宗記》載:“大年二月七月甲子,賜積慶、興圣二宮貧民錢。”又“三年七月丙辰,獵黑嶺。丁巳,出雜帛賜興圣宮貧民。”于丙辰日在黑嶺及黑山此地打獵,第二天丁巳就賜雜帛給興圣宮民,可證興圣宮也在黑山附近,遠也不超過一日程。前面七月甲子日同時賜賞兩宮,說明這兩宮也相距不遠都在黑山附近。
遼代的宮衛制度在遼史和其他資料中有不少記載,但多過于略,特別是各代諸宮的所在地址和具體結構都不甚清楚。從這一殘碑的全部碑文中,即可看出一個翰魯朵的概貌。它占有人數眾多宮戶,這些宮戶分散居住在39個莊寨中(當然碑的一面文字殘缺所列莊寨遠不止此數)。這些莊寨以遷移地命名者有興中府莊、瞿州莊、宜州莊。以當地地理地貌或以住戶姓氏為莊寨者有下三家寨、樺皮寨、團子山、孔□寨、五家寨、沙泉子、砂宏寨、上后妃寨、渤海店、□家莊、南山楊墨里寨、西陡嶺寨、西寺家莊、蘇家寨、蠅子崖、金家寨、趙□莊、趙家寨等。以生產活動的不同分工而分為務、司或寨者,有營作寨、糧谷務、八作司、南灰務、上麥務、下麥務、菓園寨、教坊寨、西麥務等。這些莊、寨、司、務清楚地反映出翰魯朵這種皇莊的性質和經濟特點。每個皇帝從即位后,就從當時的內地劃出一定的土地、山林和牧場,集中大量的宮戶,從碑文來看主要是蕃漢轉戶來從事生產勞動。按不同生產對象分工也專門化,既有專門從事農業的宮戶,又有專門從事手工業的宮戶,并且更將從事農業細分為種植麥子、糧谷(粟稷、豆等雜糧)和菓園的宮戶,專門從事手工業的宮戶細分為營作司、八作司、南灰務、柳作務、窯坊寨等。這些農業、手工業不僅分工很細,似乎都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如司、務來管理,碑文中有督監、校尉等官職。按《遼史·百官志》載:“坊場局冶牧廄等宮”中,除坊使、詳穩外,最底下的一種官吏就是督監。因此碑中的督監或許是這些司、務的管理者。碑文中他們和宮戶并列,并無特殊標識,其地位并不顯赫,也說明只是管理這些司、務的下級管理者而已。除了這些生產上的分工外,還有后妃寨、教坊寨,這可能是供奉后妃宮帳的專門宮戶。教坊寨當然就是供帝后玩賞的伎樂人戶即為樂戶了。同時還出現兩處似乎從事旅店業者,如渤海店者等。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遼代翰魯朵是一種規模很大,占地遼闊,既有農業又有各種手工業的巨大莊園。并且按照生產專業在一定的機構管理下,從事著勞動生產,是一種封建性質的莊園經濟,這種經濟形式的存在對契丹族落后的奴隸制改變成封建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當然翰魯朵本身做為契丹族早期固有的習俗發展到碑中所反映出的這種經濟形式,是有很大變化的。特別是在舊的翰魯朵內注入了大量漢人和他們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后,翰魯朵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形成了契丹建立政權后,翰魯朵經濟形式成為支撐皇室統治的經濟支柱,這一點在契丹社會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契丹早期的翰魯朵在遙輦氏時期就已經存在,名為宮分,應當是族內貴族的“宗廟”或“祠堂”所在地,被視為神圣的地方。這種習俗不止出現在契丹族,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從遠古就有一種習俗。《史記》或《漢書》《匈奴列傳》里記載的“奧脫”,實際上就是契丹、蒙古族的翰魯朵。東胡族、匈奴族都有這種習俗,匈奴冒頓單于就是因為和東胡族爭奪翰魯朵(即奧脫)而進行了戰爭。過去史學界解為邊境守望之所、休候都是不準確的。契丹的翰魯朵就是繼承了這種民族傳統,從阿保機之后,這種傳統才有了性質上的變化,以后逐漸擴大和發展,演變成了龐大的封建性質莊園。
碑文中有七處提到六院司,其下接書契丹某某,如契丹移典、契丹烏魯本、契丹郭家奴等。這些都是契丹人,只有姚家娘子,似乎是契丹人的妻子是漢人,也說明契丹和漢人在一般人中間已經有了通婚關系,這一點也很重要。至于六院司是什么官職,遍查史料都無一定的解釋。《遼史·百官志》北面邊防官有五院司、六院司。而北面皇族賬官曾云:“肅祖長子洽昚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禮及懿祖仲子貼剌,季子褭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前者空無,后者似可信,碑文中六院司下的契丹某某很可能就是這些人的后代,或自願或罪沒而進入翰魯朵的。
在碑中出現的州名除興中府和宜州前面已略作論及外,值得探索的是黑河州和瞿州兩個地點。黑河州按《遼史·地理志》慶州條載:“慶州,玄寧軍,上,節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以地苦寒,統和八年,州廢。”過去一直把黑河州和慶州混淆起來,自從沈括《使虜圖抄》被發現后,才有了新的認識。《使虜圖抄》載:“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余步。絕水有百余家,墁瓦屋相伴,筑垣周之,曰黑河州。”證明黑河州在黑水附近,黑水的上游就是翰魯朵所在地,沈括渡河的地點距翰魯朵不會太遠。碑中提到的黑河州毫無疑問就是沈括所指的黑河州,這又一次證明了黑河州的存在,證明了它不是慶州的前身,穆宗所建的黑河州,因為碑的時代遠在圣宗廢州之后。
關于瞿州,遍查史料均未載明道宗時的翰魯朵蕃轉戶已不是從宋境或渤海俘掠人民“筑寨以居之”的時候了,因而也不會從遼初經過一百多年之后仍以原籍州縣的名字來命名自己的莊寨。由此證明瞿州莊必然和興中府莊、宜州一樣是從瞿州遷移來的宮戶所組成的。瞿州定然是遼境內的一個州,到道宗時仍然存在,而《遼史》《契丹國志》都失載,碑文可補遼史料的缺漏。
另外碑文中有嚴教寺,并有僧尼的名字。一方面說明翰魯朵規模之大,另一方面說明遼晚期佛教盛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嚴教寺行下除列舉僧尼名字外,尚有不少俗人,這些可能是為寺院從事勞役和生產的人。從他們的名字和僧尼列在一起可見他們已不是奴隸,可能是佃戶、雜役之類的人。碑文中尚有“奚婆”兩處,又有“渤海店”,這些都屬于蕃轉戶中的渤海人和奚人,他們人數較少,而身份地位和漢人并無區別,都屬于翰魯朵的宮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