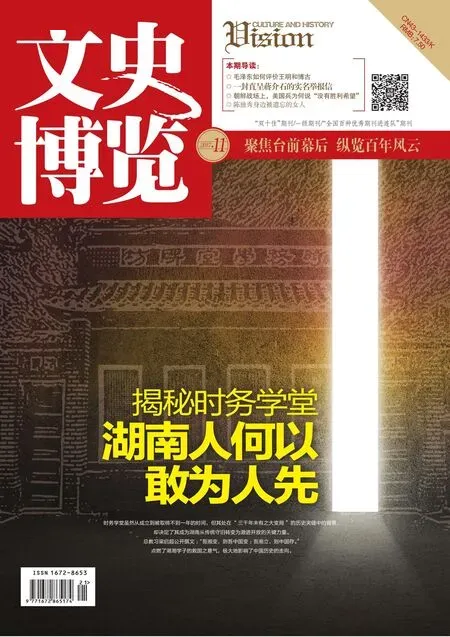揭秘時務學堂:湖南人何以敢為人先
張維欣
揭秘時務學堂:湖南人何以敢為人先
張維欣
1897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夜幕籠罩下長沙城小東街(今三貴街)的一間學堂里,師生們圍坐一起,觀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幻燈片放映。在投影屏上,學生們看到了英國倫敦的皇宮、街道、橋梁、飯店、馬車、輪船、兵器庫,看到了西方動物園中才有的獅子、大象、駝鳥,甚至還看到了英國“日不落帝國”時期的維多利亞女王畫像。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燈片放映,這座學堂名叫時務學堂。

坐落于長沙三貴街的時務學堂故址
甲午戰敗對湖南人刺激更深一層
晚清時期的中國,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近代中國幾乎每個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團體中,總有湖南人的身影。這一由湖南人所構建的湘學群體在時代交替中達以頂峰,并促使了晚清今文經學、大乘佛學以及西學東漸的融合。
而在此之前,湖南人卻并非一個整體開化較早或提前接受啟蒙思想的群體。在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后,湖南人長期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地域優越感之中。有位外國觀察家如是評價:“湖南人是個剛毅且獨立的種族,尚武、急躁、頑強,同時又自尊心強、保守、倨傲。”
固執與頑強,成了近代湖南人的“特質”。并且湖南地處內陸,與沿海省份相比,受國外影響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較強,社會風氣趨于保守。雖然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中湖南人居多,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首講西學者,為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但是包括曾國藩、左宗棠在內的洋務運動先驅,其主要活動和創辦的洋務實業多在外省而并不在湖南,因此他們的洋務思想對湖南影響較小,湖南反而“以疾惡洋務名于地球”。
這種固執自大的心態,成為甲午戰前湖南人拒絕改革的思想因子,以致其在拔電線、拆鐵軌之外,甚至聚眾圍攻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宅子,并大肆對其進行人身攻擊,以此表明自己拒絕開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務之決心。種種行為與跡象,已將湖南徹底變為一個與時代脫節的頑固保守的大本營。湖南的近代化進程因此而受到強烈阻礙,以至晚其他省份近30年。
面對甲午戰爭中打著湘軍大旗的李光久、魏光燾兵敗于遼東半島的局面,挽救了清朝命運的湘軍面對日本侵略軍并沒有創造奇跡,昔日戰績構筑的壁壘如今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的心態終于有了轉折。譚嗣同曾在致其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表示,湖南人因甲午戰敗而敲響警鐘,結束了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態,這樣慘痛的教訓亦可以視為是中國挫敗中的一絲曙光。
正由于之前的閉塞,甲午戰敗對湖南人的刺激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層。這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為其他省份的人所沒有,給湖南社會風氣的轉變帶來了機會,湖南從最保守的省份一變而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因而,短短幾年間,湖南由萬馬齊喑的排外格局轉變為維新運動時期全國最激進的省份,湘中官紳、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紛紛覺醒。此時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開風氣的士紳領袖,其中既有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思想激進的士紳新秀,他們大多年輕有為,敢作敢為;也有皮錫瑞、歐陽中鵠、朱昌琳等熱心地方事務的士紳名宿,他們老成持重、穩健熟稔。與此同時,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員,如巡撫陳寶箴、鹽法道黃遵憲、兩任學政江標和徐仁鑄。官紳都有志于開風氣,這在當時的中國各行省中十分難得。
湖南維新運動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大批維新骨干入湘,湖南成了維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動湖南維新走向高潮;二是德國搶占膠州灣之后,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加快劃分勢力范圍,瓜分危機逐漸顯露,民族救亡的意識深深滲透到湖南人的思想中。
歷史選擇了湖南。時務學堂,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大背景當中。

熊希齡
第一架大天文望遠鏡
時間追溯到1896年的冬天,最早提出創辦時務學堂的是湖南湘鄉人蔣德鈞(1851—1937,曾任四川龍安知府,因父喪返湘,后參與礦務經營),然而最初卻是以長沙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設立工藝學堂作為創辦動議,類似于現在企業中的員工培訓機構。這一提議得到了寶善成公司創辦者王先謙、熊希齡的認同,亦得到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并親自將其定名為時務學堂。
學堂開辦之初,首要問題即是經費。為此,熊希齡與蔣德鈞于1897年4月親赴南京,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求撥督銷局鹽厘7000金作為辦學經費,然而督銷局總辦易順鼎卻橫生枝節,要求將7000金中再分撥2000金以作他用。熊希齡堅決不從,在湘中官紳的周折努力下,最終于重重困難中保全了這來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隨后,陳寶箴又上書光緒帝申請撥款1.2萬兩用作學堂常年經費,至此方才解決了時務學堂的經費問題。
在籌備經費的同時,熊希齡和蔣德鈞亦趁在江浙滬之機,著力進行圖書和儀器購置等工作。曾開辦過中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的譚嗣同熱心襄助他們的儀器購買事宜,并將楊仁山(曾任駐英法大使曾紀澤的參贊)從海外購買的各類儀器售賣予時務學堂。
教育家朱經農曾回憶,當時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遠鏡就在時務學堂閣樓上,學生們可以在此觀測各類行星。學堂中的學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進的教學設備,與譚嗣同、熊希齡的努力不無關系。除此之外,譚嗣同還推薦楊仁山之子楊自超擔任時務學堂測量教習兼儀器管理員,將其從英國學到的測量知識傳布予年輕的湖湘士子們。
時務學堂選址在長沙城北一個叫侯家垅的地方。在校舍建成前,熊希齡暫時租賃了原乾嘉重臣劉權之的舊宅作為校舍,這座南北向的小院子前后共有五進院落,西邊為學生宿舍。學堂主入口位于今天的中山西路上,即是以前的小東街,東西北分別為三貴街、福慶街、連升街,是個傳說中的“風水寶地”。
陳寶箴親自為時務學堂擬定了《招考告示》,張貼于省城的大街小巷。這份告示放在今天來看同樣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避開了千軍萬馬過獨
木橋的科舉考試,時務學堂的優秀畢業生可保送京師大學堂,或公費出國留學,最差也可保證派充使館譯員,或擔任南北洋海軍、船政局、制造局等中央控股企業辦事員。
如此優厚的工作分配制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學子,第一批招生名額僅有40人,卻吸引了4000人前來報名。錄取率之低,可謂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學如章士釗也未能考中,被時務學堂拒之門外。并且,即使是第一批考入時務學堂的40位學生,也未能全部留下。錄取3個月之內,學堂進行甄別考核,中西教習會同紳董根據學生平日功課分數及性情舉動,合校互勘,綜合評定,最后確定合格學生共計27人。
時務學堂是個“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的學校,學生中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生,用學堂之法教學;專學中學而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生,用書院之法教學。但后來,內課與外課生的區別主要取決于考生的優秀程度,成績最優者方能成為內課生。
蔣德鈞在北行之時,亦將為學堂物色總教習作為重要任務。經黃遵憲的推薦,康有為的弟子、上海《時務報》總主筆梁啟超成為首要人選。梁時年僅24歲,卻已然名動天下。作為《時務報》的頂梁柱,報館總理汪康年自是不愿放人。為此,陳寶箴專程為梁送去聘書,再由熊希齡想盡各種辦法對汪康年施加壓力。最終在各方軟硬兼施之下,汪康年松口,梁啟超于1897年11月偕李維格以及同門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從上海抵達長沙,使得外國人眼中的這座“鐵門之城”堪稱集一時之萃。
至此,時務學堂成立了包括熊希齡、譚嗣同、蔣德鈞、王先謙在內的9人董事會,決定和討論與學堂相關的重大事件。同時,陳寶箴委任熊希齡擔任學堂總理紳,即校長。梁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李維格擔任西文總教習。譚嗣同、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楊毓麟擔任中文分教習,王史擔任西文分教習,許奎垣擔任數學教習,地理學家鄒代鈞擔任輿地分教習,另由楊自超擔任測量教習。

陳寶箴
點燃湖湘少年的救國之意氣
189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正式開學。當日,舉辦了隆重的開學儀式,學堂總監譚嗣同撰聯“攬湖海英雄,力維時局;勖沅湘子弟,共贊中興”以示慶賀。總教習梁啟超亦撰寫了《湖南時務學堂公啟》并刊于報紙向社會公布,他以不同凡響之筆法點燃了這批剛剛入學的湖湘少年的救國之意氣:“吾湘變,則吾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其以視今日之日本寧有讓焉!”
梁啟超親自制定了《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分別是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他提出應“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的教育理念,灌輸“國家主義”的思想,要求學生將讀書、立志與經世緊密結合,樹立“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遠大志向,為國家自強、民族救亡獻身。由此,時務學堂的政治氛圍“日日激變”,形成了獨特的精神風貌。
在課程設置上,梁啟超做出了明確的規劃,采用“中西并重”的教學方針。他將學堂所學科目分為溥通學和專門學兩大門類。溥通學,相當于現代高校中的通識課程,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學五大類;專門學,相當于現代高校中的專業課程,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三大類。學生初入學堂,需要統一學習溥通學6個月,期滿之后方可學習專門學,同時仍要學習溥通學。
不難看出,課程設置既有中文以及傳統文化的學習,亦有西學以及科學技術的學習,已經具備近代高等教育課程設置的雛形。這樣大膽改革教學內容,不僅將時務學堂變成了維新運動的前沿陣地,更是一次近代化思想的啟蒙行動。
除去課程設置,時務學堂亦對學生規定了不同時期所須閱讀的書目。為此,梁啟超亦經過了極為精心的設計。他將學生所讀之書分為“專精之書”與“涉獵之書”兩大門類。專精之書,學生必須認真完整研讀,并仔細揣摩,讀書時間須占到每天全部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六;涉獵之書,學生可以“隨意翻閱”,讀書時間占到每天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四即可。梁啟超強調此二者不可偏廢,“無專精則不能成,不涉獵則不能通也”。

時務學堂教習合影(左起):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他給學生開列的書單包括《春秋公羊傳》《萬國公法》 《幾何原本》 《日本國志》 《化學鑒源》 《萬國史記》《格致匯編》等,其書目列舉范圍甚廣,書籍報刊均在閱讀范圍內。將古典儒學、西洋科技、中外史地融為一體,學生們在課堂上無不屏息靜氣,沉浸其中。這種中西并重的教學打破了獨尊儒術的傳統觀念,使學生們能站在世界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國家,樹立新的近代國家觀念,探求自強之路。
在教學方法上,時務學堂則提倡靈活多樣,梁啟超擬定了《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要求學生每人準備札記兩冊,將讀書心得記于其中,五日一交,由教習批注,并在教室中設置一問題匣子,讀書有疑義均可投匣提問。為給學生批閱札記,梁啟超時常通宵不睡,并且每條批語達數千言之多,對于學生新穎的思想和認知,他不吝惜贊美之詞而褒揚有加,盡可能多行鼓勵。這種既有教授,又有答疑和互動的教學方法,一反傳統舊學不顧學生思維、填鴨式的教育,迅速發揮出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能力。
時務學堂的考核制度亦與現代高校的“學分制”非常接近,學生所作札記由教習評定后給予等級分數,最差者給半分,最高者可達3分,每月30分為及格線,溢分者給予銀兩獎賞,林圭、蔡鍔、李炳寰、唐才質等常常溢分達50余分。同時每季大考一次,將成績排名貼于學堂大門之上,并刊登于《湘報》《湘學報》。除此之外,優秀學生的札記亦予登報,甚至被編印成書,出版發行。這種方式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鼓勵,故而意氣風發,于學業有極大的熱情和主動性。
時務學堂能在極短的時間里造成良好的社會影響,除了梁啟超的個人魅力外,也離不開一個與他志同道合的教育團隊。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人既是梁啟超事業的盟友,又是梁啟超生活中的摯友,他們不僅能貫徹梁啟超制定的教育方針,更能實際帶領學生共同研習學業和時務;譚嗣同、唐才常、黃遵憲、熊希齡等人常與梁啟超無拘無束議論時政、共抒志向,成為知己。
作為學堂的教習,譚嗣同曾介紹他的兩位摯友唐才常、江標與梁啟超相識。初次見面,唐才常即贈給梁啟超一方家鄉瀏陽的菊花硯,并由譚嗣同親自撰寫硯銘詩一首。江標擅長金石雕刻,且素與譚、梁為莫逆,在他卸任學政預備離湘之時前往學堂與舊友話別,正巧看到此硯和詩銘,忍不住連夜將此銘刻于硯上。刻完之時,已到第二日晨曙,譚、梁、唐送別江標于舟上,這是他們的最后一次會面。
多年以后,譚嗣同、唐才常、江標均已不在人世,梁啟超十分愛惜這方見證著四人友誼的菊花硯。然而,戊戌政變后他東渡日本之時臨行匆匆,竟將此硯遺失。他揮淚寫道:“數年來,所出入魂夢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復飛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時也。念之凄然。”
正是這樣一個團隊所凝聚的理想和心血,開啟了湖南的民智,開通了湖南的風氣。

梁啟超
新舊之爭水火不容
梁啟超在26年后曾回憶起他們在湖南的“離奇思想和舉動”:“那時的青年都有進取思想,高談時局,研究滿清怎樣對不起漢人及中國兩千年來的專制惡毒,這班青年都是向這兩個目標去,而我們在湘做的事,分作四項是:辦時務學堂;組建南學會;辦報《湘報》;辦刊《湘學報》。南學會是公開講演機關,講演社會上不以為奇的話。時務學堂則專研究怎樣貫徹我們的主義。”
南學會是在巡撫陳寶箴支持下,由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創立的,講期定于每周的星期日進行,由社會名流、學者登臺講演。講演者中,皮錫瑞主講學術,黃遵憲主講政教,譚嗣同主講天文,鄒代鈞主講輿地。除此之外,陳寶箴、歐陽中鵠、曾廣鈞以及時務學堂教習李維格、楊自超亦登臺講演。
南學會之講演涉及時政、經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算類等方面,極大開拓了時務學堂學生的知識面和眼界,既是對學堂教學極好的補充,也是鼓勵學生多方學習甚至參政議政的重要途徑。
時務學堂在一年之內共舉行過3次招考。包括兩次補錄在內,時務學堂錄取人數共計264人。
然而處于新舊交替之中的時務學堂最終還是引來了激烈的紛爭,畢竟兩派的教育宗旨和目的不一樣,守舊派的育人振國是和忠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維新派的教育目的則在于以民主平等的政體代替君主專制的政體,實現國家的富強。因此,新舊兩黨為此幾乎達到了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程度,其紛爭一直持續到北京的戊戌政變發生之后。
引發時務學堂新舊之爭的重要“物證”即是梁啟超為學生動輒千言的札記批語。守舊派代表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的學生蘇輿把梁啟超所作批語收錄于一冊,并取名為《翼教叢編》,以此作為攻訐維新派的有力證據。所收錄札記中關于去跪拜、變服飾、興民權、開議院等方面的激烈言論引起“全湘嘩然”。
除此之外,梁啟超與譚嗣同還曾私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禁書,并加以按語,秘密發放給學生閱讀,表面君主立憲的改革呼號暗中已經演變為廢除君主制度、啟蒙革命思想的本質。這樣言辭激烈的批語和行為,為之后水火不容的湖南新舊黨爭乃至之后的戊戌政變的發生都埋下了伏筆。
梁啟超曾在1922年回顧這一時期學生在接觸了西方民權思想后的社會反響:“學生因在學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學問,所談論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及至年假放假后,學生回家發狂似的宣傳起來,風聲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為大逆不道。有的攻擊我們,有的勸誡我們,當時王葵園(王先謙)、葉奐彬(葉德輝)皆攻擊我們,作我們的勁敵。那種奮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滿開學,學生家庭就不準他們再來時務學堂,而學生與家庭奮斗,比老師與社會奮斗更烈。”
維新派此時處于極為不利的局勢,在陳寶箴的折中妥協下,熊希齡受命送學生赴日留學,由黃遵憲擔任學堂總理官,汪康年為總理紳,而此時的梁啟超早已受師命“即刻赴京”離開了長沙,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中文教習被辭退,時務學堂的維新色彩頓減。
戊戌政變后,維新派遭到搜捕。梁啟超和11名時務學堂的學生逃亡日本,而不愿出走的譚嗣同于9月28日遭到清政府處決。第二天,學政徐仁鑄被清廷革職。10月初,陳寶箴、江標、熊希齡亦被革職,時務學堂交由守舊派接管,名實俱亡。

譚嗣同
近代史政治舞臺上第一次優秀演出
戊戌政變以后,原時務學堂中文教習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轉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均建立聯系,意圖聯合各方在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勤王起義。那時,原時務學堂的學生林圭、蔡鍔、蔡鐘浩、范源濂、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質,以及廣東人馮自由、鄭貫一等20余名學生正在日本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就讀,這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俊杰“日夕高談革命”,并且許多人以羅伯斯庇爾、華盛頓自命。唐才常很快吸納了這股年輕的力量,銳意回國發難。
1899年9月,在他們回國舉事的前夕,梁啟超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紅葉館為他們舉行餞別會。這天之餞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氛,據與會者陳少白回憶:“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1900年春,唐才常于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氣會,后改名“自立會”,并于次年7月組建了自立軍,計劃于8月9日在長江沿岸地區的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發難。然而因資金耗盡和消息泄漏,自立軍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剿滅。唐才常與時務學堂學生林圭、秦力山、蔡鐘浩、田邦璇、李炳寰等22人被清廷殺害在武昌紫陽湖畔,蔡鍔、唐才質得以僥幸逃脫。
林圭是湖南湘陰人,畢業于時務學堂二班,品學兼優,屢次考試均名列前茅,位居“溢分”之榜。林圭素來仰慕譚嗣同的為人,譚亦對他十分器重,曾贊許他為“造世之英雄”。林圭常說:“吾人今日求學,應以挽救國家為第一要義。”林圭面貌清秀,“身高而瘦,說話時目光四射” ,是自立軍中僅次于唐才常的領導人。他以25歲之年葬身紫陽湖畔,卻點燃了革命之火。
李炳寰是時務學堂中另一位高材生,湖南慈利人,他是第一期招生考試中的第一名。唐才常胞弟唐才質曾回憶他:李炳寰與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兩人意氣相投,就換帖為兄弟。他曾對我說:‘我們求學,所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人,上利于國,下澤于民耳。’炳寰赴漢口時珍重道別,除勉勵救國外,沒有說其他的話,其愛國熱情,殊令人欽佩。”李炳寰與老師唐才常一同就義于紫陽湖畔,時年僅23歲。他的父親李樹芳亦遭株連,被清廷殺害。
自立軍起義是時務學堂學生在近代史政治舞臺上的第一次優秀演出,師生之間的肝膽相照更是前所未有。當年學堂年紀最小的學生蔡鍔更是近代史上被譽為“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鍔(字松坡)原名蔡艮寅,湖南邵陽人。唐才質在時務學堂初識蔡鍔就對他印象尤佳,他曾回憶道:“松坡在同班年齡最小,體質亦復文弱,初不為人重視,然而言論見解,有獨到之處,知少年好學,根底甚為深厚也。”蔡鍔被江標、徐仁鑄兩任學政所賞識,并被徐仁鑄推薦參加時務學堂首批招生考試,在15歲那年從邵陽出發,趕了幾百里路到長沙,并于4000多人中脫穎而出,拿到第三名,成為一班中文內課生,是時務學堂中最負盛名的“學霸”,《湘報》曾數次登載他優異的成績。在學堂中他多受梁啟超提攜關懷,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蔡鍔所寫的札記,梁啟超動輒批閱上千字,并多有“極通”“比例精當,見地瑩澈”“若能每條以此求之,則圣人之意不難見矣”等贊賞之語。
戊戌變法失敗后,蔡鍔歷經艱辛輾轉出國,找到老師梁啟超,并參與到了自立軍起事之中。在經歷了譚嗣同、唐才常兩位老師的為國殉難之后,他深受刺激,于是更名蔡鍔,取意“刺破青天鍔未殘”,并決意以身報國。
1912年,梁啟超回國擔任司法總長,當他目睹袁世凱種種專制之舉和暴露出的復辟苗頭時憤然辭職,與蔡鍔合力發動護國戰爭。蔡鍔曾有言:“袁世凱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著中國人,是什么東西呢!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蔡鍔輾轉回到云南后當即通電討伐袁世凱,率領護國軍入川,激戰十萬袁軍,最終使得袁世凱在護國浪潮中憂懼而死。

蔡鍔
1916年11月8日,蔡鍔因病情惡化,在日本福岡病逝,年僅34歲。梁啟超在公祭大會上為蔡鍔致悼詞時泣不成聲。后來他將蔡鍔生前所用的九獅刀、望遠鏡、勛章、軍裝等遺物收集起來,建立了紀念蔡鍔的“松坡圖書館”,他甚至還把蔡鍔的大幅戎裝畫像懸掛在自己飲冰室的臥室墻上,以示懷念。
1922年8月,梁啟超重回長沙,專程重游時務學堂舊址,在蔡鍔住過的宿舍內,據說他曾佇立良久,回顧往昔而至泣不成聲。之后,他題寫了“時務學堂故址”六個大字,后署“二十六年前講學處 民國壬戌八月重游泐記 梁啟超”。他曾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寫道:“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用他們的生命換出來的,他們并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華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從哪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中華民國,才配做他們的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想起,那眼淚便在肚子里倒流。”
時務雖倒,湖南人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薪火相傳
時務學堂造就的人才是多元的,除了走出一批為革命奮斗的政治、軍事人才,還有一批教育家和實業家。
范源濂,湖南湘鄉人,是時務學堂二班中文內課生,他是時務學堂中走出來的對教育影響最為深遠的學生。戊戌政變后,他和蔡鍔等同學一起前往日本,下定決心以教育救國。中華民國成立時,他曾被選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次長,護國戰爭之后,他當選為教育總長兼內務總長。他先后擔任清華學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并四次任民國政府教育總長。他重新制定頒布大學章程,將西方大學體制的優點融入其中,規定各大學按專業分科,按專業分系,使得初步的近代大學教育體制慢慢成型。
范源濂,曾與林圭是同鄉兼同學,在林圭于自立軍起事中犧牲之后,他肩負起了撫養和教育林圭獨子林受祜的重任,并送他至天津南開中學就讀。林受祜對范源濂充滿感恩之情:“范先生培成故人之子,熱腸俠誼,良深感泣,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楊樹達,湖南長沙人,是時務學堂中走出來的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他是清華大學繼陳寅恪之后第二位國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除此之外,他還曾在北京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學院任教。他在時務學堂期間的表現雖鮮有提及,也并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投身革命,但他用一生時間專注于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他在語法、修辭、金石、甲骨,以及古文字訓詁、音韻等方面造詣極深,所著的《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用心審密”“精湛透辟,曲園所不逮”。語法方面著作《高等國文法》,至今仍為我國乃至國外中學、大學的語法教學用書。他還因治甲骨文、金文而被稱之為“今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楊樹達最有成就的是《漢書補注補正》,對先秦諸子、兩漢經史大量校勘、考釋、闡述,陳寅恪讀后直呼:“《漢書》顓家,公為第一,可稱漢圣。”
李肖聃,湖南長沙人,亦是學堂中成長起來的一位著名學者。在時務學堂舊址碑坊處還留有他做的題記,就在梁啟超手跡之后。1913年梁啟超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時,他曾擔任梁的秘書,專司筆札,深得梁啟超信任。他曾長期任教于湖南大學,專授文史課程。李肖聃一生博學耿介,為眾所欽。
梁煥均,湖南湘潭人,是大實業家梁煥奎的三弟,1898年春進入時務學堂。他受長兄影響,又因為家中經營礦產實業,故而走上實業救國之路。梁煥均任華昌公司總經理期間,華昌公司除長沙南門口外的華昌煉銻廠外,還在安化、新化等地新設采銻礦廠100多家,新設鎢礦、錫礦、煤鐵礦等近100處。他在任的三年期間,華昌公司一度成為湖南最大的民營企業。
1899年,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還來不及搬進新校舍的時務學堂被更名為求實書院,遷往長沙落星田一帶。
1903年,時務學堂和岳麓書院合并為湖南高等學堂,并于1926年定名為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正式升為國立湖南大學。
1938年,時務學堂故址毀于抗戰文夕大火中,片瓦無存。
然而時務學堂的教育精神卻傳承至今,依然以其“敢為天下先”的理念教育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毛澤東曾在《湘江評論》撰文說:“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戊戌政變,陳寶箴走,譚嗣同死,梁啟超逃,熊希齡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書,一大堆在小吳門外校場坪聚燒了。于是時務學堂倒了。時務雖倒,而明德方興。”
120年前誕生的時務學堂,以其獨有的方式,培養了一大批維新人才,播撒了革命的種子,深深影響了湖南各地的學風,激發了開明紳士改革舊式書院、創辦新式學堂的熱情,促使湖南高等教育邁向近代化,促使湖南成為近現代人才大省,其地位迅速在全國崛起。
直到今天,被湖南大學的學子們所津津樂道的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叫熊希齡的校長,有過一個叫梁啟超的教務主任,有過一個叫譚嗣同的老師,有過一個叫蔡鍔的學長。”
(責任編輯:亞聞)
(郵箱:2003xyw@163.com)
201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成立120周年。
這座湖南維新運動時期的最高學府,可能許多人并不知曉,但它是戊戌維新期間的直接產物,是梁啟超、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名師匯聚之處,更是培養出了蔡鍔、林圭、楊樹達、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之處。薪火相傳,她見證了學堂師生的情深義重與生死摯交,見證了湖湘近代化歷程中最為艱辛的歲月,更寄托了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時務學堂雖然從成立到被取締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其處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歷史夾縫中的背景,卻決定了其成為湖南從傳統守舊轉變為激進開放的關鍵力量。總教習梁啟超公開撰文:“吾湘變,則吾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點燃了湖湘學子的救國之意氣,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時務學堂的誕生,點燃了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