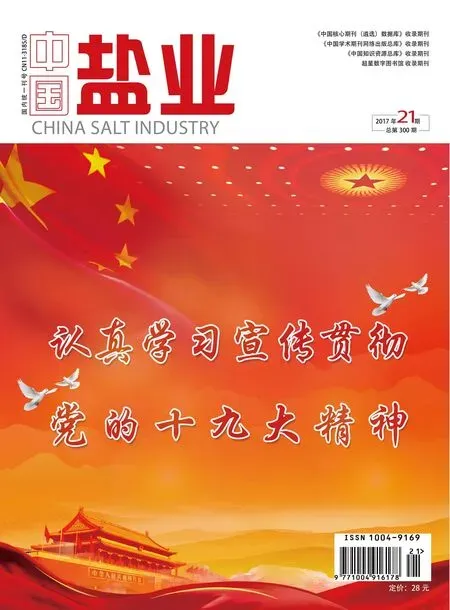非法批發食鹽定罪?慎、慎、慎
■ 陳棟
非法批發食鹽定罪?慎、慎、慎
■ 陳棟
鹽改以來,因為非法經營食鹽入罪的案例時有耳聞,到底什么是非法經營食鹽犯罪,什么情況下批發食鹽可能獲罪,食鹽跨區經營四種渠道是否存在合法性悖論?今天,小編就和大家聊一聊非法經營食鹽定罪的那些個事兒。
一、涉及非法經營食鹽犯罪的法律條文有哪些?
在我國,涉及非法經營食鹽犯罪(本文著重于非法批發食鹽犯罪)的法律條文主要集中在以下法律、法規中:
(一)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對非法經營罪,做出如下描述:“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

(二)國務院制定的《食鹽專營辦法》《鹽業管理條例》通過對鹽業資源的開發、利用、生產、儲運、銷售等一系列活動的規定,建立起較為系統的食鹽專營制度。其中,《食鹽專營辦法》第二十一條,違反食鹽批發許可行為規定如下:未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經營食鹽批發業務的,由鹽業主管機構責令停止批發活動,沒收違法經營的食鹽和違法所得,可以并處違法經營的食鹽價值3倍以下的罰款。
(三)2002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經營食鹽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銜接《刑法》與食鹽行政管理法規,在實踐操作上,做出了較為清晰的說明。
其中第一條,違反國家有關鹽業管理規定,非法生產、儲運、銷售食鹽,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條,非法經營食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非法經營食鹽數量在二十噸以上的;(2)曾因非法經營食鹽行為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非法經營食鹽,數量在十噸以上的。
二、批發食鹽什么情況下可能涉及非法經營犯罪?
以無證批發食鹽來看,構成非法經營食鹽犯罪應當至少具備以下四個要件。
(一)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管理秩序。為了規范食鹽的流通秩序,《食鹽專營辦法》對批發食鹽的活動實施許可證管理制度。沒有取得許可證的單位和個人,原則上不得從事食鹽的批發活動。
當然,現實當中大家容易把批發、零售與銷售弄混淆。銷售在柯林大辭典中的意思多表示為“出售,處置或轉讓給買方以換取貨幣或其他代價”。現實中的銷售范圍較廣,既包括了價值交換這一過程,也包含了為促進交易而進行的廣告、促銷、展覽、服務等。零售意思為“單獨或少量向消費者出售貨物”;與零售相對的是批發:相比較售賣商品給最終消費者,批發是一種向零售商大量售賣,并向制造商更加大量購買的生意。從流通環節上看,批發活動多介于生產商與零售商中間。而零售商則直接面對最終用戶,最終用戶購買后,商品被耗用、儲藏從而退出流通;從售賣數量上看,實踐中沒有清晰明確的標準,但一般說來零售相對較小,批發相對較大。
在現行的《食鹽專營辦法》中,雖然沒有直接關于批發的定義,但是從相關的法規條款中,我們認為,“向食鹽零售單位和受委托代銷食鹽的個體工商戶、代購代銷店以及食品加工用鹽的單位售賣食鹽的交易活動”可以被簡單認為批發活動,需要具備食鹽的批發許可資質。而對于食鹽的零售行為則沒有行政許可的約束。
(二)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具體到非法經營食鹽領域則為“違反國家有關鹽業管理規定,非法生產、儲運、銷售食鹽,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1)非法經營食鹽數量在二十噸以上的;(2)曾因非法經營食鹽行為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非法經營食鹽,數量在十噸以上的。”
(三)本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個人和單位均可構成本罪的主體。
(四)本罪在主觀方面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這是本罪在主觀方面應具有的兩個主要內容。如果行為人沒有以謀取非法利潤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規,買賣經營專營物品的,不應當以本罪論處,應當由主管部門對其追究行政責任。
三、食鹽是如何從生產企業流通到消費者手中的?
以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小包裝食鹽為例,改革前的流通模式如下:
食鹽定點生產企業依照國家計劃向省級批發企業供應食鹽產品,定點生產企業不得自行組織食鹽的批發、零售;省級批發企業向市縣公司轉批食鹽或者自建銷售平臺組織本省、直轄市、自治區內的食鹽批發;市縣級批發企業或自建平臺通過三種方式展開食鹽的銷售,主要包括:
(一)食鹽批發企業直接銷售給最終消費者或食品加工用鹽單位,比較典型的做法為設立食鹽零售點,開展網絡平臺零售以及面向加工用鹽單位的直接銷售;
(二)食鹽批發企業向食鹽零售單位批發食鹽,經由零售單位銷售給最終消費者,比較典型的是通過超市賣場零售給城鄉居民;

(三)食鹽批發企業向集貿市場商戶、城市副食品批發商戶批發食鹽,集貿市場商戶、城市副食品批發商戶通過不同層級的轉批發,供應零售單位食鹽,零售單位再銷售給最終消費者。
在這三類流通模式中,第(三)類方式占據了小包裝食鹽供應的主渠道作用,根據學者研究數據,在商貿物流高度發達的上海,近75%的小包裝食鹽是通過多級轉代批途徑銷售的。而在一些商貿還不夠發達的地區,第(三)類方式很可能占據了更高的比例。
參考經典的營銷理論,第(三)類方式是較為典型的密集分銷模式,通常指生產者運用盡可能多的中間商分銷其產品,使渠道盡可能加寬。當消費者要求在當地能大量、方便地購買時,實行密集性分銷就是至關重要的。該模式一般用于方便品項目,如香煙、肥皂、小吃和口香糖之類。對于今天城鎮化率還不足60%的中國,第三類營銷模式顯然是具有較強生命力的,小包裝食鹽與日化、米面糧油一起通過密集分銷層層流轉下去,有利于形成物流成本的集約,使商品能較為便宜、穩定的出現在城市與鄉村消費者面前。
但現實的流通模式與制度構建存在非常嚴重的沖突,即:小包裝食鹽在出了鹽業專營公司后就進入無證批發的狀態,在到達最終消費者手前的層層批發環節,均違反了《食鹽專營辦法》的規定。從歷年的食鹽政策上看,也許國家主管部門曾力圖通過構建食鹽流通現代化、實施轉代批發制度等來緩和現實與制度的矛盾。但時至今日,流通現代化依然無法取代市場天然形成的層層轉批,轉代批許可制度也因為種種原因走向終結。
《鹽業體制改革方案》出臺,改革了食鹽生產批發區域限制。允許食鹽定點生產企業進入流通和銷售領域,自主確定生產銷售數量并建立銷售渠道,以自有品牌開展跨區域經營,實現產銷一體,或者委托有食鹽批發資質的企業代理銷售。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又聯合發文(工信廳聯消費〔2016〕211號)指出,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改革過渡期內,食鹽批發企業(含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食鹽定點生產企業,下同)開展食鹽銷售經營活動可以通過以下四種方式進行:1.通過自建物流系統或與第三方物流企業簽訂配送合同委托其將食鹽配送到商超、銷售網點以及從事食品加工、餐飲服務的單位等食鹽終端用戶;2.通過自建分公司進行食鹽銷售業務,自建的分公司不得委托沒有食鹽批發許可資質的單位、個人開展經營活動;3.通過自建銷售網點直接開展食鹽銷售業務;4.通過現有渠道開展食鹽銷售業務。
對于密集分銷模式,在改革前,由于特殊的案件移交模式(多由行政執法機關移送公安機關)以及行政執法者的關注重心是商戶是否在經銷本地鹽,鮮有中間批發商戶因無證批發本地食鹽而被移送刑事處理。然而,到了改革時期,一些中間的批發商戶因代理了外地食鹽而侵害了本地鹽業專營公司(鹽務局)的利益。執法者頻頻利用“批發許可證”阻擊外鹽食鹽跨區域(省)經營。這在事實上造成了本地鹽務局的選擇性執法,也就是對于同樣的多層批發經營行為,對本地鹽業公司以“現有渠道”為由以合法行為對待,而對外地鹽業公司則以“非法經營”對待。對于業已存在的密集分銷渠道能否名正言順的走向合法,鹽業從業者充滿期待。“現有渠道”是否指的是改革前的密集渠道呢?我們可以從下面看出些端倪。



2月21日,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巡視員王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取得省級批發許可的食鹽定點生產企業,向食鹽銷往地的省級鹽業主管部門進行相關備案。并采用以下四種方式運營,跨省賣鹽,就不應該受阻”。“第四種是現有的渠道,在沒有改革時,鹽業公司有渠道,現在渠道照樣有效。”
相類似的,江蘇省鹽務局在蘇鹽〔2017〕10號文中指出,“進入江蘇從事食鹽跨區經營的省級食鹽批發企業(包括取得批發許可證的食鹽生產企業,下同)應當按照食鹽專營制度和鹽業體制改革相關管理規定規范開展食鹽經營活動……(三)可以通過現有渠道開展食鹽銷售業務,現有渠道指工信廳聯消費〔2016〕211號文件印發之日前已事實存在并發生業務關系的銷售渠道……”
四、相關法律法規是如何修改的?
目前有關食鹽專營管理的兩部法規,《食鹽專營辦法》、《鹽業管理條例》已完成了公開的征求意見。從公開的資料看,食鹽專營制度將呈現新的發展內涵。
從上表不難看出,專營制度體系的幾大柱石在本次修訂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調整,而計劃管理、價格管理、運輸管理等制度更是幾乎遭到了廢除,鹽業市場的活力將進一步激發。保留許可證管理也意味著行業并沒有徹底的放開,挑戰制度底線的行為依然將遭到法律的制裁。而且,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具有行政違法性,隨著食鹽行政法規的調整,也必將帶動相關的涉鹽犯罪領域規范性文件的調整工作。
五、結語
非法經營罪的前身為投機倒把罪,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一些關于非法經營的司法判決引發了人們關于“新口袋罪”的擔憂。今年2月,內蒙古農民王力軍“收購玉米案”落下帷幕,再審法院認為王力軍沒有辦理糧食收購許可證及工商營業執照買賣玉米的事實清楚,其行為違反了當時的國家糧食流通管理有關規定,但尚未達到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備與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的必要性,不構成非法經營罪,依法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王力軍無罪。
相對于糧食收購許可管理,食鹽流通的管制更加明確與具體,法律上的效力也更高。直接用糧食收購許可制度對比食鹽批發許可制度既不實際也無必要。但回顧王力軍“玉米案”的發生背景,即現實存在著大量的糧食經紀人無證從事糧食收購,并發揮收購重要渠道作用的現象,是不是和今天的食鹽批發流通現狀又存在著一定的相似呢?改革前的食鹽專營體系,是數十年來政治、法律、文化、市場等多股力量交織后形成的均衡態勢,一旦打破,便需要經過復雜的過程去重塑。《鹽業體制改革方案》提出建立公平競爭、監管到位的市場環境,兼顧現實實際與制度規定,在“放、管、服”改革大背景下,如何做好鹽業改革這道題,應當成為全體鹽業人的思考。
(作者單位:中鹽上海市鹽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