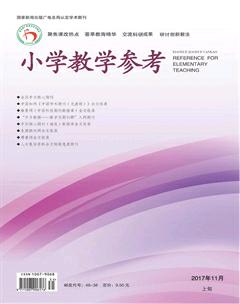從干國祥老師的課堂教學說起
[摘 要]干國祥老師教學的內容是人教版四年級上冊《語文園地三》的習作“學寫童話”。他的教學先從漫談童話入手;再出示一組故事,引導學生探尋故事的原型;接著,在此基礎上,創建了一個創編故事的大致“模型”;最后學生根據故事的原型編寫自己的童話故事。他的教學啟示我們:寫作教學要教到“上位”、教在“本位”、教在“這一類”才有效。
[關鍵詞]寫作教學進行時;課堂教學;上位;本位
[中圖分類號] G6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9068(2017)31-0001-02
在河北石家莊,我和著名學者干國祥、特級教師高子陽,一起舉辦了寫作教學高級研修活動。其間,邀請干國祥老師執教一節作文指導課作為研討案例。課前,他說:“這一課,我為何捷老師而上。”干老師知道我在兒童寫作教學領域探索了20多年,如今陷入瓶頸,找不到突破口,做得很辛苦。于是,他把這節課“獻”給我,說是向我致敬,但我知道是給我安慰。
干老師選用人教版四年級上冊《語文園地三》的習作“學寫童話”作為教學內容。我看過不少教師上這節課,大都先創設情境,再進行表演。表演時,你扮演小貓,他扮演小狗。在情景對話后,學生把之前的經歷和體驗寫成故事。也有的教師省略活動環節,直接進行天馬行空的想象。此類童話故事創編課,基本都是“成功”的,小孩能寫,且效果不錯。因為,想象是孩子的天賦;我們的教學目標,就是“寫出這一篇”。這樣的教學結果,從傳統意義上看,很容易讓我們產生自滿。干老師的教學另辟蹊徑。他從漫談童話入題,讓學生說自己讀過的、最動人的童話故事。在談話導入后,干老師先出示一組故事:《丑小鴨》《灰姑娘》《哈利·波特》《射雕英雄傳》《基度山伯爵》《瑯琊榜》。同時,他提問學生:“你看出其中的關聯么?”請不要以為這些作品是隨意組合的。經過干老師解讀,學生明白了所有的故事都是“原型故事”——丑小鴨的不同版本。干老師分析童話故事有一個“原型”,這個原型就是“丑小鴨”。這里說的“原型”是哲學所指的“原型”。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原型”的“變型”而已。例如,看到的椅子其實不是椅子,而是心中對“椅子”這一原型加工后的“象”。因為它與原型匹配,所以我們認定它就是那個事物。基于此,干老師認為:“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原型,就是“丑小鴨”——開始遭遇逆境,之后經過努力,境遇轉變,最后升級蛻變。《灰姑娘》就是《丑小鴨》的人類版,《哈利·波特》是《丑小鴨》的魔幻版,《射雕英雄傳》是《丑小鴨》的武俠版,《基度山伯爵》是《丑小鴨》的西方人物版;《瑯琊榜》是“丑小鴨”的古代宮斗版。”
緊接著,干老師基于這個“原型”,在課堂上創建了一個創編故事的大致“模型”。他將所有的故事創編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故事的開始,應有一個很平凡的男孩、女孩或者動物;第二個階段是故事的發展,主人公要遇到困境,感到自卑;第三個階段是故事的轉折,主人公可以遇到了幫助或者得到鍛煉;第四個階段是故事的結果,主人公成了英雄。至此,學生發現了一個很神奇的能幫助自己編寫出故事的框架。有了這個框架,編寫故事,學生只要填裝自己的內容就行了。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讓這個故事關于任何人,主人公遭遇任何事、實現任何目的。這樣,學生寫作的個性在編寫中得到最大的尊重,他們的創意得以展現。在熟悉故事的框架后,干老師給四年級的孩子提供了一篇例文:“一個男孩來到一所貴族學校,飽受冷落。故事開始,主人公遭遇讓人心痛的命運。之后,班級里興起了養蠶,而他卻因為受排擠而得不到蠶種。主人公在路邊的樹葉上撿到了很像蠶種的毛毛蟲的卵。后來,每個人的蠶種都順利孵化,蠶寶寶逐漸長大,而他的卵孵出來的卻是又黑又可怕的毛毛蟲。但此時的他,已經無法割舍,堅持喂養。最后,大家的蠶都化成了蛾,而他的毛毛蟲卻成了蝴蝶。”結合整個故事,干老師讓學生補充編寫故事的細節,也可以結合例文,編寫自己的童話故事。在“原型”的啟發下,每個學生都編寫出屬于自己的童話故事。每個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
觀察整個教學過程,我們沒有看到一個學生因為“寫不出”而畏懼,沒有看到熟悉的故事,也沒有看到對童話故事的簡單模仿,更沒有看到夾雜著道德教化的早熟與老成。我們驚嘆于這樣的教學結果。在課后對話中,我和干老師、高老師一同進行了總結反思。
一、教到“上位”才有效
此案教學中,“教”是居于寫作上游的,是教在構思,教在建模,教在原型。相比下位的“教”,教在文字,教在知識,教在技法,甚至是教在某一句話的推敲,教在童話中人物的外形、動作等重復性的描寫……上位的教,是真正寫作學層面的教,是有效的教。停留在寫作下游環節的教,更準確說應該是語言學層面的教,是無法真正抵達“寫”的高度的。它充其量只能是“作”,是一種制造,是一種簡單的加工、修飾。如果寫出來的文字不具備創造性,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就像“房屋”本身是空中樓閣,“裝修”的意義就沒有了。然而,我們卻在認真地“裝修”這樣的“豆腐渣工程”。反過來看,“教”在上位,“教”完成了有效的寫作建模,“教”給予了兒童一個屬于自己的故事模型后,就能看到期待的“勝景”——兒童沒有更多的束縛,擁有自由發揮的空間。這樣,“教”普照每一顆童心,讓每個學生寫出屬于自己的故事。
二、教在“本體”才有效
教,是服務寫作本體的教,讓師生都脫離和超越了對語言文字細節的糾纏。許多一線教師在作文教學中,非常注重對語言文字“對或錯”“美或丑”“優或劣”的評價,其實是期待通過評價抵達對文字美化的追逐。然而,“對或錯”“美或丑”“優或劣”這固然是寫作教學的任務之一,但絕對不是應然目標,甚至說不應成為教學中耗時較多的環節。對文字的推敲與打磨,更適合于一個成熟的作者,或者說有較多閱讀歷史、生活閱歷、表達經驗的寫手。對學生而言,過早地進入推敲琢磨階段,會耗損他們表達熱情,更可怕的是——會導致他們對文章構思的忽視,無法抵達寫作的上游環節,無法形成對文章的整體布局、宏觀設計的真正的寫作意識。因為,文字的糾纏,屬于語言學,而不是寫作學。糾纏文字地寫一輩子,都是在寫的下游打轉。經外力施“教”加工而成的所謂優質語言,也是一種假象,與作者本人的審美水平、心性發育、靈性程度、情感發展、意識水平等關聯不大。相反,不在意文字的精致化加工,著力于文章的構思,致力于故事框架設計,就切中了寫作思維,是把力氣花在刀刃上。“教”對了,就能釋放空間,讓學生有極大的表達自由,具備了言說的勇氣,確保其自如地將心中的故事寫出來,而不瞻前顧后、畏首畏尾。
三、教在“這一類”才有效
以前我們看到的童話故事教學案例,大多數是針對寫好“這一個”的精致化教學。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地累積,聚沙成塔、聚水成海式的教學,這樣對兒童表達不能說是沒有用處,但窮其一生還是無法讓他們感受到童話故事創意的樂趣。這樣,即使教了一百個,也無法讓他們領悟到童話故事寫作的核心密碼。也許有部分學生能在多次反復表達中悟出這一表達密碼,但那屬于天才,是優質生的專享。大多數學生會盯住眼前,在意“這一次”的成敗,會把自己逼入極致化的語言文字修改中,努力完成好“這一篇”。我們教師有沒有想過,這么做,幾乎是徒勞的?這么做,就是寫作教學不曾進步的根源?因為,我們一直在讓學生做“小孩不該做的事”。即便是修改,停留在語言文字的增、刪、補、換層面上,也是在修改中的最末端。對故事的構思、故事的框架、故事的創意等宏觀布局上沒有做出調整,沒有修正的能力,沒有發現問題的意識,沒有判斷后選擇地執行,是永遠也寫不出好故事的。因為,學生一直活在他們自己的認識范圍內,活在自己熟悉的表達圈子中。這就如同一只狗,咬住自己的尾巴,然后不斷地在原地旋轉,以為是走了十萬八千里,其實一步都未曾向前。
我們可以設想,“教在思維”之后,學生心中對“寫出一個故事”已經開始建模。模型一旦建好,就如同獲得授權——在模型之上自由發展;如同獲得一件秘器——在模型之上再度建模,填裝自己的想法,組合成新的模型;如同獲得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扇門,走進去,看到屬于自己的風景。這就是上位的教帶來的思想的啟迪,整個寫作的文心都開放了。
(責編 韋 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