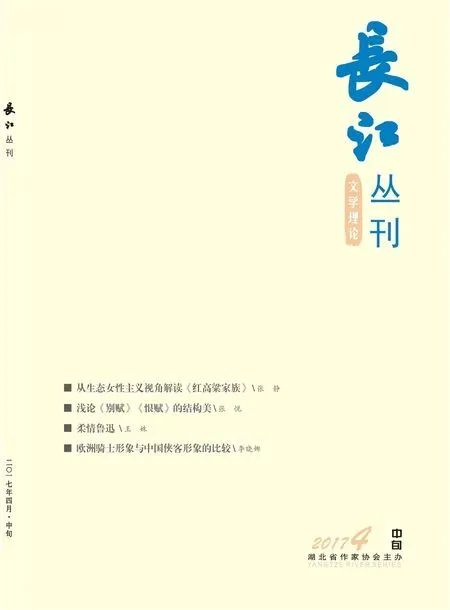從媒介議程設置理論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蘇 濱
從媒介議程設置理論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
蘇 濱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出現與媒體預測相反的“逆轉”,恐怕是美國主流媒體始料未及的。大眾媒介借助自身具有的議程設置功能影響著公眾的日常議程,使這場曠日持久的競選運動成為公眾日常生活中無法回避的內容。通過分析發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傳統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的交鋒,凸顯出在網絡環境下,媒介議程設置理論也在發生著變化,出現了網絡議程設置、民眾自我議程設置等新現象。
大眾媒介 總統大選 議程設置
一、研究背景
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中,總統選舉與媒介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從19世紀40年代的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到60年代約翰肯尼迪的電視辯論,再到2008年奧巴馬乘著社交媒體的東風入主白宮,這都表明美國總統大選離不開媒介。從報紙、廣播、電視,再到網絡新媒體,媒介在總統選舉中起到的作用更加凸顯。
比較具有戲劇性的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在這一屆大選的過程中,媒介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在大選開始后,傳統主流媒體呈現了“一邊倒”的站隊現象,美國前五十家媒體沒有一家支持特朗普。
與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不同,特朗普則充分發揮了社交媒體的優勢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可以說他充分利用社交媒體,把自己塑造成了“超級網紅”。特朗普借助社交媒體節省了巨額宣傳經費。善于利用社交媒體,給特朗普帶來的是一本萬利的營銷“快感”和令人瞠目的政治回報。
最終的結果是特朗普贏得大選,超出了美國主流媒體的預料。我們可以視為這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交鋒。從媒介議程設置理論角度出發,探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博弈以及對選舉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二、關于議程設置理論
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最初來源于李普曼在其著作《公眾輿論》中所提出的觀點,即人們頭腦中的圖景由何而來的問題。李普曼認為,新聞媒介體現著并轉而有力地支配著我們頭腦中的圖像。這可以看作是議程設置理論的雛形。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社會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新聞報道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新聞媒介能夠選擇并突出報道某些內容,從而使這些內容引起公眾的注意和重視。
麥庫姆斯等人在后續的研究中,多次強調議程設置的核心概念是顯著度的轉移,由媒介議程的顯著度轉移至公眾議程的顯著度。但是隨著互聯網的出現,新媒體的普及,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進一步拓寬,不在僅僅局限于傳統媒體,與此相對應的議程設置理論也發生了變化,也需要我們從新的視角來探討議程設置理論與媒體、與公眾之間的關系,例如媒介間議程設置、受眾自我議程設置等。
三、媒介與大選
(一)傳統媒體與大選
(1)媒體與社會階層。如果要探討此次美國大選中傳統媒體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媒體背后的因素,與社會階層的關系。在本次大選中,美國傳統主流媒體是為精英階層代言的,是受其控制的,而希拉里就是代表美國精英階層、社會頂層少數團體的利益。這也就導致了中下層普通選民關注的議題鮮有出現,主流媒體喪失了對新聞客觀性的堅守,加劇了美國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這也就導致了最終的結果,即在大選中,主流媒體紛紛進行政治性站隊,呈現“一邊倒”的支持希拉里。
(2)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在此次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美國排名前五十的紙媒沒有一家支持特朗普。晚些時候,《紐約時報》公布了10余家權威媒體的最新民調,絕大多數民調數據都顯示希拉里的民意支持率領先于特朗普。同時,這些紙媒大力宣傳希拉里的政治主張,打壓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并將其放大。除此之外,在兩者的電視辯論中,主持人也是質疑、甚至是嘲諷特朗普的政策主張。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通過大眾媒介營造一種認知,即希拉里是比特朗普跟適合當美國總統的,進而影響公眾的認知。簡而言之,為了維護精英階層的利益,媒體將特定問題進行包裝,然后再傳播給民眾,建構一種所謂客觀真實的新聞圖景,甚至以此影響民眾對于大選的判斷,實際上效果并不好。
因此最終的結果讓美國主流媒體大跌眼鏡,與媒體預測恰恰相反。媒體曾經“一邊倒”的支持希拉里,試圖以此來影響公眾的認知與判斷,但是最終并沒有取得顯著的效果,這說明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在此次大選中的作用是進一步弱化的。在新媒體時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時代,公眾獲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樣化,也更加便捷,不再是過去僅僅通過報紙、電視、廣播來獲得信息,傳統媒體對公眾的引導與施加的影響進一步減弱,公眾擁有更強的選擇與辨別能力,因此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在此次大選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新媒體與大選
(1)特朗普成為“網紅”。在傳統媒體紛紛支持希拉里的同時,特朗普則充分利用社交媒體來宣傳自己,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他在推特上有1030萬粉絲,在臉書上有990萬粉絲。特朗普把自己塑造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網紅,特朗普認為展現個性比營造形象重要,保持政治正確等于沒有新聞關注。他從一開始就頻繁利用社交媒體發布挑釁、有爭議的內容,或者是沒有證據的猜測、引發爭論的主張等來吸引網民關注。
(2)新媒體的力量。在社交媒體的沖擊下,美國主流媒體已處于下風。毋庸置疑,社交媒體已成為現代社會政治活動中越來越重要的傳播工具,它們也是作為傳統媒介權力的破壞者出現的。正常的預期是:被主流媒體遮蔽的意見會在社交媒體上自由表達并進入輿論,進而在公共領域中形成一種“聲音”。但在公共領域被嚴重侵蝕的情況下,此次大選中社交媒體上信息與意見的極端二元化幾乎與主流媒體毫無二致,因此,互聯網上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聲音被主流媒體有意忽視也就順理成章了。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戈夫曼提出的戲劇理論,把舞臺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是塑造和扮演的場合,后臺是掩飾和隱匿的場合。最成功的真人秀,本質上就是撕開舞臺間的幕布,把后臺置于看客眼前。而特朗普主動扯下了前后臺之間的幕布,沒有所謂的政治正確,敢于提出有巨大爭議的主張,借助社交媒體的力量,讓美國民眾耳目一新。
四、結論
2016年美國大選既是一場政治真人秀,也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激烈交鋒,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傳統媒體方面,美國主流媒體為了支持希拉里,并沒有堅守新聞的客觀性原則,對希拉里及其選舉活動大肆宣傳,進而忽視美國中產階層的普通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同時還多次進行所謂的民意調查,向民眾釋放希拉里能贏得競選的信號。大眾傳播可能無法決定人們怎么想,卻可以影響人們想什么,所以它們試圖通過媒體報道,影響公眾的想法。
另一方面,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也在發揮著議程設置的功能,在此次大選中,它的作用甚至是比傳統媒體更強。在網絡中,碎片化、個性化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網民關注,也更能進行傳播,特朗普深知這一點,并加以充分利用。雖然傳統媒體紛紛倒向希拉里,但是特朗普并沒有失去他的影響力,他的觀點、政策主張引起了網民的注意,甚至是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總之,他成為了超級網紅,讓美國民眾對他不再陌生。
從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它們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爭取公眾的認同。在新媒體環境下,由于信息傳播渠道多樣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效果受到弱化;同時,網絡對公眾的議程設置功能也被減弱了,還出現了受眾自我議程設置,公眾成為了議程設置的主體。由于網絡媒體具備有別于傳統媒體的新特征,受眾在從網絡中獲取信息時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比較小。同時網絡信息傳播的數字化,使得信息的復制變得非常容易,受眾只需要點擊轉發、分享或者復制、粘貼,就可以實現信息的傳播,實現議題在論壇、社區間滲透。除此之外,受眾的匿名性等特點使其在接受網絡信息時受傳播者的影響越來越小,反而越來越受自己本身的性格、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
[1]張軍芳."議程設置":內涵、衍變與反思[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10).
[2]惠耕田.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媒體因素[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0(04).
[3]李之文.新媒體與美國總統大選[J].新聞傳播,2010(06).
[4]王潤澤.談媒體的政黨傳統在美國大選中延伸[J].國際新聞界,2004(06).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
蘇濱(1992-),男,山東日照人,蘭州大學2015級碩士,研究方向: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