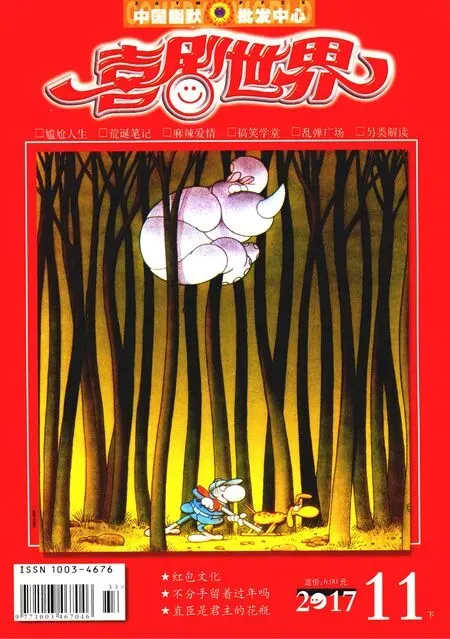下基層
★文/陳修平
下基層
★文/陳修平
十年前,我在市委黨校青干班學習。
那時候還沒有“八項規定”。作為全市科級青年干部里面的優秀代表和儲備干部,我們班的同學上課時都蠻認真的,但課余時間也都放得開,你請一頓,我請一頓,那時流行這樣,反正都能公家報銷。大家輪流做東,唯恐比別人請客安排的環境差了、檔次低了,似乎吃喝玩樂就是加強友誼的最好方式,就代表著珍惜聚在一起的緣分……
我們這兒的市委黨校在培訓結束前有一個保留節目——下基層,設置這個環節的初衷,本意是為了讓接受培訓的學員們近距離體察民情,但在那個年頭,慢慢地也就成了流于形式走走過場。
結業前,市委黨校安排我們班下基層的點是轄區一個縣的國營煤礦。聽說去煤礦,同學們都高興極了:“煤炭就是黑金啊,煤礦有的是錢,咱們這次去下基層一定要喝飛天茅臺,不喝白不喝!”那時候,飛天茅臺的價格賣到了一千六一瓶。
到了煤礦,班主任和煤礦領導商量后,特別決定讓我們這次下到井下看看。盡管對下到煤井心存恐懼,但我們作為年輕干部,表面上還是不甘示弱的,而且煤井下從來沒有去過,走馬觀花見識一下也無妨。大家抱著這樣一種心態,換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就跟著煤礦分管生產的副礦長下去了。
副礦長告訴我們,這次我們要下到煤井的四百米深處。剛進升降機時,我們還有說有笑嘻嘻哈哈的。但隨著升降機不斷下降,我們的心也跟著莫名地緊張起來,到后來大家幾乎都沉默不語了。雖然從沒下過煤井,但電視電影里的煤礦事故還是見過不少……
到了預定地點,煤井深處真是黑的世界呀,黑得令人不由自主地恐懼。就是在這樣黑暗的地底深處,我們看到不少頭上戴著頂燈的煤礦工人在各自的掌子面上一鎬一鎬地挖掘。他們每挖一下,我們似乎就感覺到了頭頂上煤層的震動,內心也就揪得更緊,雙腿也不禁輕微地哆嗦。
“你們一個人一天大概能挖多少煤?”還是班主任打破了沉默。既然下來了,還是應該了解點兒什么。
“兩噸左右。”
“一噸煤能賣多少錢?”班主任又問陪在身邊的副礦長。
“兩百。”
也就是說,一個煤礦工人冒著生命危險辛苦勞動一天產生的價值為四百元。
“井下也沒什么好看的,領導們還是上去吧!”或許是顧及我們的安全,或許是不愿影響挖煤工人,過了幾分鐘,副礦長就提議我們上去。
當升降機上到地面時,我們都不禁長舒了一口氣,但我們已經沒有了剛來煤礦時的嘰嘰喳喳,我們之間似乎被一種無形的沉默的氣氛所籠罩。
座談會上,礦長照例照著打印稿介紹了一下煤礦的安全管理和經濟效益,我們都拿出本子認真地做著記錄。會后,吃中飯,煤礦領導陪著我們在食堂旁邊的包廂里用餐。正像我們來之前嚷嚷的那樣,煤礦確實很有錢,對待我們也確實很大方,每張桌子上都放了四瓶飛天茅臺。我們心里也清楚,說不定以后我們這班同學里面就會有人到這個縣里當領導,說不定還會分管這個煤礦的。
但是,這餐飯,我們都沒有去打開擺在面前的茅臺,就連煤礦領導幾次要開酒,都被我們一致用堅決的語氣勸阻住了。班主任似乎覺察到了什么,就跟煤礦領導說下午還有活動,只吃飯,不喝酒了……
如今,十年過去了,當年我們在市委黨校青干班的那班同學基本都升到了副處級,多人還升到了正處級,但幾乎沒有一個成為紀檢部門拍打的“蒼蠅”。哦,記錯了,有一個當了縣長的同學在“八項規定”出臺后仍然大吃大喝被查處了,還被查出了一連串問題,就是下基層那天因請假而沒有去煤礦的一個同學。
(摘自《小說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