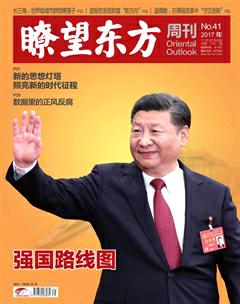活化歷史建筑的“戰役”
李振
一面要與時間賽跑,一面又要與開發商博弈
如若不是因為謝夏祥與李永泉的冒險,廣州市泰康路84號的歷史痕跡,可能會被鋼筋水泥“吞噬”。
2016年11月,建筑師謝夏祥與合伙人李永泉在這里成立了專門活化歷史建筑的公司,歷時4個月、耗資120萬元,將廢棄的騎樓打造成歷史文化活動場所,同時也開啟了他們的新事業——通過保護性開發,賦予歷史建筑等文化遺產新的生命。
謝李兩人的冒險能否成功,目前還難有定論。多位受訪者向《瞭望東方周刊》表示,歷史建筑活化是一場曠日持久且主體復雜的“戰役”,一面要與時間賽跑,一面又要與開發商博弈,任重道遠。
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對歷史建筑遺產充滿保護熱情的民間力量投身“戰場”。自2008年起,歷史建筑活化的民間力量大增,僅廣州一地的文化保育組織就從5個迅速增長到50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像謝夏祥一般,“不為別的,就是不忍心讓有價值的建筑被時代遺棄。”
一座廣州城,半部近代史
李永泉每天最愛干的事,就是穿梭于廣州老街巷,觀察和研究歷史建筑。建筑學出身的李永泉,對廣州建筑進行過深入研究,尤其對歷史建筑充滿感情。
在他看來,歷史建筑串聯起了一部城市文明的“編年史”。廣州有著2000多年的歷史,而廣州的城市文明在中國歷史上最凸顯重要性的階段,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國和改革開放時期。

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為番禺沙頭“秀才屋”進行了拍照,希望對歷史建筑進行數字化保存
事實上,李永泉的觀點很容易在廣州的歷史建筑上得到印證。
一座廣州城,半部近代史。作為晚期一口通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廣州一度是東北亞重要的貿易之都。廣州西關自明朝便是商賈聚集之地,清末十三行的興旺,更令西關一帶成為廣州城市文明的代表性地段。
“行商大院、西關大屋成為那個時代廣府民居的標志性建筑。”李永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其布局主要圍繞中軸線上的廳堂左右對稱,每廳為一進,全屋二至三進,靠天窗采光通風。”
同樣,騎樓建筑的流行明顯是伴隨著廣州商貿文明發展而來的。
20世紀初,廣州商貿興起,城市最先升級的是馬路。因廣州氣候炎熱多雨,要求商貿場所要有避雨遮陽的功能,于是,彼時的建筑師將西方古典建筑與廣州傳統建筑結構結合,設計出了廣州特色的騎樓式建筑風格。
“騎樓的商業實用性非常突出。”李永泉說,“它的建筑立面分為樓頂、樓身和騎樓底三個段式,騎樓使馬路一邊的人行道相互連接,形成一條長廊,既便于來往行人遮陽擋雨,商店也可敞開鋪面陳列多種商品。”
“東山洋房”的流行則始于清末,盛于民國初年。
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寺貝通津、恤孤院路、培正路一帶興建了學校、醫院、福音堂等西洋建筑;民國時期,廣州在此設立了市政公所,這一帶逐漸成為廣州權貴階層聚集地;1915年到1937年間,大量華僑回廣州投資安家,中西合璧的“東山洋房”成為記錄那段時光的重要載體。
梳理了這些廣州代表性歷史建筑形態,李永泉告訴本刊記者:“建筑在某種程度上記錄著廣州的文化血脈,無論是建筑風格,還是房屋功能,抑或是建造地點,都烙下了時代的獨特印記。”
城市升級的反思
李永泉覺得,城市升級就像人在社會中的成長,總是伴隨著新老交替。
“騎樓建筑的商業價值突出,西關大屋就逐漸退出舞臺;高樓大廈的居住功能完備,騎樓也逐漸退出舞臺。”但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城市升級,才有新的建筑形式補充到這部“編年史”中,而新老交替恰恰利用了時間的藝術,令多樣化的城市建筑存在于同一空間。
走入街巷越深,他越能發現廣州這座城市在成長中為建筑帶來的獨特魅力。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州城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者。但老廣州人一直聚居生活在越秀、荔灣、海珠等老城區,而外省人則會較多聚集在天河、白云等周邊市區。”李永泉說。
老城區建筑保留著原汁原味的廣州味道,承載著廣州過去的城市記憶;而新城區建筑則適應了新時代的特色,代表著現代都市的新發展。
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城市需求,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是“新老交替、一拆一建”,用循序漸進的城市更新方式,彌補老城區的衰老。
“廣州就是用這種方式,在一拆一建中從傳統城郭過渡到現代都市的。這種城市升級帶有成長性,并非大拆大建、一切推倒重來式的‘建新。歷史建筑得以保留,多半要歸功于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李永泉說。
然而,在李永泉看來,歷史建筑最大的威脅也來自于城市升級。
上世紀80年代,城市升級開始注重迅速提升居住環境,對歷史建筑保護意識不高。據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博士王茂生的統計,僅1988年荔灣區金花街改造項目,拆除的歷史建筑就高達155300平方米,大量歷史建筑被直接夷為平地。
金花街模式成為這一時期舊城改造的主流辦法。豪華住宅小區破壞了西關舊城區的風貌,它插在上下九路頗有風情的騎樓街上,插在老西關的一片舊式大屋之中,顯得格格不入。
這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和批評,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樣的方式“破壞了老西關的文脈”,歷史建筑“敵得過百年風雨,卻輸給了轟鳴的推土機”。
與時間賽跑
與謝夏祥、李永泉專門成立公司來活化歷史建筑相比,攝影師劉偉倫投身“戰場”就顯得形單影只。
劉偉倫是地地道道的廣州人,從小生活在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騎樓里,目之所及都是有些年份的老房子。
“小時候常路過一些花園建筑,園林、石柱、拱門,配上傳統的青石磚,兩種迥異的建筑風格偏偏結合得天衣無縫,美得讓人著迷。”劉偉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自童年起,他就萌發了對歷史建筑的喜愛之情。
2008年,劉偉倫第一次意識到,有相當一部分的歷史遺跡已在歲月的洗刷中湮滅,城市里每天都有一些老建筑在無聲無息地消失。“特別好的老房子,‘咚的一聲就不見了,等你聽到消息奔過去,只剩下滿地殘垣斷壁,真的很痛心。”他說。
面對廢墟,劉偉倫有了拍照記錄歷史建筑的想法,希望用這種方式告訴大家曾有這么美的建筑存在過。“一座城市如果沒有自己特色的東西就沒有味道了,文化保留下來了,世界才會豐富多彩。”
劉偉倫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掃街”,不僅把目之所及的老建筑拍進鏡頭,還進門去“采訪”,這也是劉偉倫“口述歷史”計劃的雛形。
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找到不被史籍記錄的故事,不是宏觀的事件,而是不同人眼中的生活和一座座老建筑的來源經歷,從個體層面來解讀、補充歷史。劉偉倫拜訪過很多人,影星、官員、巨賈、作家的后裔,如同在跟時光賽跑,要趕在故事被遺忘之前盡可能地記錄。
“那些曾經居住在老建筑里的老人在逐漸逝去,他們的后人也在一天天老去,如果現在不做,可能那些老建筑的故事就會永遠地消失了。”劉偉倫說,“終有一天這些建筑會消失,我希望那個時候,我所做的還能提供給人們一個看到過去的窗口。”

廣州市一座騎樓建筑的圓形窗廊,遠處是街道上的車流和樓廈群
然而,劉偉倫總是感嘆:“太遲了!”
在他看來,活化歷史建筑成了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戰役”:“我們的力量太弱小,保護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城市更新的速度。”
兩座大山
歷史建筑活化工程可謂浩大。據統計,我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登錄的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國保單位僅4296處。
廣州市的不可移動文化遺產中,屬于非國有的占比較大,其中僅有約8.8%的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為公房和代管房,大部分為住宅,有住戶在居住。
非國有歷史建筑多為華僑房,溝通成本大,另外還有一房多業主,意見不統一等情況,成了職能部門進行積極保護的障礙,導致“活化”基礎較差。
產權復雜猶如一座大山,成了擺在歷史建筑活化面前的首要問題。
資金難題,也是橫亙在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廣州大學嶺南建筑研究所教授湯國華看來,歷史建筑活化與文物保護存在很大差別:“文物保護至今已有幾十年歷史,國家對文物保護的政策、法規、資金保障都有規定,已形成一套完善的文物保護方法。而歷史建筑保護近幾年才提出,各項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尤其是資金保障的問題。”
“資金從哪里來?外立面的改善是不是由政府出錢?民居內的設施改善是不是全都由居民負責?目前仍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湯國華說。
不應只是保護
恩寧路吉祥坊最終沒有躲過被拆除的命運。
每當提起這件憾事,劉偉倫都十分心痛。實際上,劉偉倫早在多年前就通過“口述歷史”了解到,這里聚集著大量的粵劇名伶故居。為了積極向政府建言,他聯合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的成員組織發布了《廣州西關粵劇名伶故居手繪地圖》和“導賞”活動。
湯國華也曾建言,“吉祥坊1號、3號、5號、9號和11號都是民國時期的民居,吉祥坊1號體現清末官宅生活,粵劇名伶故居體現粵劇發展。而這些歷史記憶,是在街區中發生的,與周圍的人和事相互交織,并非孤立,應該連片保留。”
但是,吉祥坊的多數歷史建筑還是難逃被拆除的命運,只剩下屋頂有著小花園的1號樓。
在湯國華看來,吉祥坊難逃被拆命運,關鍵在于沒有充分活化利用。“應該重視歷史建筑如何活化利用的問題。歷史建筑的保護并不只是公布名單,后面還有第二步、第三步,都需要好好斟酌。”
多數業內專家也表示,要想通過單純的保護來留住文化遺產,事實上是很難實現的。政府對于歷史建筑有專門的資金維護,但往往陷入了“維修-空置-衰敗-再維修”的怪圈。
單純保護不但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客觀上也很難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具有的諸多價值被充分展現出來。不少學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如何在不破壞文化遺產的純粹性與原真性的前提下,對這些文化遺產進行科學有效合理的再利用,使保護與開發能夠“同時并舉”,變“輸血”為“造血”?
馨園的活化給出了一種答案。
馨園位于廣州越秀區東山口,前身是民國第一任警察署署長的官邸,原名永昌園。在東山老城區的新河浦、龜崗一帶,是廣州現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層院落式傳統民居群,高高低低的復式別墅共有600多棟,多為民國時期歸國華僑和軍政官僚所建。其中,僅有6棟被列為歷史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廣東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以下簡稱“文保院”)院長劉峰牽頭白天鵝酒店管理集團,對馨園這座百年官邸進行活化,如今“馨園?白天鵝”作為一所古建筑酒店,已成為廣州新晉的文化地標。
“文保院已經成立了文創投資部,嘗試尋找具有深厚產業運營能力的企業聯手,著力對改造后的古村落、工業遺產及歷史建筑進行活化再利用。”廣東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副院長馮卓思告訴《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