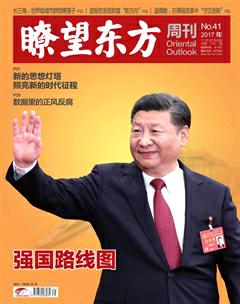什么才是中年真正的失敗
這樣的旅行,也許是恢復青春的一種斗爭
陳思呈:專欄作家,已出版《我虛度的那部分世界》《神仙太寂寞,妖怪很癡情》《每一眼風景都是愉快的邀請》等著作
前陣子,手捧保溫瓶的搖滾樂手讓我們震驚于中年危機的普遍性。我們意識到,年齡像一個咻咻作響的野獸,一直蹲在生活的某個角落,伺機將我們的活力吞服。
2016年秋天我有過一次長途旅行。在年輕的時候,旅游曾是我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中間幾年因為生育原因而停頓。重新開始旅游的時候,變化多得令自己吃驚。年輕時在旅途中一觸即發的激情,已經難以被喚起了。旅途中,我變成了真正的旁觀者,真正的過客。風景像立體的明信片,我遇到的人不再與我相關——我無法在他們的臉上看到故事,我無法忘掉我的生活,無法在火車上,在一個陌生的異鄉,喚起另一個我。
我想,這可能就是中年。
有兩部電影,都是講中年的狀態。
一部是賈木許導演的電影《破碎之花》。電影中,憑空知道自己有個私生子的中年男人唐尼,逐一回訪當年的老情人。他看著那些和他一樣已經變老,但又還沒有老到可以不再掩飾的女人,各種不同的際遇把她們在各自軌道中夯實,曾經親密的他在她們的生活里出現,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局外人。他這一場歷程,仿佛就是去確認:中年人,就是成為彼此生活的局外人。
青年時光就像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最活潑的鉀鈣鈉鎂鋁,與世界的能量交換如此頻繁,隨時遇到的一個人都可以讓你掉頭拐彎,走上計劃外的線路。
中年,不再如此了。我們與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人,都很難深入地嵌入對方的生活。
另一部電影叫《遠方》,是土耳其導演錫蘭的作品。攝影師馬姆生活在伊斯坦布爾,他接待了鄉下來的表弟尤素夫。尤素夫很想在這個城市立足,舉目無親的他需要表哥的幫助,但是馬姆拒絕了他很多的求助,包括做他的擔保人。
聽起來很冷漠,但實際上不過是馬姆看到了盡頭的一無所有。對于尤素夫來說,伊斯坦布爾是遠方,而馬姆則在影片最初的閑聊中就說道:所有的地方最后看起來都一樣。
沙龍上,馬姆的朋友對他說:“你記得我們曾經爬到雷科詩山的山頂,就為了能得到白山谷一個更佳的攝影角度嗎?你常說,你應該像塔克夫斯基那樣拍電影……”馬姆訕笑著打斷道:“攝影已經完蛋了,伙計。”他的朋友激動地說:“不,它沒有,群山也沒有。也許是你自己已經完蛋了。在死亡來臨之前,你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死訊。你沒有權利埋葬自己的理想……”
馬姆的狀態是很多中年人的寫照。對中年人來說,似乎是沒有遠方的。他們被巨大的慣性推著前行,很少見到改變的機會。旅游變得乏味——仿佛只不過是換一個地方睡覺,看著更立體的風景。
但我想,更艱難的旅游也許可以改變這種感受。比如說,那種連上廁所都困難的、在拖拉機上顛簸一整天的旅游。
那樣的旅游,它的作用是喚起我們對慣常舒適生活的陌生感。我所習慣的舒適,在僵化我,從生理,乃至心理。讓我覺得自己只能適應穩定,讓我覺得只有一條路:要活得更優越,更舒適,更便利。
在赫拉巴爾的小說《過于喧囂的孤獨》中,廢紙打包工古怪地引用黑格爾的教導,“世界上唯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結、垂死的形態,唯一可喜的是……通過斗爭而恢復青春”。
這樣的旅行,也許是恢復青春的一種斗爭。多年前曾聽到吾友張曉玲說,她曾與幾個同學帶著很少的錢騎車出游,整整兩個星期,在長江三角洲平原上游蕩,從這個鄉到那個鄉,有時候住在橋洞里,有時候住在堤壩上,有時候住在江邊廢棄的小屋里。回家時,形同鬼魅,身上全是被蚊蟲咬出來的紅點,曬傷的皮膚一層層往下蛻皮,非常黑,非常瘦,頭發散發出難聞的餿味,但是眼神湛亮。曉玲說,她從那時便已明白人生最壞的可能性,知道人生退讓到底,不過是重返自然,赤貧如洗,并無可懼。
日子越過越好,但我們對生活的適應性的衰退,對僵化的不自覺,以及略有動蕩便隨時升起的不安,也許才是真正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