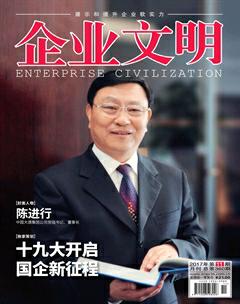一種生命形式的躍動
趙武成
舞蹈藝術可謂博大精深,不僅全面展現了一個時代不同民族的風俗風情,還享有極高的文化藝術內涵,其廣泛地存在于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藝術文化體系中,因此,決定了其多元化特點。隨著電影藝術的出現,舞蹈藝術開始與電影藝術相融合,由于其包容性、互補性強,因而極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藝術審美價值,增強了影片的主題思想與文化內涵。
當舞蹈與電影美麗邂逅,其伴隨著二者的融合應運而生,并顯示出了強大而驚人的生命活力。舞蹈元素對于電影而言,無疑是電影眾多藝術表現形式中最為引人矚目的一種,其運用賦予了電影更持久、強烈的感染力、魅力、表現力,使得電影的主題表達更為傳神、生動、到位,使電影成為最具藝術魅力的類型。而電影所運用的蒙太奇表現手法,實現了舞蹈場景同時空之間的自由切換、穿插,拓展了舞蹈藝術的深刻內涵與強大的藝術張力。從觀眾視角出發,由電影鏡頭對舞蹈藝術的審美表現加以安排,為觀眾帶來了無窮的視覺感受,為舞蹈創作帶來了全新的思路。
電影是集舞蹈、音樂、美術、文學、戲劇、繪畫等多種藝術形式于一體的綜合性視聽藝術形式。在電影中,舞蹈藝術借助于跳躍的手法,對電影的主題思想加以詮釋,展現主人公的喜怒哀樂等情緒,給觀眾浪漫而又脫俗的藝術體驗。當電影、舞蹈藝術二者相融合后,電影獨特的蒙太奇手法,促使舞蹈藝術更顯立體化、審美化,也賦予了舞蹈藝術獨特的敘事、烘托氛圍、塑造角色形象等功能。由此可見,舞蹈藝術恰到好處地融合是成就一部電影作品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也是借以電影彰顯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電影中,很多圍繞著影片劇情所設計的有機融合的舞蹈,正如電影的精魂,于每個動作之中,向觀眾彰顯了電影的生命與活力。例如,在戲劇大師卓別林的作品《淘金記》《大獨裁者》中,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各種肢體動作,這正是早期電影所展現的舞蹈元素。隨著電影的進一步發展,百老匯歌舞被廣泛地運用其中,有些甚至被改編翻拍為電影,深入促進了二者的有機融合。例如《雨中曲》等就被公認為享有極高藝術價值的歌舞電影,在影片中,吉恩·凱利在漫天雨中一邊歌唱一邊跳舞,為廣大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電影的推動下,舞蹈也早已深入觀眾的思想、生活各個角落。在電影中,舞蹈片段、場景除了為觀者提供了視覺審美享受以外,還借助于舞蹈充分地表達了電影情緒與主人公感情,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內心情感的曲折變化,也為影片注入了強大的活力。電影技術的飛速發展,為二者的完美融合提供了途徑。例如,在影片《十面埋伏》中,章子怡一席“仙人指路”舞驚艷了無數觀眾,彩衣飄飄的她揮揮長袖,舞步輕盈猶如仙女一般,飄逸而韻美,使萬千觀眾賞心悅目。
在電影中,舞蹈已經由一門獨立而生動的藝術形式,轉變為了一個表情達意、參與敘事的重要元素,舞蹈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交融,不僅產生了獨特的審美特性,還衍變出了很多新的藝術功能:
第一,抒情性。這是舞蹈藝術在電影中最為顯著的藝術功能。舞蹈作為一種發自表演者內心情感的一種外在藝術形式,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樣,舞蹈肩負著抒發人類情感之重要使命,其實質在于抒情,而情感也是舞蹈藝術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本質生命力。在電影中也是如此,舞蹈藝術表演肩負著影片人物的情感發展。觀眾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每每看到舞蹈段落表演之時,往往會難以自制地將自己所經歷的所見、所聞同作品相聯系,試圖找到情感的共鳴,繼而滋生精神上的聯想、想象,借以自我經驗、人生經歷,對這部作品加以補充、完善。在這一過程中,觀眾深刻地體會到了電影的思想內涵及其所富有的更為廣闊、深刻的生活內容。舞蹈元素之抒情,在電影中大量使用,不僅豐富了電影劇情之敘事,還活躍了影像畫面之語言,促進了劇情的發展與人物矛盾的激化。如:在電影《夜宴》中,舞蹈已經超越了視覺語言形式,同劇情深刻地融合于一起,深刻地傳達了各人物的情感變化。當跳《面具舞蹈》時,太子的舞步、肢體十分放松,并無規范化的動作,一切都樂而動,這充分展現了其內心超然灑脫的心境和與世無爭的心態。而當在夜宴獻舞之時,太子舞步沉穩而猛烈,極具節奏感,肩部不停地發力,扭動著身體,展現了他內心的動蕩與情感的復雜,也體現了其復仇之心。再如:在《英雄兒女》這部電影中,女主角王芳成為志愿軍戰士后,其內心的激動、興奮難抑,影片就采用了一段朝鮮民族舞蹈傳達了自我內心的激動與喜悅之情。
第二,舞蹈還能夠銜接劇情進展,烘托場景氛圍,推動故事發展,塑造人物形象,展現電影主題。在電影藝術中,采用蒙太奇技術手法,將各種分散的鏡頭有組織、有節奏地加以拼接,構成一部具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影像,為觀眾帶來生動而明快的審美體驗,如此手法不僅提高了電影藝術審美價值,更使得觀眾從多角度、多層面欣賞民族舞蹈的美。如在印小天、張靜初等演員所加盟的電影《花腰新娘》中,由12個妙齡少女所組成的舞龍,賦予了彝族“煙盒舞”以全新的生命力,并將古老、傳統的民族舞蹈同現代、時尚元素加以融合,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聽覺沖擊。
第三,舞蹈使得影片敘事成功地形成了“內”“外”兩大節奏。電影之“節奏”,就像是一種具象的注意力,這并非單純地控制各鏡頭間的時間關系,還必須掌握好各鏡頭的時間延伸及其所激發并滿足注意力運動的所有結合。舞蹈就像是在流動中的藝術形象;就像是一種“虛幻的、力的王國”,而非現實、肉體所生成的力,是由舞者虛幻而張力的姿勢所創造的力與作用,其有自身獨特的運動規律,而該規律所需遵循的一點即節奏。若沒了節奏,舞蹈就如一盤散沙,成為了毫無意義的肢體動作。例如,在影片《夜宴》的片頭,男主角頭戴面具,手握利刃,時而翩翩舞動,時而靜若處子,而女主角舞姿如牽線木偶一般,時而輕盈,時而沉穩,越人舞的呈現將觀眾帶到了五代十國時代。
第四,舞蹈藝術營造了影片虛幻的空間,同劇情的發展和敘事的真實空間交叉并行。作為電影感知客觀世界的主觀表現形式,舞蹈藝術依據事物的邏輯順序和因果關系,對客觀時空關系加以反映,而舞蹈作為一個虛幻的時空,是演員對時空感知之后的主觀再創造,也是客觀時空在舞蹈藝術空間中的二次構建。舞蹈與影片光影的結合,更好地拓展了空間,刻畫了影片復雜而難以表露的真實精神世界,也將觀眾情緒成功地帶入到了影片情節氛圍之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敘事格調。例如,在電影《黃土地》之中,導演借助于大段的民俗舞蹈藝術形式,渲染了劇情發生的時代背景與文化氛圍。在影片中,當狂放的“安塞腰鼓”震響起來之時,其熱情似乎霎那間席卷了整片黃土地,引發了人們對延安秧歌舞蹈的深刻記憶,為觀眾帶來了一股生機與激情。
總而言之,舞蹈藝術與電影藝術歷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兩種藝術形式。電影愛上了舞蹈,而舞蹈藝術又為電影錦上添花,為其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電影與舞蹈藝術密不可分,只有將二者完美融合,方可將電影事業推向輝煌。
(作者單位:四川藝術職業學院)
(責任編輯:郝幸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