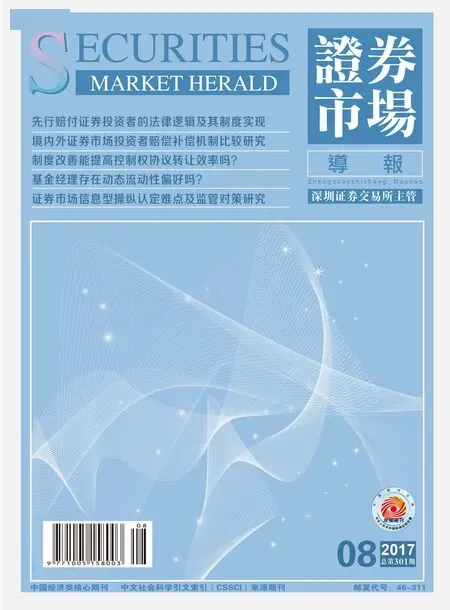推動上市公司去杠桿需標本兼顧
實體經濟杠桿率的變化過程,反映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演變。以往過于依賴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方式,導致我國非金融實體部門的杠桿率高達141%,在國際清算行所選取的13個國家中排名第一。上市公司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面臨去杠桿的重任。自2000年起,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持續上升10余年,至2013年達到階段性高峰,隨后開始緩慢下降,2016年末為59.84%。其變化過程,與經濟增長速度、信貸投放量等高度相關。
在結構上表現為三大特征:一是重資產公司負債率高,輕資產、服務類公司負債率低。資金消耗型的房地產、建筑業負債率最高,近5年維持在75~80%之間;制造業、交通運輸、水利環境、租賃和電力燃氣等行業平均負債率在55~65%之間;文化、衛生、住宿餐飲、教育、信息傳輸和軟件等行業,平均負債率在45%以下。二是制造業公司在產業鏈上分化明顯,上中下游負債率依次遞減。鋼鐵、石油冶煉、化學纖維、有色金屬等上游行業的負債率平均在60%左右;石油加工、玻璃制品、電器及機械制造等中游行業的負債率平均在50~55%之間;酒精飲料、食品、紡織服裝、家具等下游行業的負債率平均在40%以下。三是國有企業負債率高,債務體量大。2016年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負債率分別為63.19%、60.55%和52.18%;在債務體量上,央企、地方國企、民企的債務比例分別為48.95%、28.22%和22.83%,國有企業的債務體量合計占比將近8成。
整體上,上市公司經營狀況較為穩定,債務風險可控。但是,四大局部性、突發性風險隱患也較為嚴峻。一是利息費用嚴重侵蝕上市公司利潤。上市公司2016年利息費用占利潤總額的比例為18.97%,260家公司的利息費用占比超過50%,31家公司因為利息費用而虧損,徹底淪落至為“債主打工”。二是部分行業和公司的財務風險加大。69家公司的年末現金余額小于全年的利息支出,其中23家是ST/*ST企業,財務風險和退市風險不容小覷。此外,部分鋼鐵和房地產企業杠桿率高、債務規模大,債務風險正在逐步累積。三是聯合擔保、過度擔保可能會帶來連鎖反應。截至上年末,43家公司擔保額超過全年營業總收入的50%,16家公司擔保額超過了全年總收入;11家公司擔保額超過了總資產的40%,2家公司擔保額甚至超過了總資產。四是局部風險可能會通過金融機構和債券市場蔓延。目前大部分債券主要持有者為金融機構,一些機構持有單一債券余額巨大,一旦違約,風險可能順著這些機構蔓延至整個債券市場。此外,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連續5年上升,不良貸款撥備率最近兩年也大幅下降。
面對復雜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去杠桿必須要兼顧當前和長遠,力度和節奏要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避免政策上的操作風險,防止在化解風險的過程中激生出新的風險。
本質上,去杠桿僅是一個手段,與其它任務相協調以提高要素流動性與生產率。在這個過程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深化國企改革、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是固本之變。徹底摒棄“唯GDP論英雄”的發展觀,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提升增長質量上下功夫,是去杠杠的關鍵。在國企改革“四梁八柱”架構逐漸形成的時刻,深化落實各項措施推動國企去杠桿。依托資本市場,積極推動國有企業整體上市,鼓勵符合條件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資產證券化,鼓勵地方政府利用資本市場平臺優化債務結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是去杠桿的最直接方式,這需要進一步完善股票發行、退市等基礎性制度。
固本之變必然難于一日之內見成效,防控和化解杠桿風險,還需多方面統籌。在“減分子”方面,按照“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的整體思路,鼓勵企業債務重組、并購重組,加快推動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出清。在“擴分母”方面,堅持IPO的常態化,積極發展股權再融資。在“杠桿轉移”方面,鼓勵發展創新性金融工具,規范發展永續債、名股實債等新型投融資工具。此外,還需加大監管力度,防范風險累積蔓延。及時對上市公司隱患進行全面排查,抓早抓小;加強相關公司和金融機構跨領域、跨部門業務的監管協調;嚴格規范、從嚴審核債券類產品的信息披露;健全基于大數據的風險監測和預警系統,及早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守住風險底線。(文/于忠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