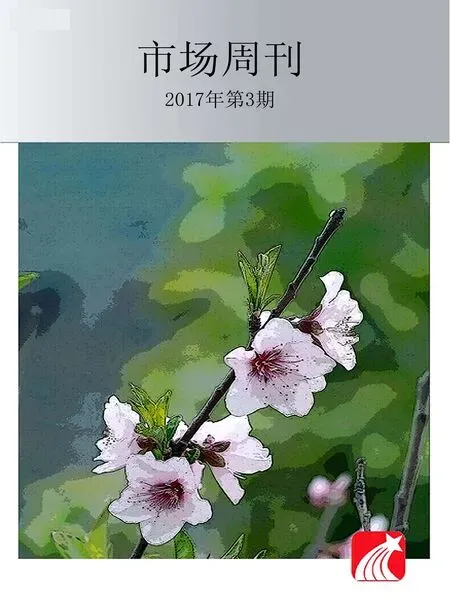論目標公司董事信義義務的法律規制
徐華
法學研究
論目標公司董事信義義務的法律規制
徐華
我國反收購法制亟待完善,目標公司董事于反收購中可能損害目標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利益,通過信義義務規制來平衡各方利益值得研究。制度完善首先應回歸董事信義義務的法理基礎,包括股東利益至上原則、目標公司股東與董事的利益平衡、中小股東保護原則以及目標公司債權人保護原則等,剖析現行信義義務法制缺憾所在,提出制度完善路徑應從明確董事信義義務具體內涵和外延、完善少數股東的訴權救濟、反收購決策權歸于股東(大)會、法律體系的內外部統一。
信義義務;注意義務;忠實義務;利益平衡
公司收購與反收購,其目的在于目標公司控制權的取得或維持,在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的“攻防大戰”。目標公司董事身處利益沖突之中,督促董事盡到信義義務,確保其不利用反收購措施以維護私利的手段,是反收購法制建構之核心。法制的建構須從其法理基礎做出本源審視,評判現行法制是否符合立法主旨。
一、董事信義義務規制的法理基礎
(一)股東利益至上原則
隨著公司社會責任理論與實踐發展,股東利益至上原則的根基發生動搖,但仍至關重要。《收購管理辦法》第8條:“被收購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應當公平對待收購本公司的所有收購人。被收購公司董事會針對收購所做出的決策及采取的措施,應當有利于維護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不得損害公司及其股東的合法權益。”該規范明確在反收購中董事負有法定忠實義務,也是判斷反收購行為是否合法的基本標準。公司的固有特征之一是營利性,作為股東經營管理者的董事采取反收購措施之時,應當服從于此目標約束。
(二)目標公司股東與董事的利益平衡
反收購法律關系的真實利益主體是目標公司股東與董事,利益平衡也在其中。在反收購中講求利益平衡,在于公司經營模式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董事利益與公司利益、股東利益并非完全重合。董事的自利性與逐利性可能催使其濫用職權,采取不恰當措施妨害公司合并。在收購實務中,區分目標公司董事行為的真正目的很難操作。要期望董事在做出重大決策時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股東利益無異于癡人說夢。
(三)目標公司中小股東權益保護
相較于收購者、目標公司董事和控制股東,目標公司的中小股東明顯處于弱勢地位。董事實施反收購措施時,往往難以全面顧及全部股東利益,中小股東極可能地成為附屬,因而存在著董事與公司之間的利益矛盾。實踐中收購者為促進收購順利完成,往往給予持股較多的股東以一定優惠條件,這無疑是對中小股東的不公平待遇。董事義務從表面上源于公司法與公司章程之規定,實質上源于董事與公司之間存在的某種特殊的法律關系。
(四)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原則
反收購過程中,目標公司股東關注重心偏向于股票短期盈利,而非公司可持續發展收益,因此易導致董事、股東貪圖較高的溢價收益,而對收購公司的收購意圖、能力、發展預期等因素漠不關心,將公司股權拱手轉讓。然而實踐中往往存在這樣的現象,即收購公司在收購成功后掏空目標公司的資產退出,嚴重損害公司及債權人的利益,產生該現象的一項重要因素是董事未盡必要信義義務,對公司經營信息知之甚少的債權人,其利益需要董事盡到合理的義務以維護債權人債權實現的可能風險,債權人之保護亦屬重要。
二、我國現行董事信義義務法制評析
公司法未對董事注意義務做出全面詳盡的規定,僅在第148條和151條設置了勤勉義務并作出基本架構,第149條列舉董事的禁止行為,《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第97條和第98條規定對目標公司做集中規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014)第8、32、33、34條等確立了信義義務的基本框架,《證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條例》及《禁止證券欺詐行為辦法》等規范較少涉及上市公司反收購。公司法對董事的注意義務除了原則表述之外,幾乎未涉及任何具體的內容。此外,現行公司信義義務法未對注意義務作出屆分,也未對其行為模式作出分類歸納。同時,呈現出注意義務功能面臨弱化的局面,只規定了董事勤勉義務,同時董事注意義務沒有到位規定,而勤勉義務僅是注意義務的項下內涵,涵蓋范圍上注意義務寬于勤勉義務,以勤勉義務規范替代注意義務,上下位顛倒而有漏洞。董事勤勉義務的認定標準未臻清晰,因而產生可訴性適用疑問。其三,對于忠實義務的內涵和外延的規定,公司法“規定+列舉”模式并不全面。該立法模式仍停留在自我“經濟利益沖突”的矛盾解決上,傳統思維上稍顯僵化,對于其他形式的個人目的與公司利益的沖突尚無規制。其四,對信義義務的規定缺乏在司法上可執行的檢測標準。
雖然《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了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對其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股東負有誠信義務。但該規范是否包括注意義務,在法律解釋上亦存在疑問。其二,信息披露的義務主體僅限于上市公司,未將居于數量多數的非上市公司囊括在內,主體有限決定法律適用范圍有限。此外,雖然列舉了董事會不得采取的反收購措施,但收購市場的復雜性決定了其不可能窮盡董事層出不窮的反收購措施。盡管規定了一系列董事會不得采取的措施,仍有難以列舉全面疑慮,而應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以適應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實際。
三、反收購董事信義義務的法律規制完善
我國反收購法律制度處于初創階段,可從以下路徑著力:
(一)確立董事信義義務內容及法律責任
對公司收購與反收購中董事信義義務的具體規制有四個方面:1.決策謹慎義務,旨在保證董事會決策的合理性與妥當性,以及限制董事會反收購的提起權及董事會未經股東會批準單獨采取某些措施。2.防御適當義務,不得超出明顯不合法界限,以及侵害公司、股東、債權人之利益;3.全面信息披露義務,目標公司董事會應及時發表意見和決策,獨立董事獨立發表意見;4.股東利益保護義務,包括為股東判斷、決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為股東爭取最有利的收購條件,盡到最大限度的股東利益保護。
(二)完善少數股東的訴權救濟
公司法對于質詢權的規定簡略,質詢權的行使與救濟等有待于立法進一步明確。譬如遭到被質詢人(董事)的無理拒絕,應當賦予提起給付之訴的權利,即要求法院判決被質詢人履行說明、解釋之義務;以及被質詢人在股東會會議上不履行義務或者故意告知不充分、虛假信息的,依據此信息表決的股東,也應當在事后得以會議程序下次為由主張提起決議撤銷之訴,此點有待于納入股東訴訟的類型之內。
(三)反收購決策權的權利主體予以明確
這一點已為新《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采納。反收購決策權主體應為股東會,股東(大)會未做出準予收購決策之前,董事會不得決定或采取任何反收購行動。但是,基于股東至上原則考慮,董事會享有向股東大會提議與建議的權力,對重大的反收購舉措應由股東會決定,對于技術性的反收購措施或急迫性的反收購措施可以由董事會決定,但事后應當取得股東會的追認。
(四)法律體系的內外部統一
宏觀的法律體系內,公司法制與其他部門法的聯系和銜接也存在問題。舉例而言,《反壟斷法》雖已頒行,但在與公司法律制度中的反收購制度的銜接上尚有問題,以反壟斷視角對反收購的合法性審查尚缺乏制度支撐。“立法應當鼓勵和引導并購活動向創造價值的方向發展,在發展中立足于制定公平的并購游戲規則。”
[1]陸文山、項劍.論目標公司應對措施有效性的界限[J].王保樹.公司收購:法律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85.
[2]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3][劉俊海.公司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41.
[4]范建、蔣大興.公司法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388. [5]施天濤.公司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94.
[6]王建.董事義務構造的兩大發展趨勢及我國公司立法的不足[J].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04).
[7]施天濤.公司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94.
[8]曲冬梅.目標公司反收購的法律規制[J].法學論壇,2004,(02).
[9]李建偉.公司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55.
[10]劉俊海.公司收購與中小股東的保護[J].王保樹.公司收購與法律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6.
[11]公司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信義義務研究[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02).
湯欣.公司治理與公司收購[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56.
徐華,男,江蘇溧陽人,東南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D923
A
1008-4428(2017)03-1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