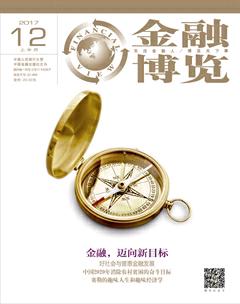第三方支付管理辦法法律位階亟待提升
趙鷂
第三方支付行業(yè)從發(fā)展之初即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其有限的發(fā)展歷程中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tài)勢,目前已成為支付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推動了支付行業(yè)的創(chuàng)新。而伴隨著該行業(yè)新利益主體的不斷加入,相關利益格局也在逐步發(fā)生著變化,在此過程中,諸如法律風險、金融安全風險、信息風險等多方面問題也隨之相伴而生。中國人民銀行在歷經(jīng)多次行業(yè)監(jiān)管制度的探索后,于2010年出臺了《非金融機構(gòu)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與《非金融機構(gòu)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簡稱《實施細則》),由此正式確立了央行作為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監(jiān)管主體的地位。伴隨以《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為核心的規(guī)范性文件的監(jiān)管調(diào)整,第三方支付行業(yè)日漸成熟,其市場行為逐步走向規(guī)范。
但基于中國現(xiàn)行立法體制,央行依據(jù)《管理辦法》向第三方支付企業(yè)頒發(fā)牌照的行政審批行為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來自專家學者的質(zhì)疑。他們認為在法理上,央行并不完全符合法定授權(quán)的主體要求。根據(jù)我國《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guī)定,除國務院以行政法規(guī),省、直轄市政府有權(quán)設定一年臨時許可權(quán)限外,包括國務院直屬部門在內(nèi)的其他地方政府并無設定行政許可的法定權(quán)限。且《行政許可法》第十七條也明確規(guī)定:除本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guī)定的外,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許可。因此,央行作為國務院直屬部門頒布的《管理辦法》屬于部門規(guī)章,嚴格意義上無權(quán)設立關于第三方支付行業(yè)準入的行政許可制度。
央行關于第三方支付業(yè)務行政許可權(quán)限的尷尬境地亟須解決。雖然市場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會促使監(jiān)管當局對處于過渡階段下的新興產(chǎn)業(yè)實施相對適度的監(jiān)管原則,政府也會對有關監(jiān)管規(guī)定的效力層級保持相對寬容的界定立場,以鼓勵新興產(chǎn)業(yè)在創(chuàng)建之初獲得迅速成長。但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的增長速度與市場規(guī)模,理論上已經(jīng)超越相關機構(gòu)實施適度監(jiān)管的界限。如果繼續(xù)維持《管理辦法》的現(xiàn)有法律位階,將不利于維護央行作為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監(jiān)管主體的權(quán)威性,從法律角度而言,更會引發(fā)行政訴訟等法律風險。因此,結(jié)合現(xiàn)實的行業(yè)發(fā)展狀況與監(jiān)管需求,借鑒成熟市場經(jīng)濟國家的支付監(jiān)管體系建設的有益經(jīng)驗,我國立法部門應當將《管理辦法》的法律位階由部門規(guī)章上升至行政法規(guī),且應盡快推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確定央行監(jiān)管主體的地位。
相關立法建議
由部門規(guī)章上升至行政法規(guī)。作為部門規(guī)章的《管理辦法》在法律意義上的現(xiàn)實履行或是可能引發(fā)的法律后果,均存在障礙與風險,且針對規(guī)模與影響力日益發(fā)展的第三方支付行業(yè),實踐已經(jīng)表明,單純依靠中國人民銀行的監(jiān)管仍不足以管控行業(yè)風險與保證資金、信息安全。將《管理辦法》由部門規(guī)章上升至行政法規(guī),由國務院授權(quán)中國人民銀行監(jiān)管,并要求相關部門予以配合,在立法中對相關主體賦予與之相稱的權(quán)利義務,不僅是符合法理與現(xiàn)行法律體系要求的需要,更是行業(yè)現(xiàn)狀與保證行業(yè)未來健康有序穩(wěn)定發(fā)展的需要。
推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中國現(xiàn)行立法流程決定了提高《管理辦法》立法位階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完成,在這段時期內(nèi),通過現(xiàn)實判例推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是提高央行監(jiān)管權(quán)威性的最有效方法。雖然我國不屬于英美法系,但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現(xiàn)實判例出臺的司法解釋在實踐中仍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可確定央行作為行政許可主體的地位,初步解決其與《行政許可法》所要求立法位階不符的尷尬局面。
對第三方支付行業(yè)資格準入
實施行政許可的現(xiàn)實理由
第三方支付行業(yè)在高速發(fā)展的同時,暴露出背后隱藏的風險,如不通過提高《管理辦法》立法位階等方式加強監(jiān)管并肯定央行監(jiān)管主體的地位,可能導致監(jiān)管缺位情況的出現(xiàn),進而引發(fā)不可控的市場失序。
金融穩(wěn)定風險。第三方支付機構(gòu)與銀行業(yè)等金融機構(gòu)之間互為補充、互相推動,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系統(tǒng)網(wǎng)絡,風險一旦發(fā)生,所波及的市場范圍與受眾主體均十分廣泛,可能引發(fā)支付服務市場秩序混亂,影響金融穩(wěn)定與安全。
資金風險。支付機構(gòu)在業(yè)務中形成大量備付金,這一特點決定了資金安全引發(fā)的風險應當?shù)玫教貏e重視。在監(jiān)管缺位時期,持有巨額資金流的第三方支付企業(yè)中,出現(xiàn)擅自挪用備付金直接進行風險較高的實業(yè)投資與證券投資等情況,甚至某些第三方支付企業(yè)借助支付平臺從事洗錢等犯罪行為,嚴重危害客戶資金安全與市場經(jīng)濟秩序。
信息泄露風險。由于行業(yè)本身的獨特性,支付機構(gòu)在業(yè)務開展過程中會接觸到大量客戶信息,如果不對企業(yè)本身實施行業(yè)準入的行政許可制度,強迫其配置安全有效的客戶信息認證與保全系統(tǒng),可能導致客戶信息泄露的嚴重后果。而在不受強制監(jiān)管的情況下,有些企業(yè)甚至會出現(xiàn)利用出售客戶信息以獲得非法收入的情況,導致消費者權(quán)益受到嚴重損害。
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的西方監(jiān)管體例
成熟的市場經(jīng)濟國家,如美國、歐盟等,其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發(fā)展十分成熟,我們可借鑒其在發(fā)展過程中的有益經(jīng)驗,結(jié)合我國實際需求,有效構(gòu)建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監(jiān)管體系。
美國監(jiān)管體例。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關于電子商務領域監(jiān)管體系的國家,其對相關支付行業(yè)的監(jiān)管經(jīng)驗也最為豐富。而通觀美國電子商務與支付行業(yè)的立法史,會發(fā)現(xiàn)即便是在最尊重市場經(jīng)濟資源配置規(guī)律的美國,有關政府也毫不猶豫地選擇將其納入國家級別的立法監(jiān)管序列。
1997年美國政府就在國家層面率先頒布了《全球電子商務綱要》,這是全球第一個官方正式發(fā)表的關于電子商務立場的文件。到1999年美國統(tǒng)一州法全國委員會(Nation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State Laws)通過了《統(tǒng)一電子交易法》(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這個法案確定了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排除了電子商務的障礙,使電子商務的發(fā)展得到了保障。其后,美國眾議院法律制定委員會(The House of Judiciary Committee)在同年10月通過了《全球及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草案)》,成為各州在州際(國際)電子商務場合使用電子簽名的法律基礎。
雖然在美國的立法體例中,并未專門制定針對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的法律,而且在國家與州的之間,對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的監(jiān)管還存在一套雙軌制系統(tǒng),但是,即便如此,在最高立法級別的規(guī)范性文件中,卻始終存在著各類涉及第三方支付業(yè)務的核心條款。
歐盟監(jiān)管體例。歐盟也是最早建構(gòu)關于電子商務與支付行業(yè)監(jiān)管體例的組織之一,其在1997年就頒布了一部法規(guī)《歐洲電子商務行動議程》,專門指導電子商務活動。其后,1998年11月發(fā)布了《發(fā)展電子商務法律框架之指令》(Leg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erce),希望清除歐盟范圍內(nèi)對電子商務造成阻礙的法律,指導會員國修改法律,促進電子商務的發(fā)展。而為了保障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歐盟的電信部長理事會又于同年公布了《電子簽名指令》,促使建立一個完整的電子簽名法律認證體系,和有利于電子簽名推廣的環(huán)境。2000年,歐洲議會通過了《歐盟電子商務指令》,該指令對歐盟所有成員國都有約束力,致力于對電子商務作出綜合性的規(guī)范。
從第三方支付行業(yè)的監(jiān)管體例上進行比較,歐盟與美國存在明顯的不同,歐盟的監(jiān)管體例有直接關于第三方支付企業(yè)準入方面的規(guī)定,具體到有關法律規(guī)定,即指歐盟的第三方支付企業(yè)要想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必須要取得銀行業(yè)的營業(yè)執(zhí)照或者電子貨幣企業(yè)的營業(yè)執(zhí)照才能進行。而上述有關法律直接授權(quán)歐洲中央銀行作為監(jiān)管主體,同我國的監(jiān)管機構(gòu)相一致。
綜上所述,通過結(jié)合現(xiàn)實中的風險考量,并考察西方發(fā)達國家相關立法的經(jīng)驗,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采用何種監(jiān)管體例,將第三方支付業(yè)務作為重點監(jiān)管對象,并在最高層級的立法文件中將其體現(xiàn)是對行業(yè)最有效管控的方法。作為發(fā)展中國家,我們更應當注重有關立法文本的制定,提升《管理辦法》的立法位階,并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以維護監(jiān)管機關的權(quán)威性,構(gòu)建合法合規(guī)、高效有序的監(jiān)管體系。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