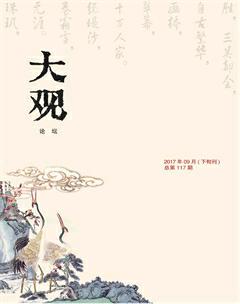淺析電視新聞專題節目的真實感營造
摘要:《看見》,作為一檔電視新聞紀實類的專題欄目,事實、真實是它所圍繞和探求的主題。然而百分之百地還原事實并不可能。而《看見》綜合運用電視節目的各種要素,最終賦予節目本身一種新聞真實感,給觀眾創造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本文結合文本分析新聞真實性原則,解析了這些元素對《看見》營造真實感的作用。
關鍵詞:《看見》;真實;蒙太奇
一、《看見》與真實感構建
《看見》作為一檔記錄現實題材的專題節目,觀察變化中的時代生活,用影像記錄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畫這個飛速轉型的時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與渴望,期待和觀眾一起,了解陌生,認識彼此;端詳相似,審視自我。人性是《看見》的中心,而紀實則是其重要手段。
《看見》通過對當事人的采訪與外在的敘事結合,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情節,使作品與觀眾情感產生共鳴。《看見》這檔電視新聞紀實節目對于新聞真實感的構建,主要通過其完整的表達體系來完成,即:細節展現、情感烘托、直觀感受和戲劇表達。
二、《看見》節目真實性的營造手法
(一)采訪——細節展現
麥克盧漢說,“媒介即訊息”。《看見》采用一對一、面對面的采訪方式,讓當事人與主持人近距離口述事件和感受。這種口述的傳播方式屬于人際傳播的一種,當事人的敘述也自然是承載和傳遞歷史信息的一種有效且令人信服的媒介。其本身就是“訊息”。這樣的采訪環境對《看見》來說極其重要。這樣的方式讓觀眾可以很直觀地觀察到被訪者的生活工作場景,可謂是對真實環境的一種極好展示。
例如在“教練李永波”一期中,可以從電視節目中觀察到采訪地點是在國家羽毛球場;在“告別盧安克”一期中,土坡、學校等也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采訪的地點是在盧安克支教的地方;“專訪劍橋大學校長樂思哲”一期中,解說“吃時間的蟲子”、劍河泛舟更是把觀眾帶進了人物所生活的大環境中去。可以說每一期的一些細小的元素,在主持人的帶領下,觀眾總是可以很容易的進入到與人物相關的最真實的環境,同時勾起許多個人化的細節記憶,就像在給大家提供一個事實“雛形”,把事件和歷史的原貌展示給大家,盡管這“雛形”剛開始看上去簡單,不全面,有瑕疵,但只要有了這個“雛形”,后人就能在上面精雕細刻,去總結分析,提煉出屬于事件和人物的歷史記憶,一步一步地更接近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的本來面目。
(二)音響——情感烘托
電視符號是一個復雜的符號,它自身是由兩種類型的話語——視覺話語和聽覺話語——結合而構成。電視作為聲畫的藝術,聲音的應用也至關重要。要把真實的生活搬到電視節目中去,音響必不可少。音響在創造環境氣氛,刻畫人物內心情感和藝術空間時有著獨特的功能,能增強電視節目的真實感和感染力。
電視音響主要有同期聲、音樂、旁白解說等,在《看見》中也是各有運用。在專訪“劍橋大學校長樂思哲”一期中,柴靜身處三一學院的植物園介紹達爾文時可以很明顯聽到植物園內的鳥叫聲,在劍河泛舟碰到霍金的時候人群的嘈雜聲,這些同期聲的處理都極好的還原了當時的場景和情景。在同一期節目中,也是在柴靜遇到霍金的時候,節目中又加入了歡快愉悅的音樂,更是將柴靜心中當時的興奮喜悅完美地展現給觀眾。另外,每一期節目中都會有柴靜對視頻材料的旁白解說,通過聲音、語調、情感的把握,也將觀眾帶入人物的情景,極好地營造出真實的環境與感情。
(三)鏡頭——直觀感受
《看見》中擅用紀錄片風格的長鏡頭和一些特寫鏡頭來增強生活真實感。長鏡頭表現過程,特寫鏡頭恰好刻畫細節。《看見》中多用客觀鏡頭,是攝影師站在自己的角度對被訪人物的表情、動作等的把握。
在“告別盧安克”一期中,多次對盧安克面部的特寫,蒼白惆悵,細致地展現了盧安克在遵從妻子選擇離開支教事業的那種迷茫和糾結。“孝子弒母”一期中對鄧明建臉部的特寫,把人物內心深處選擇弒母的那種無奈、無助生動地刻畫出來。“雨后”對張圣才面部特寫,表現出他執著之外的善良。節目通過這些細節的處理,運用特寫鏡頭,讓觀眾也仿佛到了情景之中,與人物面對面交流,能看清人物的一舉一動,一個動作、表情都逃不過觀眾的眼睛……這些鏡頭的運用給了觀眾極好的現場感受。
《看見》中鏡頭與鏡頭之間組接所展示的視覺空間的依據通常是表現主題思想的需要和不同視角的重現。在進行鏡頭與鏡頭組接時,一般會先交待新聞事實發生的大環境,再逐步展現新聞事實中受眾看到的東西,這樣就使得每一個鏡頭所展示的視覺空間都與大環境總有重合,從而保證每一期節目中視覺空間的統一和連貫,使新聞看起來是現實生活的再現,是真實的。
(四)蒙太奇——戲劇表達
蒙太奇作為電視電影的一種藝術手法,創作者按照拍攝的許多鏡頭和講述事件的創作構思,把這些不同人物的鏡頭有機地、藝術地組織、剪輯在一起,形成屬于畫面剪輯特有的邏輯思維。
在采訪李安的一期中,當提到李安關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這部電影時,講到電影中派與老虎間的斗爭故事,而在這個時候柴靜開始旁白“但是,真實的世界真的是這樣嗎?”。在談及真實的時候,畫面就立即切到了2010年柴靜在《面對面》采訪翟墨的一段視頻。翟墨,中國單人無動力帆船環球航海第一人。在視頻中,翟墨也講述了一個人在海上和一條鯊魚的遭遇,而剛好采訪中柴靜也對翟墨提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翟墨與鯊魚、派與老虎,這兩個一個真實、一個影視藝術,通過這種畫面的巧妙銜接,將電影與現實結合起來,把電影的故事進一步體現出來,讓觀眾在這兩種視覺符號的交織領域,解讀出新的符號意義,即深入了李安內心對影片故事選擇的拼搏和掙扎,從而也加深了對影片故事、導演生活經歷的理解。
諸如此類通過蒙太奇的使用手法,通過策劃人編導等有意識地主觀創造,把一系列表現真實的素材拼接剪輯在一起,不僅讓作為采訪對象的人物豐滿起來,而且給觀眾對人物、對故事等等的判斷也提供了極好的素材,給了觀眾真實的感受。
三、結語
在傳統媒體受到新媒體強烈挑戰沖擊的今日,在電視媒體娛樂化、商業化泛濫的大環境下,《看見》仍能夠獲得觀眾和業界學界一致好評,源自不忘“以影像記錄飛速轉型的時代”這一初心,并且合理地運用富有人情味且觀眾所接受的采訪報道方式、拍攝方式及剪輯敘事技巧,切實地用電視新聞實踐詮釋著自身對于新聞與真實的理解,對一樁樁新聞事件、新聞人物發出了自己獨特而真實的聲音。這對于其他諸多電視乃至傳統媒體的新聞節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冷冶夫.從真實到真實感的流變——21世紀對“真實”的再認識[J].當代電視,2009(04).
[2]嚴進生.營造意境與真實——音響在電視節目中的運用[J].聲屏世界,2008(04).
作者簡介:許君覺(1991-),男,漢族,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