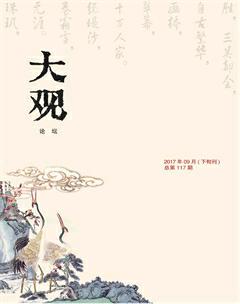哲學視域下的原始社會生殖崇拜問題探要
侯則名+霍妍
摘要:原始社會時期的生殖崇拜現象是人類原始先民對自我與自然的一種初級認知和改造,其不僅反映了人類早期對萬物化生這一現象的內在規律及人類自身再生產這一問題的探究,更是后人關于“性”所產生種種思考和舉措的思想發端所在。其中如何認識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現象?如何審視這一觸及人類自身最本質的問題?又應當如何從中汲取對當今性文化有科學理性導向的正能量營養?這些問題千百年來飽受爭議卻又懸而未決,故而以全新的哲學視角來透析原始社會生殖崇拜現象,從而為解決上述的問題提供新的思維方式與方法途徑,便是本文的旨要所在。
關鍵詞:生殖崇拜;天人合一;馬克思主義哲學
在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之際,原始社會中的部族們依據當時的生存環境與認知水平衍生了諸多信仰形式。時過境遷,原始社會中的大多崇拜形式已成為文化歷史中的化石,但唯有生殖崇拜,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中依舊生命鮮活,甚至至今仍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現代人的生活思維。然而當談及先祖生殖崇拜這一文化現象,我們大多抱有諱莫如深或欲說還羞的態度。這無疑不利于我們對這一古老的文化現象的正確理解,更無法有效發掘其中的文化價值與時代意義。對此通過哲學的視角去審視人類文明中這一古老的文化現象,是具有思想高度與科學價值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生殖崇拜現象與“天人合一”觀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根本觀念之一,其意指人與自然之天、道德之天、義理之天的和諧統一。其濫觴于莊子,發展于董仲舒,并為后世所不斷豐富深化,從而構建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率先闡述了天地萬物間相生相承的關系;而后的漢儒董仲舒,更在此之上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將天上升為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認為天人相通相感。縱然董仲舒這一唯心色彩濃厚的“天人感應”說未能為后世所推崇,但其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卻在原始社會的生殖崇拜現象中得到了佐證。據史料記載,原始先民將生殖現象與農業生產、畜牧發展情況相關聯;認為對其祭祀可感天動地,可祈得豐厚的大地回饋和上天僻佑。
不僅如此,先民把生殖和土地聯系在一起的原始思維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后世以思辨的態度將這種關系擴展為天地、陰陽關系。“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諳識陰陽和合之道,體查化生增長之理,這便是生殖崇拜現象中所折射出的深刻而成熟的“天人合一”思想。時至今日,當我們考察地方的民風民俗,尤其是少數民族中所流傳的文化遺產,以生殖崇拜所折射“天人合一”思想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自然世界是人類賴以為生的家園,也是人們所實踐改造的對象;人類的繁衍生息,離不開自然的福澤給予;因此,原始社會中人們所進行的生殖崇拜現象,正是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思考的證明,也是后世深入研究“天人合一”問題的思想淵源。
二、生殖崇拜現象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實踐認識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先前其它哲學流派所表現出的最顯著的特點。其將前人形而上學的主觀認識論復歸到人類的生產實踐上來,以解釋古往今來的人類認知變化與社會演進。
母系社會時期,女性以采集為主要形式的社會生產方式與在生殖方面的主導權,造就了母系社會中女性崇高的社會地位。由于采集這一生產方式所帶來的收益穩定之優勢和人們對生殖原理的有限認識,使男性的生產與生育都附庸于女性。
而后,隨著人類社會發展中男性以農耕和畜牧為主的生產方式的生產力的顯著提升與男性對自身在生殖過程的作用的重新定位,致使女性的社會地位受到沖擊。原始部落中的群婚習俗漸變為“一夫一妻”的婚配形式,并為維護男性對女性的人身所有權而形成了日益繁復的律法約束和道德規范。而究其這一現象產生和演變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實踐對認識具有決定與推動作用”這一原理的蹤影。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動力和目的;更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哲學較之以往哲學的根本區別之一就在于馬克思充分肯定并重視了實踐在人類生產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人類日益發展的技術進步,尤其是科技進步成為了社會轉型的關鍵因素。從而伴隨著生產實踐,人們對自然世界以及人類社會的認識也得以不斷地深化和進步。因此放眼原始社會時期,縱然男女生殖地位的轉換只是母系社會衰落的原因之一,但其間所彰顯的實踐與認識的辯證原理無疑為我們分析歷史與展望未來提供了科學的哲學思維與依據。
三、生殖崇拜現象與否定之否定辯證思想
列寧說過:“人的認識不是直線(也就是說,不是沿著直線進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線。”人們的認知與過程總要經過否定之否定的歷史環節,會總體呈現出在曲折中前進發展,故而生殖崇拜現象自然也無法規避這一規律的作用與影響。因為說到底,生殖崇拜是人類對自身生產實踐的認知表現。曾幾何時,被視為神圣而純潔的生殖崇拜演變為世人眼中難以啟齒的話題,這與后世反復發生的性禁錮與性解放運動息息相關。從古羅馬時代的縱欲之風到中世紀的禁欲浪潮,再從天主教禁制下的性禁錮到文藝復興的性解放。反反復復,不斷在否定的道路上曲折前行。歷史總會抹去時代的煙云,留給我們最真實的啟示:性,只是生殖崇拜現象中的一個方面,而人類對性的態度則折射出了人類對自己的態度。
正視先民生殖崇拜現象對當今性文化的科學導向,反對歷史中對性的不公允態度與偏激的處理方式;馬克思如是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們呼喚人性的復歸但反對縱欲主義,我們倡導價值理性但拒絕禁欲之風,以思辨的態度與科學的方法處理當今社會關于性所存在的諸多問題。這就是我們研究生殖崇拜這一文化現象所得到的啟示以及該文化對當今社會所具有的科學導向價值之所在。
【參考文獻】
[1]列寧.列寧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15.
作者簡介:侯則名(1991-),男,漢族,黑龍江省大慶市人,南開大學哲學院2017級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研究。
霍妍(1991-),女,漢族,黑龍江省齊齊哈爾人,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6級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