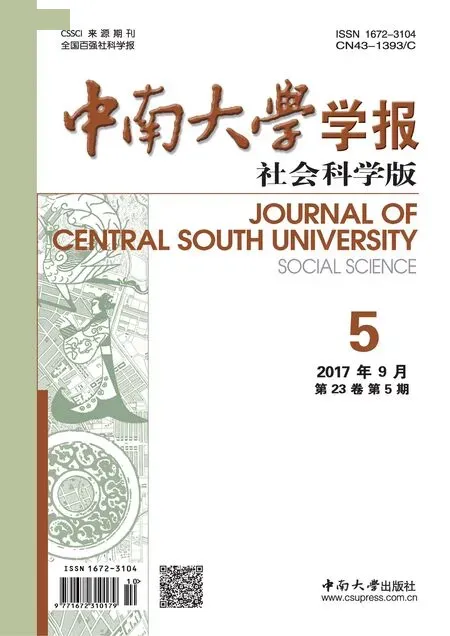論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及其治理
李志鍇
?
論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及其治理
李志鍇
(重慶大學法學院,重慶,400044)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系行政規制形成的“非市場工資”,長期遁入公共政策空間并成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工具,有違最低工資標準制度的初衷。如何在保留地方政府自由裁量空間的同時,保證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員行為的合理性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最低工資標準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合理性判斷,應當跳出狹義的勞動者保護視角,依據比例原則將審查重點轉移至保障經濟共同體整體性、流動性和公平性的視角,對勞動者利益進行整體理解,重點在于“協調”而非狹義的“保護”。
最低工資標準;地方政府間競爭;比例原則
一、問題的提出:“向下競爭”的最低工資標準
2016年初,財政部長樓繼偉提出薪酬增長過快,導致企業搬遷至國外,既減低了我國企業競爭力,也最終損害了勞動者就業機會[1]。同年8月,國務院頒布《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鑒于嚴峻的經濟形式,各省市的最低工資方案提升放緩,廣東等省市則提出凍結最低工資標準兩年。對最低工資標準的抑制并非僅是當前應急之策,實際上過去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實際值與法定的理論值之間一直存在較大差距。
依據《最低工資規定》中規定的比重法計算,通過國家統計局網站和各省統計年鑒收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簡稱“各省市”)的最低收入組人均每月生活費用支出和贍養系數,共收集20個省的有效數據。數據樣本涉及我國大部分地區。其中,“月消費支出”是該省市最低收入組人均每月生活費支出;“贍養系數”是各省市總人口數與總就業數之比,系就業人口的家庭負擔情況;“理論標準”是按照比重法計算的標準,實際標準為該省市一類地區2014年工資標準;“實際標準”是各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若該省市最低工資標準分不同類則取最高標準。如表1所示,我國各省市的實際最低工資標準普遍低于法定理論標準,多為法定理論標準的55%~75%。
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現狀,有觀點認為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2.8%,其增長速度快于CPI,其調整適當[2]。有的則認為“我國最低工資標準一直偏低,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僅能保障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生存”[3]。張五常教授等甚至主張最低工資標準違反經濟規律應當予以取消。對最低工資標準的研究多采用結果導向性的研究方式,此類目的?手段的研究方式作為邏輯起點的“目的”應當是確定的。然而,在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制定中,“目的”包含保護勞動者、均衡勞動市場、穩定就業等多個需要均衡的目標。基于不同目標可采取的調控手段可能是相反的:以提高勞動者生活、促進利益共享的理由,可以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促進就業、提高地區或企業競爭力的理由,可以壓縮最低工資標準。如果說最低工資標準對就業的影響是有爭議的,那么其對地方招商引資的影響便是實在的。換言之,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會確實執行中央的社會政策,因為這些社會政策的執行會影響到地方政府自身的資本積累,中國社會福利體制的特點是地方可能比中央具有更關鍵性的影響[4]。在地方政府與納稅企業政商利益共生的格局下會有向下的力抑制最低工資標準,存在“向下競爭”的沖動,這是最低工資標準實際值長期低于法定理論值的重要原因。
無論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趨勢是“向上”還是“向下”,都不改變其競爭的本質,競爭本身是中性的,對競爭的判斷需要結合競爭的過程與結果進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有序競爭,可以避免權力的恣意性,促使地方政府均衡各方利益。公平、健康、透明的競爭既可避免地方政府因民粹主義而盲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又可避免地方政府為短期經濟利益而壓低最低工資標準。一般認為,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但是政府俘虜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等均證實政府并非當然是大公無私的,政府及政府官員有其依據自身利益進行判斷的行為邏輯方式。事實上,政府間不當競爭會導致政府失靈并產生破壞性后果。在單一制國家中,由于地方個體的同質性極大,對資源的需求也極為相同,競爭較之聯邦制只會更加激 烈[5]。缺乏法律約束的地方間政府競爭與最低工資標準,極易脫離原有行政規制目的轉變為變相尋租,破壞勞動關系的穩定性,損害低收入勞動者的利益,對社會資源總量和公共利益毫無益處可言。

表1 全國20省市2014年最低工資標準表
二、以地方政府為中心的最低 工資標準擬定及行為邏輯
(一) 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形成
1994年的《勞動法》第48條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由各省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原勞動與社會保障部2003年頒布的《最低工資規定》第8條規定,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各省市勞動行政保障部門會同同級工會、企業家協會等研究擬定后,報勞動保障部。《最低工資規定》實施至今,各省市擬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都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未出現申請未予批準的情況。同時,各省市勞動行政保障部門作為各省市政府的下屬部門,其擬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都需報各省市政府決定,因此地方各省市政府獲得了最低工資標準的決定權。
不同國家政府對于最低工資標準有不同的價值取向,荷蘭等國傾向于將工資作為一個社會保護儀表,而愛沙尼亞則將其作為三方談判中的一個重要工具,英國政府則傾向于將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促進公平和效率的一種手段[6]。我國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一種保障制度,源于《憲法》第42條“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是憲法規定的國家義務。各省市政府負責擬定標準是因為地方政府在信息收集、利益權衡和綜合評判上較中央更有優勢,也符合行政區域管理負責制的要求。遺憾的是,雖然法律規定了勞資雙方有權參與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但是我國勞資談判機制孱弱、工會行政色彩濃厚與地方政府的強勢使地方政府的行政決定權缺乏相應制衡。
(二) 地方政府間的利益博弈與地方官員的行為邏輯
上下級行政機關間屬于隸屬關系,下級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應當服從上級的命令和決定,中央擁有對官員評定和升降決定的大權,這種權力資源是下級爭奪的極其稀缺的資源。依此推論,地方官員必定會全力執行中央的命令,以取得上級的青睞。然而時間和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命令時必定有所側重,地方政府會選擇那些中央更看重也符合地方政府利益的命令執行。事實上,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并非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提出“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實際上,多數省市都無法達到這一要求。例如,2014年北京職工月平均工資為6 463元,按40%計算已達2 585元,然而至2016年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僅為1 720元。可見,地方政府在調控最低工資標準上并未完全達到國務院的要求和法律擬定的理論值。
依據傳統的政治學觀點,行政規制作為國家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是“捆綁式消費”,相應的組織和個人只能遵從,但事實是很多的法律制度是可以被選擇適用的[7]。《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大量的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遷到內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區便是一種行為選擇。我國實行國稅、地稅分稅制財政體制,地方企業的稅收是地方財政重要的來源,并且影響到招商引資的考評和當地就業率。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考慮,其自身缺乏推動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動力。更重要的是經濟分權的背后是政治上的集權,地方政府對上級政府負責,上級對地方政府的評價、獎懲主要憑借以GDP等經濟數據為核心的績效考評系統。在晉升機會有限的背景下,地方官員必須完成提升GDP等經濟政績,才有可能在向上的“零和博弈”中勝出,獲得自己的前程[8]。雖然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的收入增倍計劃等要求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但是從理性的角度,政府官員顯然更加關心地方的稅收、就業等指標,因為這些指標直觀并容易獲得上級認可,更能為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帶來實際的好處。此外,由于各省市政府間存在競爭關系,只要有一個省市不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就有可能影響周邊省市。在競爭實力相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帶來降低競爭力的風險。我國競爭實力相近的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看似不謀而合,并非各省市對保護勞動者利益有相同的理解,而是各省市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參考彼此標準。
(三) 地方政府的兩難處境及其選擇
我國地域廣闊,北上廣等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無異,而西部地區仍較為落后,無法適用統一的保障標準,故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各省市擬定。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失業金等眾多財政性支出直接掛鉤,在財政分權制下這些財政性支出又多由地方財政承擔,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實際是要求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財政負擔。換言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便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在面對地方政府間競爭、經濟轉型和日漸加重的財政壓力下,一味苛責地方政府對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利可能違反了“無人有義務做不可能之事”的正義原則。
我們應當注意到最低工資標準是一種易升難降的剛性標準。印尼2003年勞動法未明確何為“合理生活標準”,導致地方政府為政治因素而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甚至超過了勞資雙方決定的幅度,造成了激烈的勞資對抗甚至演變為大規模示威及罷工事件,導致社會動蕩不安[9]。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設計的目標除《最低工資規定》所確定的保障勞動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目標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等文件還提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動內需等目標。其中,保障勞動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目標是最基礎也最易完成的,其他目標的實現則有賴于地方財政狀況與經濟整體形勢。從風險偏好的角度,地方政府的選擇多趨于保守,優先選擇完成最基本也最容易完成的目標以回復上級行政機關的命令,選擇需要根據經濟狀況和地方財政現狀決定的其他目標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偏好。此外,最低工資標準過高有可能使地方政府喪失在經濟下行時調控的空間,這亦是地方政府考慮的重要風險。判斷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的正當性,不應單純從最低工資標準數值高低進行判斷,控制最低工資標準背后政府行為的合理性,才是保證最低工資標準調控目標得以實現的基礎。
三、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之法律審視
(一) 行政規制下的“非市場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是政府對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正常勞動后可獲得的最少工資的強制性規定,屬于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是規定勞動關系基本事項之最低基準的法律,要求勞動關系涉及的責任主體不得低于此基準,是“政府對勞動條件干預、介入之法,故為行政法,對勞動基準法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應當按照行政法途徑進行救濟”[10]。
行政規制是“特定的行政主體所采取的,直接影響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的,設立規則、制定政策、實施干預措施等行政活動的總稱”[11]。行政規制是政府運用公權力直接干涉市場交易,基于私人選擇無法糾正市場失靈,而不得不選擇的行政手段。最低工資標準行政規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市場失靈,規制主體是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行為的對象是勞動關系中勞資雙方訂立工資的最低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制度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行政管理活動,應當將其歸為行政規制。以公共管理的視角,最低工資可謂優良的政策工具。最低工資作為政策工具的優勢在于不需要政府支付很多的行政成本,便可對社會經濟產生直接的干預效果,還可以體現政府對弱勢群體或勞動者的關愛,樹立政府愛民的良好印象,提升政府的威望和穩定執政基礎。在公共政策的視野中,政府管理公共事務有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就是如何恰當地挑選和運用政策工具的過程,最低工資就是一種政策工具與“非市場決定”的工資[12]。
(二) 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之考量
“現代行政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將國家權力的行使保持在適度、必要的限度之內,特別是在法律不得不給執法者留有相當自由空間之時。”[13]如何既保證行政的效率又保證其不肆意妄為,如何在立法機關授權立法不斷增多的情況下避免政府失靈,實現對私權的有效保護,是現代行政法無法回避的問題。目前對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學研究較多,公法角度多以憲法為視角。我國憲法中保障人權、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條款是最低工資標準的憲法基礎,憲法基礎的確立固然重要,但是鑒于憲法的抽象性和我國憲法實施基礎的孱弱,憲法研究并不能解決對最低工資調控的合理性判斷,更無法約束其背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
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經驗便是通過刺激地方政府與政府領導間相互競爭產生源源不斷的動力。這樣的競爭關系同時也使地方政府重視局部利益,從而引發地方政府間的不當競爭。最低工資標準調控作為行政行為,對其約束應當回歸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最低工資標準調控與地方政府間競爭實則都系行政適當性問題。
對于判斷行政行為適當性,英、美等國采用合理性原則,德國則通過比例原則進行判斷。目前,比例原則不斷從德國向歐洲乃至世界眾多國家推廣,合理性原則在英語國家不斷退縮,呈現比例原則替代合理性原則的趨勢[14]。比例原則不斷擴張的原因是其更適合新時代保障人權的司法需求,其三子項的審查方式具有良好的工具性和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力。最低工資標準的目的是保障勞動者利益,勞動者的利益是在勞動力市場中實現的,自由流動、就業自由和社會福利公平是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核心利益。只要勞動力市場是整體并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者便可以“用腳投票”選擇從工資較低的地方遷移到工資較高的地方。因此,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審查重點在于地方政府的調整行為及其他勞動力市場行政規制行為是否有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性和流動性。只要勞動力自由流動、就業自由和社會福利公平得到保障,那么具體標準的高低應屬于行政合理裁量范圍之內。
(三) 合比例的最低工資標準競爭
歐盟法院在審理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15]時巧妙地避開了人權保障問題和對成員國內政審查可能引發的爭議,采取從保障經濟共同體整體性、流動性和公平性的視角審查最低工資標準等行政規制行為,并提出合比例調控的判斷方法和判斷要件。歐盟有26個成員國,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各異,人員自由流動、服務貿易自由流動是歐盟的基本原則,是將歐盟凝結在一起的不可妥協的準則。鑒于歐盟現狀,比例原則被廣泛應用于處理不同國家間勞動政策的沖突。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是一起審查和判斷歐盟不同成員國間以最低工資標準為核心的行政規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案件。在AndréMazzoleni vs ISA案中,歐洲法院指出:
首先,最低工資標準中涉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對勞動者的利益,重點在于“協調”而非狹義的“保護”。勞動者的自由流動、就業自由和社會福利公平是構成歐盟共同市場的基礎。共同市場構建的原理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中是一致的,但是強制性勞動標準的制定實際是強行規定了特定民事主體(雇主)對另一特定民事主體(雇員)的法律義務,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認同、政治結構等都對標準的制定和實行產生影響,不同國家勞動政策不可照搬套用。對勞動者的整體保護包括勞動條件、工資福利、稅收負擔等,因此對勞動者利益的保護應當就從整體理解,重點在于“協調”而非狹義的“保護”。勞動者應當指多數勞動者,因為一個國家或者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規、政策規范時,從效率角度首先考慮的是多數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因此對法律法規、政策規范的評判無需求全責備,其目的是維護多數勞動者利益,手段“不過分”即可。
其次,歐洲法院認為東道國的主管當局應當評估所有相關的因素,以確定其規則適用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是必要和相稱的。歐洲法院指出全面的評估是必要的:第一,政府必須考慮到,特別是提供服務的持續時間和行為的可預測性,以及成員國間勞動力流動的現實情況;第二,為了確保在會員國建立的員工保護制度是等價的,他們必須特別考慮到報酬和工作期間涉及的數額的因素,以及社會保障的貢獻和稅收的影響水平;第三,東道國確立對工人的保護應當與實際情況以及其歐盟成員國的義務相稱。
最后,應當采用合比例的評估方法。比例原則的適用作為“目的?手段”的檢測方式,如何對行為進行評定是正確適用該原則的一個重要基礎。比例原則作為一種法律工具,在應用時必然包含相應的價值基礎,如果這些價值基礎和評判標準是可以被任意解釋的,那么比例原則規范公權力的作用定然減損。故,比例原則在具體應用中也應當規范。應用比例原則評判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恰當時,應當注意三性:第一,可預測性。相應的強制性勞動標準應當是可操作、可預測的,“模糊不清”也是“過分”的表現。第二,整體性。比例原則的應用與評定應當從整體出發,在強制性勞動標準領域,應當從勞動者、雇主和社會進行綜合考慮,盡可能保護勞動者,也避免“過分”保護。第三,可比性。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應當脫離現實的標準、無視現實的環境,用單純的理想替代政府決策的理性是有害的。比較表1的最低工資標準便可知,經濟發達程度接近的省份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類似,正所謂重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由四川決定的。反之亦然。
《歐洲社會憲章》第1部分第4條規定“所有工人都有權要求公平的報酬以使自己及其家人保持體面的生活水平”。針對跨國勞務合作的興起而引發的同工不同酬、稅收安定和社會安定等問題,歐洲法院通過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等一系列案件闡述了共同體勞務自由對勞工權利的重要性,以及各國的最低工資規定應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著重整體判斷而不拘泥于具體標準的高低。
四、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優化路徑
(一) 地方政府間競爭之比例治理
調控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傳統經驗是中央通過行政命令、會議協調等方式進行調控,通過中央的權威來約束地方。但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始終存在,另一方面這樣的調控方式也沒有跳出命令型管理的思維定式,并且使得地方政府更樂意于比拼“上層通道”,曾經的地方政府駐京辦和現在的類似地方政府機構便是權力命令型管理模式的副產品。最低工資標準調控作為行政行為,對其約束應當回歸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最低工資標準調控與地方政府間競爭實則都系行政適當性問題。歐盟法院在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中實際是運用了比例原則中的適當性、必要性和均衡性[16]的三分判斷方式。
首先,適當性是指行政機關采取的措施有助于達到其所追尋的目標。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地板工資”應當達到保障勞動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的目標。其次,必要性是指行政規制在追求相同行政目標時,選擇對公民利益損害最小的手段。應當結合社會福利、稅收負擔等整體考慮勞動者與企業的負擔比例,選擇利益的均衡點。不反對最低工資標準等勞動基準作為地方競爭實力的一部分,反對為了形成比較競爭優勢而刻意控制勞動基準產生螺旋向下的競爭。最后,均衡性原則要求利益均衡,要求實現手段獲得的收益不能與受到的損害間不成比例。當前與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掛鉤的財政指標太多,使得地方政府變為了直接的利益相關者而非中立第三方,在此需要我國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改革相配套,減少地方的財政負擔。地板工資保障勞動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是審查監督地方政府調控行為合理性的核心,只要不低于地板工資的地方間最低工資競爭都可以視為合理的。另外,以最低工資標準的方式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標,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應當陷入狹義保護,脫離“協調”一味強調數值的增長會割裂社會經濟的整體性,這并非最適當、必要和均衡的做法。
(二) 合比例的審查機制與地方政府間最低工資標準競爭的治理
不同于法、德等歐洲發達國家,當前我國存在工會不發達、集體談判體系不成熟、罷工缺乏明確法律基礎等問題,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也主要是采用政府主導下的調研?協商?制定的方法,如何對問題進行評估是行政決策的基礎。從英國撒切爾政府開始,“成本?效益”的評估方式成為了英美行政法中較常采用的一種對行政行為合理性的評估方式。《國務院工作規則》第21條規定:“國務院及各部門要完善行政決策程序規則,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決定作為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增強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最低工資規定》亦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研究擬定”的。當前,多數省份在擬定最低工資標準時會對最低工資標準對雇主和勞動者的影響進行評估,采用了較為簡單的“成本?效益”評估方法。然而,勞動者的收入受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社會保障、社會負擔、地區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等的影響,當前采用的簡單的評估方式顯然存在不足。
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勞動者、雇主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對社會影響重大,因此,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程序與依據應當公開。各省在公布最低工資標準時,應當同時公布“成本?效益”的整體評估辦法,建立評估體系和標準權重,使最低工資標準制定中的利益考慮與利益博弈公開。國務院可以對各省的評估文件進行審查,要求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應當具備可預測性,應當整體地對本省市的勞動者狀況進行評估。要使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不過分”,應當整體考慮社會福利、稅收等因素,在保護勞動者的同時選擇對雇主影響最小的手段,避免雇主所失遠大于勞動者所得的違反狹義比例原則的制度設計。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一種行政規制行為,起到的是勞動市場的“安全網”作用,其標準不應當明顯超過工資結構可接受的范圍,政府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目標、過程等亦應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約束。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給勞動力市場溫和的壓力,使得勞資雙方關系向良性的方向轉化,而非以行政規制取代勞資雙方談判。
(三) 落實行政程序參與原則
行政程序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遵循的步驟、方式、空間等要素的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為了保證程序的正當性和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行政權的不法侵害,必須讓個人參與到行政機關行使這些權利的過程中去,越是重要的權利對應的行政權力就應當越嚴密,或者說更貼近訴訟原則[17]。在擬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程序中,勞資雙方應當能夠全程有效參與制定的過程。行政程序參與原則落實不足,便容易陷入輿論引導執法的困局。
勞資雙方的意見應當能夠對最終結果產生影響,政府應當對是否采納勞資雙方建議及其理由和依據給予相應說明,否則行政程序參與權就只是擺設。此外,勞資雙方代表應當適格,具備代表的正當性,并能夠真實代表其所應當代表群體的意志和利益訴求。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實行的是一元工會體系,其組織方式和社會背景的行政色彩較為濃厚,在政府主導的最低工資制定程序中我國工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身份特征的影響。要改善我國工會的現狀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期間更應當保障最低工資標準制定過程的公開和透明,迫使工會以其行為顯示其代表性。同時,普通勞動者也應當有機會了解和參與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的過程,進而督促我國勞資談判體制的改革發展。
[1] 樓繼偉. 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J]. 財經界, 2016, (3): 49.
[2] 白天亮. 最低工資標準10年漲了兩倍多[N]. 人民日報, 2015?3?24(8).
[3] 羅小蘭, 叢樹海. 基于攀比效應的中國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對其他工資水平的影響[J]. 統計研究, 2009, (6): 65.
[4] 鄭志鵬. 差序壓制型勞動體制——中國兩次勞動法在臺資企業治理結果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 臺灣社會學刊, 2014(6): 82.
[5] 劉亞平. 對地方政府間競爭的理念反思[J]. 人文雜志, 2006(2): 81.
[6] Lothar Funk, Hagen Lesch. Minimum wage regulations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J]. Intereconomics, 2006, (10): 89.
[7] 劉雙舟. 法律市場視野中的制度競爭與立法行為選擇[J]. 政法論壇, 2010, (3): 91.
[8] 靳文輝. 論地方政府間的稅收不當競爭及其治理[J]. 法律科學, 2015, (1): 141.
[9] 方俊德. 調高最低工資對于勞動市場之影響——以印尼為例[J].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4, (9): 104.
[10] 黃越欽. 勞動法新論[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11] 江必新. 論行政規制基本原理問題[J]. 法學, 2012, (12): 29.
[12] 鄭益奮. 政策工具視野中的澳門最低工資[J]. 九鼎, 2014, (12): 12?13.
[13] 余凌云. 論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J]. 法學家, 2002, (2): 33.
[14] 楊登峰. 從合理性原則走向統一的比例原則[J]. 中國法學, 2016, (3): 91?93.
[15] NZA 2001, In Case C-165/98[EB/OL]. http://curia.europa.eu/ juris/liste.jsf?language=en&jur=C,T,F&num=C-165/98&td=ALL, 2016?09?15.
[16] 蔣紅珍. 論比例原則——政府規制工具選擇的司法評價[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7] 章劍生. 現代行政法總論[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編輯: 蘇慧]
On the improper competition in the minimum wage among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 Zhikai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The minimum wage in China is "non-market wage" formed unde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which has been in the public policy space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the tool of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violating the ration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How to ensure the behavioral rationa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officials while kee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solve. The reasonable judgmen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hind should jump out of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laborers' prote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the key review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guaranteeing the integrity, the liquidity and equity of econo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interests of laborers, with the key lying in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its narrow sense of "protection."
minimum wag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proportional principle
D912.1
A
1672-3104(2017)05?0053?06
2016?12?11;
2017?01?15
重慶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比例原則中國化的原理與應用路徑研究”(No.106112016CDJSK08XK21)
李志鍇(1981?),男,廣西桂林人,重慶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勞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