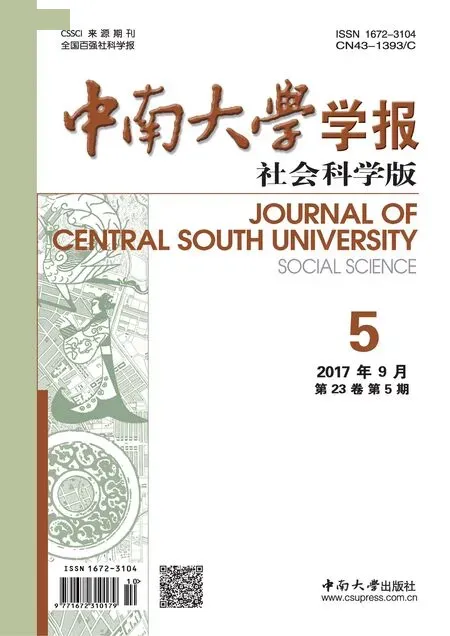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西游記》小說之前的觀音書寫——以“玄奘西行”題材為中心
周秋良
?
《西游記》小說之前的觀音書寫——以“玄奘西行”題材為中心
周秋良
(中南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湖南長沙,410083)
在以“玄奘西行”為題材的文獻(xiàn)作品中,有大量關(guān)于觀音的書寫。對其進(jìn)行縱向梳理,可以清晰地考察出我國早期觀音信仰的衍化軌跡。《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尚屬實(shí)錄性質(zhì),其中關(guān)于觀音信仰的敘寫,真實(shí)地反映了一個佛教信徒所親身經(jīng)歷的宗教體驗(yàn),但還沒有對觀音形象進(jìn)行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隨著“玄奘西行”故事的發(fā)展,觀音的地位日漸凸顯。在《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中,觀音雖作為主要神靈出現(xiàn),但還處于次要地位,也沒出現(xiàn)具體的真身形象。《西游記》雜劇是第一個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為目的的關(guān)于玄奘西行取經(jīng)的作品,觀音在取經(jīng)途中的作用大大加強(qiáng),已經(jīng)成為取經(jīng)隊伍的組織者和主要保護(hù)者,更主要的是,還首次出現(xiàn)了具體的南海觀音形象。小說《西游記》對南海觀音形象的塑造就是承接雜劇《西游記》而來的。
玄奘西行;觀音信仰;觀音書寫
觀音是《西游記》小說中一位舉足輕重的女神。小說通過對觀音形象的極力塑造,不僅寫出了觀音信仰的神圣性、宗教性,更寫出了觀音形象的世俗化、人情化。學(xué)界對于這樣一個充滿無窮藝術(shù)審美魅力的文學(xué)形象,已有多角度的解讀。其實(shí),在《西游記》小說成書之前的玄奘西行故事流傳中,還有著許多關(guān)于觀音的書寫,通過對這些觀音書寫的梳理,不僅可以考察《西游記》小說觀音形象的發(fā)展淵源,分析我國早期民間觀音信仰藝術(shù)化的規(guī)律和特點(diǎn),而且有助于我們對《西游記》小說成書過程的認(rèn)識,因?yàn)椤靶饰餍小鳖}材不斷被文學(xué)化的過程,即是《西游記》小說成書的過程。
一、“玄奘西行”實(shí)錄性書寫中的觀音信仰
唐代僧人玄奘本來就是一個虔誠的佛門弟子,在他16歲至20歲時,曾于成都的空慧寺(圣壽寺)修行五年,在此期間接受了佛教的具足戒,形成了觀音信仰并接受《般若心經(jīng)》的傳授[1]。爾后,玄奘西行取經(jīng),歷時十七載,經(jīng)歷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他不僅從印度帶回了諸多的佛教精典、諸佛塑像,還對古印度地理、政治、經(jīng)濟(jì)、宗教、哲學(xué)、民俗等許多方面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考察。自唐以來的歷史著作、筆記、佛典、小說等都留下了諸多關(guān)于“玄奘西行”的書寫。相比較而言,《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尚帶有鮮明的實(shí)錄性質(zhì)。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對自己西行路上所見所聞的記錄。因?yàn)樾蕦τ^音菩薩十分虔誠,所以他在西域取經(jīng)途中對所見聞的有關(guān)菩薩事跡也特別留意,并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描述。一路上他注意到的觀音圣像有:
(迦畢試國質(zhì)子伽藍(lán)北嶺上有數(shù)石室)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愿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身色,安慰行者。[2](143)
(烏仗那國)……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跡昭明。法俗相趨,供養(yǎng)無替。[2](288)
(摩揭陀國的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佛涅槃后,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biāo)界,東向而坐。聞諸耆舊曰:“相傳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dāng)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2](699)
(摩揭陀國那爛陀僧伽藍(lán))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zhí)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發(fā)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2](760)
這些觀音塑像表明了公元7世紀(jì)初期觀自在在印度受到了人們的普遍敬仰。另外,他還詳細(xì)記載了當(dāng)?shù)氐男磐絺兡苡H睹菩薩顯靈的事跡,如:
(孤山)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zhí)蓮華,頂戴佛像。常有數(shù)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像莊嚴(yán),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睹贍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是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yǎng)。自后諸王,尚想遺風(fēng),遂于其側(cè)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yǎng)不絕。[2](773)
(馱那羯磔迦國的清辯論師) ……于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xiàn)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愿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愿生睹史多天,于斯禮覲,尚速待見。”……[2](844)
這里不僅有古代印度一般民眾對于觀音信仰靈驗(yàn)故事的體驗(yàn),還有古印度高僧清辯求觀音保存其身以待彌勒下生事跡。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以觀察者的身份對古印度的觀音信仰進(jìn)行了仔細(xì)而全面的考察,并做了比較詳實(shí)的記錄,這些記錄反映了觀音靈驗(yàn)信仰在印度社會流傳的情況[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大唐西域記》相比,文學(xué)性較強(qiáng)些,內(nèi)容有了一些虛構(gòu),其中有多處關(guān)于玄奘對觀音信仰靈驗(yàn)體驗(yàn)的記載。玄奘一心朝圣,西行路上,歷經(jīng)千難萬險,唯有對佛法追求的執(zhí)著、對觀音信仰虔誠是他戰(zhàn)勝一切的動力:
后莫賀延磧長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玄奘)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jīng)》。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jīng)》,因常誦習(xí)。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繞人前后,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jīng)》,發(fā)聲皆散,在危獲濟(jì),實(shí)所憑焉。[4](16)
對觀音菩薩的靈驗(yàn)描述得更為神奇:
行百余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行路艱難,玄奘“專念觀音,西北而進(jìn)”。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魅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fēng)擁沙,散如時雨。……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幾將殞絕,不復(fù)能進(jìn),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舍。啟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yù),但為無上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wù),此為苦矣,寧不知耶?”如實(shí)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fēng)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行。[4](17)
在異國他鄉(xiāng),玄奘對自己在取經(jīng)路中的安全也沒把握,內(nèi)心充滿恐懼,面對傳說靈驗(yàn)的小孤山觀音菩薩,他也想尋找點(diǎn)慰籍。于是這位享譽(yù)五印的東土法師,也在菩薩前跪下了:
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華,穿之為蔓,將到像所,志誠禮贊訖,向菩薩跪發(fā)三愿:“一者,于此學(xué)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愿華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愿生睹使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愿華貫掛尊兩臂;三者,圣教稱眾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愿華貫掛尊頸項(xiàng)。”語訖,以華遙散,咸得如言。即滿所求,喜歡無量。其旁同禮及守精舍人見之,彈指鳴足,言未曾有也。當(dāng)來若成道者,愿憶今日因緣先相度耳。[4](78)
果然,菩薩對這位頂禮膜拜者也特別青睞,讓他體會到了最圓滿靈驗(yàn)的快感。
據(jù)其描述,玄奘處于危難時總會心念觀音菩薩,這樣一路上的危險就都能化險為夷:法師心念觀音,可以使心生邪惡的胡人改惡從善;心念觀音,可以使頓生動搖之念的自身意志堅定;心念觀音,可以減少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fù)無水草,顧影唯一”的沙河中的寂寞感;心念觀音,可以在水盡喉涸、幾將隕絕的困境中,狹處逢生,找到水草。這些充滿奇異性的記敘為后來戲曲小說的再創(chuàng)造奠定了基礎(chǔ)。
概括說來,在《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玄奘取經(jīng)與觀音菩薩的關(guān)系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奘在西去途中見到了沿途人們對觀音的崇拜情況;二是取經(jīng)途中玄奘在危難時,向觀音求助,觀音會應(yīng)聲而來救苦;三是玄奘在取經(jīng)圣地,就自己取經(jīng)的事情向觀音祈禱的靈驗(yàn)。這些內(nèi)容基本上是當(dāng)時人們尤其是作為一個佛教信徒所親身經(jīng)歷的宗教體驗(yàn),反映的是那時候較為普遍的觀音信仰,尚未對其信仰的對象——觀音菩薩的形象進(jìn)行有意的創(chuàng)造,不過這些實(shí)錄性的宗教體驗(yàn)成為后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 濫觴。
二、講唱、雜劇文學(xué)階段的觀音形象
隨著取經(jīng)故事的發(fā)展,觀音在故事中的地位開始顯現(xiàn)。《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①(下文簡稱《取經(jīng)詩話》)描述了唐僧和猴行者等在去西取經(jīng)途中所經(jīng)歷的種種磨難,他們一路上遇到了妖魔的阻撓,也獲得神靈的保護(hù),其中提到的神靈主要是大梵天王和觀音菩薩。就《取經(jīng)詩話》中寫到的兩位對三藏取經(jīng)起到保護(hù)作用的神靈來說,大梵天王的護(hù)持作用是主要的,他給予取經(jīng)者以非凡的能力去對付取經(jīng)途中遇到的妖魔:三藏遇到猴行者后,行者領(lǐng)法師到大梵天王宮,天王賜予他們一頂隱形帽、一條金環(huán)錫杖、一只缽盂,并囑咐他們在危難之時,只要對著天宮大聲呼喚一聲“大王”,就能獲得天王的幫助。后來他們走到了火類坳,遇到一大坑,“四面陡黑,雷聲喊喊,進(jìn)步不得。法師當(dāng)把金環(huán)錫杖遙指天空,大叫‘天王救難’,忽然杖起五里毫光,射破長坑,須臾便過”[5](12),果真是非常靈驗(yàn)。三藏師徒在取經(jīng)路上,也主要是靠這三件寶物的保護(hù),最后才到達(dá)目的地取得真經(jīng)。這大梵天王,本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創(chuàng)造之神,與濕婆、毗濕奴并稱為古印度的三大神,被佛教吸收后成為了釋伽的右脅持,后為“佛梵合一”的密宗所崇尚,得到了信徒的崇拜。在密教盛行的唐代,天王信仰迅速流行開來,傳說在唐朝與西藏和大食(阿拉伯)交戰(zhàn)時,著名的高僧一行曾建議唐玄宗祈求天王神力的幫助,果然靈驗(yàn)。[6]后來皇帝還詔告天下,在城門立梵天王像,以佑平安,民間也因此相信他一定有無比法力。這可能是他在《取經(jīng)詩話》中成為取經(jīng)路上消除妖魔之主要神靈的原因。
而較之于大梵天王的除惡解難,《取經(jīng)詩話》中觀音菩薩對三藏師徒的幫助處于次要地位,主要是觀音菩薩以自己的宏法、大善來普度眾生,即使是毒蛇野獸也不例外。如《入香山寺第四》,講到師徒二人來到了香山,開篇交代:
逶迤登程,遇一座山。名號香山,是千手千眼菩薩之地,又是文殊菩薩的修行之所。舉頭見一寺額號“香山寺”,法師與猴行者不免進(jìn)上寺門歇息,見門下左右金剛,精神猛烈,氣象生獰,古貌楞層,威風(fēng)凜冽。法師一見,遍體汗流,寒毛卓豎。猴行者曰:“請我?guī)熑雰?nèi)巡賞一回。”遂與行者同入殿內(nèi)。寺中都無一人,只見古殿巍峨,芳草連帛絲,清風(fēng)颯颯。法師思維:此中得恁寂寞。猴行者知師意思,乃云:“我?guī)熌牐髀芳帕取4酥袆e是一天,前去路途盡是虎狼蛇兔之處,逢人不語,萬種恓惶,此去人煙都是邪法。”法師聞言,冷笑低頭,看遍周回,相邀便出。[5](16?17)
可見香山寺在他們?nèi)〗?jīng)途中是一個重要的驛站,而且這寺院又是千手千眼菩薩之地。后來,師徒來到了與香山寺不遠(yuǎn)的蛇子國、獅子林,那里的毒蛇與猛獸“大小差殊,且皆有佛性,逢人不傷,見物不害”,他們來到此地,“其蛇盡皆避路,閉目低頭”,獅子“搖頭擺尾,出村迎送”。這些只是從側(cè)面頌揚(yáng)了觀音的佛法無邊,以致香山四周的毒蛇猛獸都結(jié)上了佛緣,法師就此留詩:“行過蛇鄉(xiāng)數(shù)十里,請朝寂寞號香山,前程更有多磨難,只為眾生覓佛緣”[5](17)。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點(diǎn)明香山是千手千眼菩薩的地方,也就說明了《取經(jīng)詩話》時期南海普陀山還沒有被認(rèn)為是觀音的主道場。這里把千手千眼觀音和香山聯(lián)系在一起,與北宋《香山傳》中說到的妙善在香山寺顯化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傳說相同,反映出妙善傳說在當(dāng)時的流傳情況。但是《取經(jīng)詩話》又說這香山寺還是文殊菩薩的修行之所,而文殊菩薩的應(yīng)化道場是在五臺山,不知《取經(jīng)詩話》中的香山寺與五臺山關(guān)系如何?還有待進(jìn)一步考證。
可以看出,《取經(jīng)詩話》中的主要神靈是大梵天王,而觀音菩薩則處于次要的地位,僅僅提到了香山寺千手千眼菩薩的善化作用。同時,在《取經(jīng)詩話》中,不管是天王還是觀音菩薩,始終都沒有出現(xiàn)具體的真身形象,而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西游記》雜劇②可以說第一個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為目的的關(guān)于取經(jīng)故事的作品。全劇共六本二十四出,繼承和發(fā)展了《取經(jīng)詩話》“歷經(jīng)磨難終于成功”的故事類型,并對具體的取經(jīng)過程進(jìn)行了豐富的創(chuàng)造:其一,故事情節(jié)更加曲折。唐僧自出世就歷遭禍殃,出家為僧,后奉旨西行取經(jīng),經(jīng)歷了流沙河、黃風(fēng)山、紅孩兒、黑風(fēng)洞、女人國、火焰山等諸多磨難,終于到達(dá)西天佛地雞足山,取得真經(jīng)傳回東土,自己也證果成佛。其二,人物形象有世俗化傾向。劇中不僅出現(xiàn)了“師徒加龍馬”的取經(jīng)群體,而且出現(xiàn)了較多的神靈,有佛教的觀音菩薩、佛祖、鬼子母、華光天王等,還有道教的玉帝、二郎神以及黑豬精等。這種有佛有道、亦神亦魔的神靈世界反映出作品與民間信仰的關(guān)系,而塑造的各色神靈形象也具有了民間性。曾有論者指出:雜劇在把取經(jīng)人物出身來歷神異化的同時,卻把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寫得更加世俗化,形成了有趣的二律背反。這既是佛教日益滲透于民間、更加本土化的結(jié)果,又是元末明初東南沿海新興市民階層興起,個性解放思潮影響所致。正是這種新的社會變化,引起人們思想觀念進(jìn)一步世俗化,促使取經(jīng)主題由弘揚(yáng)佛法變?yōu)榉从呈浪咨鐣偈谷宋镄愿裼沈\的佛教徒變?yōu)橐喾稹⒁嗟馈⒁嗳澹醵錆M市民氣息[7]。其三,在這充滿市民氣息的作品中,觀音菩薩的地位開始突顯。在取經(jīng)途中,觀音的作用大大加強(qiáng)了,而在《取經(jīng)詩話》中處于主要地位的大梵天王則下降到次要地位了。下面我們結(jié)合具體內(nèi)容來分析。
劇本第一本的正名為“觀音佛說因果,陳玄奘報大仇”,這就直接地突出了觀音地位。第一出《之官逢盜》中觀音登場時交代自己是在南海修行,為了取經(jīng)之事而來到東土:
(觀世音上云):旃檀紫竹隔凡塵,七寶浮屠五色新。佛號自稱觀自在,尋聲普救世間人。老僧南海普陀落伽山七珍八寶寺紫竹旃檀林居住,西天我佛如來坐上徒弟。得真如正偏知覺,自佛入涅槃后,我等皆成正果。涅槃?wù)吣藷o生無死之地。見今西天竺有《大藏經(jīng)》五千四十八卷,欲傳東土。爭奈無個肉身幻軀的真人闡揚(yáng),如今諸佛議論,著西天毗盧伽尊者托化于中國海州弘農(nóng)縣陳光蕊家為子,長大出家為僧,往西天取經(jīng)闡教。爭奈陳光蕊有十八年水災(zāi),老僧已傳法旨于沿海龍王隨所守護(hù),自有個保他的道理。不因三藏西天去,哪得金經(jīng)東土來。[8] (652)
可見,觀音對取經(jīng)的因由非常了解,三藏的身世也全在她的掌握中,并提前做好了安排,讓玄奘報其父仇,命龍王救其亡父,十八年后,令其父還生,一家團(tuán)聚。江流報仇后,觀音又安排玄奘的取經(jīng)工作:
(觀音佛上高垛云)眾官見老僧么?(眾做拜科)(觀音云)長安城中今大旱,可著玄奘赴京師祈雨救民。我佛有五千四十八卷大藏金經(jīng),要來東土,等玄奘來,虞太守聽我叮嚀,依老僧國祚安寧,陳光蕊全家封贈。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下)(夫人唱)云頭上顯出白衣士……[8] (652)
后來,虞世南遵從觀音的法旨推薦玄奘到長安祈雨,“玄奘打坐片時,大雨三日”。太宗因此賜玄奘“金襤袈裟,九環(huán)錫杖,封玄奘為經(jīng)一藏,法一藏,輪一藏,號曰三藏法師”,并要他奉旨“馳駿馬赴西天,取經(jīng)歸東土,以保國祚安康,萬民樂業(yè)”[8](658)。玄奘登上西去取經(jīng)的征途,觀音又為玄奘取經(jīng)做了周密的安排。
首先,觀音組織了取經(jīng)隊伍。她既為唐僧準(zhǔn)備了西去取經(jīng)的腳力,在玉帝面前救得行雨差池的火龍三太子,著他化作一白馬,隨唐僧去西天馱經(jīng),然后復(fù)歸南海為龍,傳法旨叫徒弟木叉行者化作一個賣馬的客商,送馬與唐僧;又為唐僧物色了西去路上的保護(hù)人孫行者,把這孫行者壓在花果山下,叮嚀山神要看緊這通天大圣:
(李天王、那吒等與通天大圣斗,觀音出來救起。)(觀音上云)天王見老僧嗎?(天王云)我佛何來。(觀音云)老僧特來抄化這猢猻,與唐僧為弟子,西天取經(jīng)去,休要?dú)⑺?天王云)這廝神通廣大,如何降服得他。(觀音云)將這孽畜壓在花果山下,待唐僧來著他隨去西天取經(jīng)便了。(眾綁行者上)(觀音云)將他壓住,老僧畫一字,你那廝且頂住這山者,(做壓科)(行者云)佛羅,好重山也呵。……(觀音云)道與山神,看得這廝緊者。(下)[8](667)
其次,觀音為取經(jīng)成員組織了保官隊伍,并自我擔(dān)負(fù)起保官隊長的重?fù)?dān)。
(觀音引揭帝上云)老僧為唐僧西游,奏過玉帝,差十方保官都聚于海外蓬萊三島。第一個保官是老僧。第二個保官李天王,第三個保官那吒三太子,第四個保官灌口二郎神,第五個保官九曜星辰,第六個保官華光天王,第七個保官木叉行者,第八個保官韋馱天尊,第九個保官火龍?zhí)樱谑畟€保官回來大權(quán)修利都,保唐僧沿路無事。寫了文書,要諸天畫字,都畫字了,則有華光未至,此時想必來也。(華光上云)釋道流中立正神,降魔護(hù)法獨(dú)為尊,驅(qū)馳火部三千萬,正按南方位丙丁。某乃佛中上善,天下正神。觀音佛相請,須索走一遭。[8] (652)
這一龐大的保官隊伍對取經(jīng)的成功起到關(guān)鍵作用,尤其是觀音菩薩,她一路與唐僧師徒保持著聯(lián)系,遣二郎神細(xì)犬收服豬八戒,派韋陀護(hù)法救出困在女兒國的唐僧,差水部的雷公雷母神滅掉火焰山的火,為他們掃除一路的困難,為他們能順利取得真經(jīng)提供了安全保障,見表1所列情節(jié)。
概括說來,雜劇中的觀音菩薩,作為一神靈,集中表現(xiàn)了她的神性。她先知先覺,對玄奘的身世非常了解,并為其做了周密的安排;她神通廣大,能上天下地,能呼風(fēng)喚雨,因此眾人對于她,是十分虔誠,每次見到,都要頂禮膜拜,即使是悟空也不例外。同時,觀音又成為了玉帝旗下的一員,這是與《取經(jīng)詩話》一個主要不同的地方。觀音和玉帝的這種關(guān)系反映的是北宋真宗年間以來,隨著道教地位提升,玉皇大帝成為民間信仰中的最高神靈的現(xiàn)象,觀音這位佛教菩薩也被納入到道教神靈的體系中。
更主要的是,就觀音在取經(jīng)故事的發(fā)展歷史來看,戲劇中首次出現(xiàn)了具體的觀音形象。作品不僅通過具體的語言、行為、情節(jié)塑造出具有文學(xué)意蘊(yùn)的觀音形象,而且舞臺上還出現(xiàn)了具體的觀音扮相,雖然劇本沒有用明確的穿關(guān)、科介來描述,但我們還是能從劇本中捕捉到觀音形象,如觀音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在南海普陀巖居住;虞太守夫人見到的觀音是白衣士;唐僧師徒也已經(jīng)可以一睹觀音真容。這是在“玄奘西行”取經(jīng)故事中首次出現(xiàn)的、具體的南海觀音形象,但又是穿著白色的行頭。這種具體的觀音形象是當(dāng)時社會觀音信仰現(xiàn)實(shí)情況的反映,這些具體的物相又為后來小說的創(chuàng)造提供了線索。

表1 《西游記》雜劇塑造觀音形象的情節(jié)總覽
還需說明的是,雜劇中觀音自稱為“老僧”,反映出當(dāng)時人們對觀音菩薩的崇拜心理。觀音以老僧自稱,與觀眾的心理距離比較遠(yuǎn),顯得不親切。而且由“老僧”這詞可以想象其形象比較呆板,給人一種固作姿態(tài)的感覺。這種效果的出現(xiàn),實(shí)際上也是合乎當(dāng)時觀音信仰的實(shí)際的,是因?yàn)槊癖妼τ^音過于迷信而產(chǎn)生的一定的敬畏心理。
然而,雜劇所塑造的觀音形象是小說《西游記》中觀音形象形成的關(guān)鍵點(diǎn)。把雜劇塑造的觀音形象放到取經(jīng)路途涉及到的神靈的變化發(fā)展歷史中相互比照,就可以看出雜劇中觀音形象的特色及其在取經(jīng)故事傳播中的地位:《取經(jīng)詩話》中無論是大梵天王的應(yīng)聲降魔,還是千手千眼菩薩的佛法善化毒蛇猛獸雄獅等等,都是為宣揚(yáng)佛法弘大,《取經(jīng)詩話》“從藝術(shù)形式和思想內(nèi)容方面都表現(xiàn)出是一部宏揚(yáng)佛法的宗教書籍”[9],而且其中表現(xiàn)觀音的內(nèi)容很少。雜劇中眾多神靈的塑造反映的則是民間信仰,尤其是民間觀音信仰內(nèi)容,劇中觀音已經(jīng)成為取經(jīng)隊伍的組織者和主要保護(hù)者,全面表現(xiàn)了觀音的神通廣大,同時戲劇也表現(xiàn)了對玉帝的肯定,《取經(jīng)詩話》中那處于主要地位的保護(hù)神大梵天王已經(jīng)變成了民間的托塔李天王并處于次要的地位了。這些都是宋代以來民間信仰的特點(diǎn)。
三、結(jié)語
通過考察《西游記》小說成書之前的觀音書寫發(fā)現(xiàn),觀音信仰在“玄奘西行”取經(jīng)故事中的地位并非一開始就很突出,而是不斷加強(qiáng)的,其形象也是不斷豐富和完善的,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中土觀音信仰的漸變性。
小說《西游記》對觀音形象的塑造承接雜劇《西游記》而來,尤其是秉承了雜劇那種以民間信仰為主要創(chuàng)作源泉的傳統(tǒng)。如對于孫悟空被壓在山下的情節(jié)的處理,雜劇中是觀音把孫悟空壓在花果山下,并畫了一字(符),讓孫悟空不能頂起那花果山,而小說則把壓伏孫悟空這樣的“壞事”移到了如來的身上,如來把孫悟空壓在五行山下,并在山上貼上一張?zhí)樱@帖子上寫的是觀音咒中的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哞”六字。這如來怎么會和觀音的咒語一樣呢?其實(shí),這既體現(xiàn)了雜劇對小說的影響,也反映了民間信仰的特色。貼上字符的情節(jié)是從雜劇而來,而如來也能隨手用這“唵嘛呢叭咪哞”六字神咒的細(xì)節(jié),反映出民間信仰中那種對于佛教神靈以及相關(guān)事跡的認(rèn)識模糊性,人們不會明白這“唵嘛呢叭咪哞”是觀音的專用咒語,以為隨便是誰都可以說的,只要你與佛有緣。因此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也就不會甄別如來能不能用它了。
然而,《西游記》小說對觀音形象又有著高于雜劇的創(chuàng)造,尤其是小說中對觀音形象所具有的更多人性的塑造,是將觀音菩薩這一信仰民俗化、藝術(shù)化的典范。于是,對于《西游記》小說中的南海觀音形象及其與觀音信仰文化之間的深層關(guān)系,也值得我們特別關(guān)注。
注釋:
① 《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應(yīng)是產(chǎn)生于北宋中后期的一個宋人的話本,屬于“說經(jīng)”類,這類話本既包括演說佛教經(jīng)籍,又有演說佛教史籍的內(nèi)容,主要是為了弘揚(yáng)佛法,根據(jù)今存或已不知存佚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目連救母故事、僧伽降無支祁故事和唐僧取經(jīng)故事三種。
② 雜劇現(xiàn)存的版本雖為明萬歷四十二年,但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應(yīng)是元代所作。在《錄鬼薄續(xù)編》中就記載有楊景賢的《西游記》。
[1] 祁和暉. 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xí)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 2008(12): 241?247
[2] 玄奘, 辯機(jī)原. 大唐西域記[M].季羨林, 等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3] 李利安. 玄奘法師對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考察[EB/0L]. http:// www.gming.org/fjrw/jsrw/lilian/40991.html, 2014?12?26.
[4] 慧立, 彥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5] 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M]. 上海: 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 1955.
[6] 不空. 毗沙門天王經(jīng). 大正藏(21冊)[C]. 臺北: 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 1990: 217.
[7] 馬冀. 雜劇西游記思想內(nèi)容的時代特色[J]. 內(nèi)蒙古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 2000(6): 30?35.
[8] 楊景賢. 西游記. 元曲選外編[C].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652?667.
[9] 張錦池. 西游記考論[M].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7.
[編輯: 何彩章]
The writing of Avalokitesvara beforeOn the theme of “Xuan Zang westbound”
ZHOU Qiu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unan 410083, China)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ry works written on the theme of “Xuan Zang westbound”. Combing longitudinally, we can clearly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China’s early goddess of mercy trajectory. The “Buddhist Records” and “Da Ci’en Temple Tripitaka Master Biography” are of the nature of record, in which the narration of belief in Guanyin truly reflected a Buddhist's religious experience, but no conscious creation about Guanyin had come out up to that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of “Xuan Zang westbound,” Guanyin's position became prominent. In “Xuan Zang,” the main deity appears as a goddess, but in the secondary position with no specific body image. The dramais the first literary creation about Xuan Zang westbound, in which Guanyin's role in their pilgrimage is greatly strengthened as the organizer and major protector of the pilgrimage group and more importantly with a specific image as the South China Sea Guanyin. The South China Sea Guanyin image in te novelis taken from the drama.
Xuanzang westbound; Guanyin faith; Guanyin writing
I207
A
1672-3104(2017)05?0184?06
2017?03?30;
2017?08?25
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女神書寫研究”(15BZW069);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以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教育為切入點(diǎn)培育大學(xué)生文化自信研究”(16ZXB01);湖南省社會科學(xué)成果評審委員會項(xiàng)目“高校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教育與大學(xué)生文化自信之培育”(XSP17YBZC200)
周秋良(1971?),女,湖南衡山人,博士,中南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xué),傳統(tǒng)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