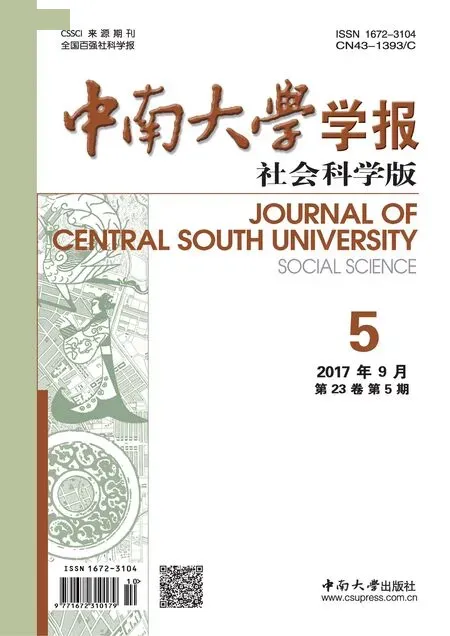戰時強迫失蹤與國際人道法的規制考量
邵懌
?
戰時強迫失蹤與國際人道法的規制考量
邵懌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100270;奧斯陸大學挪威人權中心,奧斯陸,0864)
有鑒于二戰后拉丁美洲各國的廣泛使用,強迫失蹤早期往往被定義為一項“國家鎮壓政策”,其實質是對于人權大規模、系統的侵害。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強迫失蹤與戰爭及武裝沖突的結合開始日益密切化、常態化以及主流化,越來越多地被交戰方視為一種作戰手段來加以使用。雖然當前直接針對強迫失蹤行為與相關受害人救濟的規制在國際人道法淵源之中依舊處于空白,但總結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相關規定,通過對平民與戰俘的拘留程序進行規范,對個人戰時家庭生活權與公正司法權的保障,可以從根源上抑制戰時強迫失蹤的發生,進而最大限度地維護戰時基本人權的享有。
強迫失蹤;國際人道法;日內瓦公約;國家行為;家庭權
一、引言
強迫失蹤本身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事實上,最早的有關強迫失蹤行為的記錄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德國[1],其于1941年頒布的“夜霧法令”賦予了有關公權力主體對罪犯及持有政治異議的主體實施秘密逮捕并不對外宣布的權力[2,3]。據統計,有將近7 000人被秘密逮捕、轉移甚至最終被處決[4]。在二戰結束以后,強迫失蹤行為并沒有隨著納粹的滅亡而銷聲匿跡,相反,在20世紀60?80年代,強迫失蹤在拉丁美洲各國得到了廣泛的使用。這其中以包括阿根廷、烏拉圭等在內的“禿鷹計劃”國家最為嚴重①[5,6]。以阿根廷國家失蹤人員委員會1986年的報告為例,在長達7年的國內軍事獨裁期間,阿根廷全國共有約12 000人被迫或非自愿失蹤,并且在報告提交之時,仍有8 960人下落不明。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議中,“強迫或非自愿失蹤問題工作組”(以下簡稱“工作組”)的報告也表示,自1980年以來,工作組收到的關于阿根廷的強迫失蹤報告共計3 449起,收到的關于智利的報告有908起[7]。
考慮到多數拉美國家與納粹德國在政治制度上的共性,加之二者都以國家法律的形式來為非法的強迫失蹤行為背書,都以形式合法的行為來非法侵犯個人的基本人權,因此,強迫失蹤在早期往往被學界認為是一種國家鎮壓政策(state repression policy),乃至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8,9],其實質是一種系統的、大規模的人權的侵權行為[10]。但這種認識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遭到了現實的質疑,隨著哥倫比亞內戰、土耳其內戰、第二次車臣戰爭、美國“反恐戰爭”、敘利亞內戰等的相繼爆發,學界開始認識到,強迫失蹤不僅僅只是一種“區域現象”,也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11];不僅僅只是一項“國家鎮壓政策”,也可能是一種“作戰手段”;不僅僅只是一種人權問題,也可能是一項戰爭罪行。正因如此,考慮到現實的發展,以不同的視角,尤其是從國際人道法的視角,來看待并解讀強迫失蹤便具有了顯著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二、強迫失蹤:從國家政策向作戰手段的轉變
自二戰以來,強迫失蹤之所以廣受拉丁美洲國家青睞,主要因為其存在著兩方面的現實需求:首先,拉丁美洲國家自二戰結束以后紛紛確立了新型資本積累模型(capitalist accumulation model)[9]。該模型一方面對市場經濟基本結構采取了摒棄的態度,另一方面加重了社會底層人民的負擔,進而直接導致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其次,拉丁美洲各國獨立于二戰的硝煙之中,部分國家的獨裁政治體制與民眾對民主改革訴求的矛盾日益加深,這促使了國家公權力部門尋求更為高效的措施來壓制國內的反對聲音與抗議行為。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拉美各國紛紛確立強迫失蹤行為在國內法中的合法性,紛紛以國家政策或法律性文件來對強迫失蹤的正當性背書[12],以至于有學者表示,腐敗與系統化的強迫失蹤已經成為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特征[9]。
不可否認,雖然作為一種“國家政策”的強迫失蹤曾經得到了拉美各國的廣泛采用,但上述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了根本性的好轉。從數據上來看,隨著軍事獨裁國家的相繼轉型[13],強迫失蹤在傳統的高發國家有了明顯的減少。如工作組2015年的報告顯示,自1980年以后,工作組年均收到的關于阿根廷國內強迫失蹤行為的報告僅為1起。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了其他原“禿鷹計劃”國家[7]。但從全球范圍來看,強迫失蹤實際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抑制,其總量反而一直在增長,這種增長在一些爆發戰爭或武裝沖突的國家里尤為明顯。在這些國家,強迫失蹤往往隨著沖突的發生而井噴式地爆發,隨著沖突的結束或者中止而又迅速回落。如俄羅斯,隨著第二次車臣戰爭的爆發,2000年工作組收到的涉及俄羅斯的強迫失蹤報告從上一年度的2起激增到147起。而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京于2002年宣布結束車臣戰爭,工作組收到的報告數量便隨之銳減為6起[13]。再如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自其2011年爆發內戰以來,工作組收到的關于敘利亞國內的強迫失蹤報告便從3起增加到38起[13]。同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還對外表示:僅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后的8個月內,已有超過4 000人被報道確認死亡,數以千計的人員被逮捕(arrest),更有至少14 000人因為鎮壓(crackdown)而被拘禁(imprisoned)[14]。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蘇丹共和國、斯里蘭卡、東帝汶等國。
如果將戰爭或武裝沖突爆發年份與工作組收到的關于強迫失蹤的來文數量進行比照,選取俄羅斯與敘利亞兩個國家,可以得到圖1和圖2②。
結合圖1和圖2,我們可以發現,如果說早期拉丁美洲各國的強迫失蹤多為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國家政策的話,那么,在當今時代,強迫失蹤行為則更多地與戰爭及武裝沖突聯系到了一起。如上文所述,強迫失蹤行為的數量隨著沖突的爆發而激增,又隨著沖突的結束或者抑制而回落。引用2013年5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布的《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獨立國際調查委員會的口頭更新》()的表述:“在過去的三年時間內,在敘利亞內戰中,發生了包括:謀殺、酷刑、性侵、非法處決、強迫失蹤等多項反人道罪行。”[15]在這其中,強迫失蹤已經成為了一種在戰爭中被廣泛使用的作戰手段(tactic)③[14]。因此,這也決定了我們有必要基于社會、政治的新發展,在傳統的人權視野之外,從國際人道法的角度來挖掘戰時強迫失蹤的個性,以戰爭法為淵源思考對于強迫失蹤的約束與限制。

圖2 工作組1999—2003年關于俄羅斯來文統計
三、戰時強迫失蹤的比較分析
對于強迫失蹤的定義,國際上并沒有形成合意。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2條將其定義為:強迫失蹤系指由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實施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的行為,并拒絕承認剝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較為權威的定義還包括《美洲強迫失蹤人員公約》()第2款:強迫失蹤是對個人自由的剝奪,這種剝奪可以直接來自于國家機關或者來自獲得授權、支持、默許的組織或個人,行為人同時拒絕對外透露被強迫失蹤人員的具體信息以阻止受害人獲得法律補償或者程序救濟。除此以外,《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也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強迫失蹤是一種反人道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是指國家或政治組織直接地,或在其同意、支持或默許下,逮捕、羈押或綁架人員,繼而拒絕承認這種剝奪自由的行為,或拒絕透露有關人員的命運或下落,目的是將其長期置于法律保護之外。雖然,各個國際性文件對于強迫失蹤的定義不盡相同,但都將強迫失蹤行為視為是對基本的或者不可減損(non-derogable)人權的嚴重侵犯,是危害人類的罪行。同時,以下三個構成要素也是為各定義所一致認同的:首先是對個人自由權的任意剝奪;其次是隱瞞受害人失蹤的事實與相關消息;最后,強迫失蹤的行為主體是國家機關或國家授權、支持或者默許的組織或個人。可以說,上述三個要素是判斷一項行為是否構成強迫失蹤的基礎性標準。但是,在具備上述共性之外,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強迫失蹤又會具有不同的個性,在行為主體、行為動因、追責等方面,戰時強迫失蹤便顯著區別于作為國家政策的強迫失蹤。
(一) 戰時強迫失蹤行為主體的確定
在戰爭與武裝沖突環境中,強迫失蹤最為顯著的個性便在于行為主體的復雜性。如上所述,強迫失蹤是一種國家行為,其主體必然是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在非沖突環境中,由于一國之內只存在一個統一的政府,因此行為主體的確定較為簡單、明確,且通常都是單一的主體。但在戰時,尤其是一國內戰之中,會存在多個主體分別宣稱自身為國家合法主體的情形④,也會存在多個主體分別在一國不同領土范圍內獨立行使公權力并組建公權力組織的情形⑤。因此,考慮到在一國主權范圍之內可能存在多個適格主體,戰時強迫失蹤的行為主體不能依舊以國家為單位來加以確定。依據聯合國2001年《國家國際不法行為草案》()的規定,任意組織在滿足如下兩方面條件中任意一項的情況下,可被視為國家主體,其行為也可被視為國家行為:首先,早前的政府對其部分管轄范圍出現了徹底的權力的真空(completely vacuum of power),且已有私主體和組織在此區域建立了完整的政治與司法組織形式;其次,新生的(insurgent)組織計劃推翻并取代原有的國家政府⑥[16,17]。以敘利亞內戰為例,依照聯合國《國家國際不法行為草案》的標準,敘利亞政府由于得到了國際上的普遍承認,其行為當然可被視為國家行為。但敘利亞國內主要的反對派組織“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由于致力于推翻現有的政府并且已在其勢力范圍內實際行使了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18],因此,其也可以被視為國家主體,進而也可以被視為強迫失蹤的適格主體。除此以外,《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7條第2款第9項也明確表示“政治組織(political organization)”可以成為強迫失蹤的主體,只要該組織具有政治目的(purpose)或野心(ambition),且代行了部分國家職能[19,20]。如哥倫比亞國內的部分區域,政府已經逐漸喪失了對其麾下部分區域的游擊隊(guerilla)的控制權,這些游擊隊雖然并沒有切實的政治目的,但實際上也已經代行了政府的部分功能[19],因而也可以被視為強迫失蹤的行為主體。
(二) 戰時強迫失蹤行為的動因與性質
傳統觀點認為,實施強迫失蹤行為的動因基本可以概括為“緘默反對聲音”與“實施懲戒與報復”這兩項[12]。也正因如此,強迫失蹤往往被定性為繼續行使其他罪行的一個途徑(gateway)[21],純粹為了失蹤而失蹤的情形并不常見。但在戰爭與武裝沖突的環境中,強迫失蹤行為并非總是其他罪行的先行“途徑”,其常常被定義為一種作戰手段。在國際人道法中,常見的作戰手段有多種,如恐懼戰、謀殺、饑餓、圍城、計謀等等⑦。在沖突中,強迫失蹤行為會在如下兩種情況下被視為作戰手段:首先是傳播恐懼以削弱交戰對方的戰斗意志。這種情況較為常見,包括秘魯內戰、敘利亞內戰[21]等在內,都出現過類似的以強迫失蹤行為為手段來實施“恐懼戰(terror attack)”的情形。其次,也存在出于敲詐勒索的目的而展開的強迫失蹤行為,實施強迫失蹤行為的一方希望借此換取對方控制的己方人質,如車臣對俄羅斯武裝人員所實施的強迫失蹤[22]、尼泊爾政府和共產主義分子的武裝沖突[23]等等。也可能是單純地進行物質敲詐,如上述的敘利亞內戰。當強迫失蹤基于勒索目的而實施時,其又會構成國際人道法中的另一項非法戰爭手段,即“挾持人質(hostage-taking)”[21]。
另外,在戰時,強迫失蹤在部分情況下也不具有主觀的故意性。如在車臣戰爭末期,俄羅斯為了有效解決車臣地區的“分裂行動(separatist movement)”,基于1998年《反恐法》()與1996年《防御法》()的規定,以反恐和國家安全為名秘密關押了超過3 000名車臣戰俘[6]。不同于非沖突環境下的強迫失蹤,上述強迫失蹤行為并非是繼續行使其他罪行的一個途徑,也并非出于“緘默反對聲音”與“實施懲戒與報復”這兩項動因,其實際是對于戰俘的非公開關押,是一種非法的戰俘處置行為。在此情況下,對于戰俘的非公開關押可能是出于受害人主觀的意愿,也可能是來自客觀環境的約束⑧。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了土耳其內戰和美國在巴基斯坦、約旦以及敘利亞實施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之中[6]。
(三) 戰時強迫失蹤行為的約束與追責
如上所述,主體的復雜性是戰爭及武裝沖突環境中強迫失蹤行為的一項顯著特征。也正是該項特征,導致了對沖突中強迫失蹤的約束與追責要遠難于作為國家恐怖主義而被加以實施的強迫失蹤。當前專門性的國際人權法規制,如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主要針對的是締約國,對于非締約國以及非傳統的國家主體,如敘利亞內戰中的反對派武裝、哥倫比亞游擊隊等則不具有可適性基礎。強迫失蹤受害人能夠得到及時救濟的前提是國內的國家機關之間存在有明確的分權制衡機制,且司法或者相關權力機關能夠獨立地對被指控的行為主體展開調查與追責行為,如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第9條便要求締約國在其管轄的領土上確定對強迫失蹤罪案的司法管轄權。但在戰時,由于交戰雙方可能是兩方獨立的國際法主體,一般性的國內機構無法得到交戰各方的認同進而集中行使司法權。即便是依據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設立的強迫失蹤委員會以及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由于缺乏實質性的國內司法權與強制執行權,也無法有效地對強迫失蹤行為進行追責,無法對受害人進行救濟。因此,除非戰爭結束,不然無法組建一個統一的政權來對強迫失蹤行為進行統一的追責。但在沖突平息之后,期望勝利方會對自身的行為進行及時的檢討與追責,多少有點不切實際。如秘魯內戰時期以藤森總統為首的政府對“光榮道路”成員的非人道罪行,由于藤森于1995年通過了特設法案以終止對所有強迫失蹤以及屠殺案件的審理,因此相關罪行直到2000年其卸任后才由于政治因素被起訴[24,25]。又如美國在巴基斯坦實施的“反恐戰爭”,戰勝方巴基斯坦政府軍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共同實施的強迫失蹤行為,至今沒有任何人對此負責或者受到追究[26]。可以說,面對戰時強迫失蹤罪行,傳統的國際人權法規制由于高度依賴締約國國內司法機關的管轄權,加之自身在適用上存在的局限與限制,其效用很難發揮。因此,預期有效地對戰時強迫失蹤行為進行約束與追責,我們更需要從國際人道法的規制中去尋求有針對性與普適性的法律規制。
四、戰時強迫失蹤的國際人道法規制
(一) 強迫失蹤對于國際人道法的違反
參考日內瓦四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的規定,結合上述強迫失蹤的定義與行為性質,筆者認為強迫失蹤行為主要從如下三個方面構成了對國際人道法的嚴重違反,包括:對自由權的任意剝奪(arbitrary deprivation of liberty)、非人道的對待(inhuman treatment)以及任意的殺害(willful killing or murder)。
1. 對自由權的任意剝奪
無論是依據日內瓦公約⑨及其議定書⑩的相關規定還是參照國際習慣法[27],任何對自由權的剝奪都應當是合法的與非任意性的[28],日內瓦第四公約總結認為任意的拘留包括有“非法關押(unlawful detainment)”以及“無理由拘留(internment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對自由權的任意剝奪定義為:基于政治理由(view)的剝奪,沒有具體控訴理由(specific charges)的拘留以及無法對外交流的(incommunicado)拘留[29]。不難看出,無論參照哪種標準,強迫失蹤都構成了對自由權的任意剝奪,構成了對國際人道法的違反。
2. 非人道的對待
讓·皮克泰先生曾總結,國際人道法的基本原則應當包括對喪失戰斗力或未直接參與作戰行動人員的尊重、保護和人道待遇[29];同樣,這項原則也體現在了國際習慣法之中[27]。需要注意的是,國際人道法并未以條款的形式明確對“人道對待(humane treatment)”進行定義,但卻以列舉的方式介紹了“人道對待”應具有的要素,包括:對于退出戰斗的個人(hors de combat),其個人人身、榮譽(honor)以及宗教法人(religious conviction)應當得到尊重;免于一切形式的暴力行為或者暴力威脅。另外,任何能夠引起物理痛苦(physical suffering)以及滅絕的行為都不應當被視作人道對待。除此以外,日內瓦公約還對戰時的信息收集做出了規定:在信息收集的過程中,個人以及第三方應當免于任何物理形式的或者道德形式的強迫;拒絕回答問題的戰犯,也應免受威脅、攻擊或者任何不利的對待。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依照讓·皮克泰在日內瓦第三公約評論中的觀點,無法與外界聯系的拘留行為本身便是非人道的,而秘密的拘留又是構成強迫失蹤的必要要素。因此,即便強迫失蹤行為本身不伴隨任何的物理痛苦、不與其他酷刑相結合,也屬于非人道的對待[30],進而構成了戰爭罪,更何況強迫失蹤行為通常都伴隨著對受害人的任意處決與酷刑對待。
3. 任意的殺害
強迫失蹤與謀殺在很多情況下是相伴而生的。如上所述,強迫失蹤在部分情況下會成為謀殺的預備行為。盡管在國際人道法的通常認識中,生命的損失在所難免,是戰爭通常伴隨的后果,但是,任意的謀殺卻是為國際人道法所嚴格禁止的,無論是在日內瓦各公約之中,還是國際習慣法之中[27],都明確將對平民或者囚犯任意的殺害視為戰爭罪。
(二) 戰時針對強迫失蹤的約束與救濟
縱觀日內瓦公約以及相關國際習慣法,目前并沒有專門性的國際人道法條款來對強迫失蹤行為進行約束,也沒有專門性的條款來對受害人加以救濟,但這并不代表強迫失蹤行為處于法律的空白領域。考慮到強迫失蹤的三大要素,即對個人自由權的任意剝奪、隱瞞被失蹤人失蹤的事實以及國家主體行為,實際上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中有大量的條款可以被引用以約束、限制上述三要素在戰時的發生,進而從根本上杜絕強迫失蹤行為的發生。這些條款主要側重于規范逮捕、拘留的相關程序,力求實現自由權、公平審判權以及家庭生活權在戰時的保障。同時,如果以作用對象來劃分的話,上述條款又可以分為針對平民與針對戰俘這兩類。
1. 戰時針對平民的保障措施
日內瓦第四公約認為在戰爭及武裝沖突環境下,作為非戰爭參與者的普通平民需要得到特殊的保護。但上述身份需要建立在如下的任一前提之上:首先,平民必須身處沖突的領土范圍之內;其次,平民所處的領土已經實際為交戰一方所占領。上述的特殊保護主要針對平民的拘留、轉移與司法程序三個方面。在戰爭及武裝沖突過程中,對于非沖突參與者的平民的拘留并不當然地為國際人道法所禁止,拘留本身也并不被視為是一種懲罰措施。對于平民的拘留應基于國家安全的目的,并且應該嚴格地被視為是一項例外的措施(exceptional measure),非因“絕對必須(absolutely necessary)”不得加以使用[25]。在沖突的環境中,為了確保拘留不至于演變為強迫失蹤,拘留的程序應具有最基本的司法保障[25,31],包括:首先,對于被拘留的人員應予以定期復核(periodical review),該期間一般為6個月[30]。定期復核的意義在于確保被拘留的人員不再對作出拘留決定的公權力主體(detain power)構成現實的危害[31]。其次,公權力主體做出的拘留決定須和中立保護國(protecting power)進行及時溝通,并且在不影響執行的情況下將被拘留人的姓名及時告知中立保護國[32]。除此以外,拘留過程中,保護國或者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代表應具有訪問拘留地點的權利[31],在被拘留人員釋放之后,中立保護國也應當得到及時通知。除了最基本的程序保障與外界監督之外,防止拘留向強迫失蹤轉變還需要保障被拘留主體對外(exterior)溝通的權利,尤其是與家庭成員的溝通。另外,拘留方還需保障被拘留人員定期會見親友、接受訪客的權利。上述措施的核心在于保障拘留過程的客觀與中立、保障國際社會對拘留環境的可控以及促進對任意拘留受害人救濟的順利實施。但是,日內瓦公約也規定了部分例外情況。如在公民被懷疑實施了間諜行為,且該行為足以危害國家行為的情況下,公權力主體可以對被拘留公民的對外溝通進行限制[25],但該限制行為應當被信息委員會所知曉(Information Bureau)[30]且被拘留人員依舊應當免于非人道的待遇。
在戰爭及武裝沖突環境中,給予公民公平的司法程序也能夠有效地避免公民遭受強迫失蹤的侵害。依據國際慣例,被占領地原有的法律規范與程序規則在被占領之后依舊保持有效[31]。但是,占領方基于以下原因,可以自行制定法律法規,即為了更好地維持占領地區原有的政府、更好地確保被占領地區的人員和財產安全。同時,日內瓦公約還規定了若干條款來確保審判程序的公平:第一,公民有權獲知其被控告并且被毫不延遲地加以審判;第二,公民有權選擇并自由會見律師,有權陳述辯護意見并且傳喚證人;第三,審判法庭必須構成合理、去政治化、去軍事 化[31];第四,公民被判處的刑罰應當與其罪行成比例,且公民的上訴權利應當被充分保障;第五,被控告或者判刑的公民有權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會見。第六,當沖突結束之后,被拘留人員應當被移交至被解放領土(liberated territory)的公權力機構[31]。
可以說,對于平民的逮捕、拘留等強制措施并不為國際人道法所禁止,但上述條款為沖突中的相關行為提供了判別合法與非法的標準,可以有效約束對于平民的任意逮捕與拘留,有效防止非人道待遇的發生,有效抑制拘留的非公開化。同時,在平民遭遇強迫失蹤罪行的情況下,日內瓦公約的相關規定也為受害者提供了若干基本的救濟途徑。
2. 戰時針對戰俘的保障措施
在戰時,對交戰方個人的拘留是必要且為國際人道法所允許的,并且此類行為也并不被視為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必要的戰爭手段,一種削弱對方實力、獲取信息的手段[33,34]。雖然國際人道法明確,對交戰方的控告和懲罰只能基于其戰爭罪行,而非其參加戰爭及武裝沖突的行為[34]。但不可否認,在沖突中,由于人身權以及家庭權方面所遭受的限制,加之如上所述的復雜主觀因素與客觀環境,戰俘面臨著較高的強迫失蹤風險,對于戰俘的合法關押往往也極易轉化為非法的強迫失蹤。所以,對于涉及戰俘權益的相關規范以及適用于戰俘的拘留程序,國際人道法也有著特別且細致的規定。
對于戰俘的拘留。日內瓦公約規定,拘留機關有義務設立專門的信息委員會以收集在押戰俘的信息,同時負責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中心信息機構(central Information Agency)聯絡,在收到信息之后,中心信息機構又會將戰俘信息轉交給戰俘所屬國家。拘留作為最容易引發強迫失蹤行為的戰時懲戒措施(disciplinary measure),在戰時面臨著來自人道法規制的諸多約束。拘留受到的最為基本的約束在于場所層面,拘留不得在監獄機構(penitentiary institution)執行。另外,在拘留過程中,根據國際人道法的相關規定,戰俘享有如下權利:①有權向拘留機關提出與改善其拘留條件相關的請求(request);②有權請求與家庭成員進行通信、聯系;③在戰俘嚴重受傷或者疾病的情況下,有權請求被送回其國籍國進行救治;④如果戰俘在關押過程中死亡了,那么拘留方有義務制定死亡證書交由拘留委員會,證書上應記載死亡的日期、地點、死亡原因。對于死亡的戰俘,拘留方還必須保其獲得光榮的(honorable)、獨立的以及符合死亡戰俘宗教習俗的安葬。對于上述權利與義務,雖然日內瓦第三公約明確視其為基本且必要的,但經由必要程序與補償(rendered)可以適當地予以克減,唯獨戰俘的對外通信權是絕對的。
3. 戰時對于家庭生活權的保障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對于家庭生活權(right to family life)的保障也被認為是防止戰時強迫失蹤的有效方式之一[1]。家庭生活權是得到了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共同承認的基礎性個人權利,在戰爭及武裝沖突環境中,對于家庭生活權的尊重也被認為是國際人道習慣法所蘊含的一項一般性原則[27]。目前,總結國際人道法的相關規定,各個交戰主體需要保障公民戰時兩方面的權利:包括保障家庭成員享有獲知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ruth)以及保障家庭成員享有重聚(family reunification)的權利。上述權利也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明確認定為強迫失蹤罪行所違反的基本人權之一[35]。
日內瓦公約第一議定書是第一個賦予“獲知真相權”以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性公約[1]。在其看來,鑒于家庭生活權的重要性,所有的締約國在戰時都有義務保障家庭成員對于真相的獲得,都有義務采取一切盡可能的措施來對因沖突而失蹤人員進行解釋(account for)[1]。同時,根據國際人道習慣法的規定,交戰方在戰時還有義務采取可行的(feasible)措施來對被報失蹤的人員進行記載[1],記載的事項除了失蹤人員的姓名、國籍、生日等這些基礎信息外,還應當包括失蹤人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剝奪其自由權的行為人。根據日內瓦第一議定書的相關規定,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上述締約國義務應當被不加延遲地履行,最遲不得晚于敵對行為終結之后。
除了上述權利,日內瓦第四公約還要求締約國在戰時要賦予個人與家庭重聚的權利,這其中的個人既包括戰俘,亦包括平民[28]。但日內瓦公約中的“重聚”并不代表著傳統意義上人與人的直接會面,對于身處交戰領土之內的平民,“重聚”主要是指其能夠向家庭成員傳達自身的信息,同時也能夠從家庭成員處接收信息;對于被剝奪自由權的戰俘而言,“重聚”是指其有與家庭進行通信的權利。如果由于戰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個人無法獲得上述權利的話,那么締約國應當以最佳的方式來免除(discharge)自己的義務,如經由紅十字會的幫助。除此以外,日內瓦公約還要求各締約國在交戰的過程中建立信息中心,以記載其手中的戰俘與平民的個人信息。可以說,上述各個措施的核心在于保障家庭成員信息傳遞的暢通,防止秘密非公開的拘留的出現,因此,對于強迫失蹤的預防毫無疑問地具有直接的作用。
4. 最低限度的保障:日內瓦公約第一議定書第 75條
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的上述規定無疑可以有效地抑制戰時強迫失蹤行為的產生,保障被拘留平民與戰俘的最基本權益。但實際的情況卻不盡如人意,大規模的強迫失蹤依舊屢見不鮮。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可以歸于四點:首先是戰爭及武裝沖突中部分交戰方對于人道法認識的缺失,缺乏規范武裝行為的意識;其次,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一系列程序,如報告制度、信息委員會制度等,受限于戰時的現實環境,不具備較高的可執行性,同時由于部分相關概念,如“嚴重受傷”“疾病”“懲罰”等模糊概念,使得人道法相關規定在執行中缺乏可量化的具體標準;再次,由于日內瓦公約及其議定書并不具有強制執行力,加之戰時國家行為主體的確定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故而對相關規范的可訴性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最后,不可否認,國際人道法目前為止只對戰時的平民與戰俘的相關權益進行了規定與保障,但實際上,在沖突中受到強迫失蹤的并非只限于平民與戰俘,還可能包括外國記者、非政府組織人員等,對于他們的保護在人道法中依舊難覓蹤跡。
正是考慮到上述情況的存在,日內瓦第一議定書第75條規定了在戰時對于所有被拘留主體的最低保障措施,這些措施可以視為是對日內瓦公約的總結與提煉,針對強迫失蹤行為也能夠起到有效的預防效果。這些措施包括:第一,對于因戰爭或武裝沖突而被關押的人員,應當及時(promptly)以其所能夠理解的語言告知被拘留的原因;第二,在拘留結束后應當及時釋放在押人員;第三,被拘留人員享有最為基本的公平審判的權利(minimal fair trail guarantees)。
五、結語
如上所述,強迫失蹤行為與戰爭及武裝沖突的結合在現今愈發成為常態,而面對復雜的戰時環境與交戰主體,現有的專門性人權法規制在適用范圍與效果上都面臨著一定的局限與困境。因此,預期有效地約束戰時強迫失蹤行為的發生,及時救濟戰爭與武裝沖突中的相關受害人,國際人道法規制的作用應當被最大限度地發掘。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國際人道法淵源之中并沒有可以直接規制強迫失蹤行為的條款。不過,這并不代表強迫失蹤就處于國際人道法的空白之中。實際上,如果有的放矢地針對強迫失蹤的三大構成要素入手,以保障受害人自由權與家庭權為目的,從程序上保障拘留過程的透明、從制度上明確被拘留者的權益與各交戰方的義務,那么便可以從根源上有效地約束強迫失蹤行為的發生。
注釋:
① “禿鷹計劃”簽訂于1975年11月28日,于1976年1月30日生效,除了最初的5個訂立國以外,其后又有秘魯和厄瓜多爾加入。“禿鷹計劃”的實質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情報共享系統,其目的在于政治肅清、排除異己以及傳播恐懼。
② 圖1、圖2數據均來自:2014年8月4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強迫或非自愿失蹤問題工作組的報告》,A/HRC/27/49。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阿爾及利亞(1992-1999年)、埃塞俄比亞(1989-1995年)、印度尼西亞(1997-2001年)、伊拉克(1987-1989年)、黎巴嫩(1981-1984年)、尼泊爾(1996-2006年)、巴基斯坦(1994-1999年)、斯里蘭卡(1988-1991年)、蘇丹(1994-1997年)、東帝汶(1989-1995年)、也門(1983-1994年)。
③ 一般情況下,“tactic”會被翻譯為“策略”,但在國際人道法中,“策略”更多對應的是“ruse”,且“ruse”是為人道法所允許的,所以為了強調強迫失蹤的非法性,故將“tactic”翻譯為“手段”。
④ 如敘利亞國內,政府與反政府武裝都聲稱自身代表國家且對方組織為違憲的非法組織。
⑤ 如敘利亞與緬甸,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與緬甸眾多地方武裝都聲稱獨立于中央政府,且在自身的勢力范圍內實際上行使著中央政府的公權力。
⑥ 《國家國際不法行為草案》(), UN Doc. A/56/10,已經于2001年8月9日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所通過(adopted)。雖然上述文件屬于草案,但其代表了國際習慣法的觀點。
⑦ 在國際人道法中,策略(ruse)是為戰爭所允許的合法行為,意指交戰一方用行為誘使對方做出錯誤的行為或者魯莽行事(act reckless)。該誘使行為一般是指:偽裝(camouflage)、誘騙(decoy)、模擬行動(mock operation)以及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但強迫失蹤是公認的危害人類的罪行,因而無法被當做策略來加以使用,只能被視為是一種作戰手段。
⑧ 在部分情況下,受限于戰爭環境或者由于戰俘拒絕公開自身信息,行為人無法通知戰俘家人或者朋友。需要強調的是,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和《美洲強迫失蹤人員公約》都確定強迫失蹤行為成立的必要要素之一是“隱瞞被失蹤人員下落”,但隱瞞不僅僅指主動的、作為的隱瞞,被動的不作為亦可以構成隱瞞。根據《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規定,除了犯有間諜罪等危害國家及公共安全的罪行,在戰俘被關押之后應及時告知其家人,對于受限于客觀原因不能告知的,應將關押戰俘信息通知中立第三國或者國際紅十字會。因此,基于上述規定,僅以受限于客觀原因不向戰俘家人、中立第三國或者國際紅十字會公開在押戰俘信息的,或者在客觀限制原因消除之后沒有及時公開的,構成了“隱瞞被失蹤人員下落”。
⑨ 包括日內瓦公約總則第3(1)(d)條,日內瓦第三公約第21條及118條以及日內瓦第四公約第42和78條。
⑩ 包括日內瓦第一議定書第75(3)條與第二議定書第4~6條。
[1] Finucane B. Enforce disappearance as a crim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neglected origin in the Laws of War[J]. Yale J. Int'l L., 2010, (35): 171?197.
[2] Criminality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M].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22.
[3]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M]. Geneva: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Print, 1949: 73.
[4] Anderson K. How effective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likely to be in holding individuals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act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J]. Melb. J. Int'l L., 2006, (7): 245?278.
[5] Capdepón U. Surviving forced disappearance in argentina and uruguay: Identity and meaning by gabriel gatti[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017, 39(2): 478?480.
[6] Vermeulen M L. Enforced disappearance: Determining stat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M]. Utrecht: Intersentia Press, 2012: 18, 74, 84.
[7]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強迫或非自愿失蹤問題工作組的報告[EB/OL].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 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Pages/ListReports.aspx.A/HR C/27/49.doc, 2014?08?04.
[8] Berman M R, Clark R S. State terrorism: Disappearances[J]. Rutgers LJ, 1981, (13): 531?577.
[9] Dieterich H.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corruption in Latín America[J].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1986,(25): 40?54.
[10] 趙洲. 強迫失蹤與國家的人權保護責任[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 18(2): 68?73.
[11] 何志鵬, 戴珊珊. 強迫失蹤的國際法治理[J]. 東方法學, 2010, (4): 23?34.
[12] Brody R, Gonzalez M. Nunca Más: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on “disappearances”[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97, 19(2): 365?405.
[13] 張愛寧. 論強迫失蹤罪——兼評《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J]. 環球法律評論, 2009, 31(2): 143?151.
[14]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Human rights council opens special session on human rights in syrian arab republic[EB/OL].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DisplayNews. pdf. 2017?05?01/2017?05?03.
[15] United Nations Humn Rights Council. Oral update of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EB/OL].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 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9/Pages/ListReports.aspx. A/HR C/29/CRP.3.doc, 2015?06?23.
[16] Caron D D. The ILC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author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41): 857?873.
[17] K?lin W, Künzli J.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8.
[18] 李良勇. 敘利亞反對派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N].中國青年報, 2013?10?4(04).
[19] Clifft W. Columbia, democracy, and the intermingling thereof[J]. Pursuit-The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2016, 7(1): 8.
[20] Scovazzi T, Citroni G. The struggle against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the 200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M].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22.
[21]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Without a trac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syria[EB/OL]. http://www.ohchr. org/ EN/ 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5/Pages/List Reports.aspxannexe.A/HRC/25/65.doc, 2014?02?12.
[22] Chevalier Watts J. The phenomena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urkey and chechnya: Strasbourg’s noble cause?[J]. Human Rights Review, 2010,11(11): 469?489.
[23] Jeffery R. Nepal’s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human rights, compliance and impunity a decade on[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93(2): 343?364.
[24] Mallinder L. The end of amnesty or regional overreach? Interpreting the erosion of South America’s amnesty laws[J].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16, 65(3): 645?680.
[25] Gasser H-P, D?rmann K.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C]// Dieter Fleck. The Handbook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7?274.
[26] Nader L. Anthropology of law, fear, and the War on Terror[J]. Anthropology Today, 2017, 33(1): 26?28.
[27] Henckaerts J M, Doswald-Beck L, Alvermann 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3.
[28] Nowak M. UN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 commentary (First Edition)[M]. Strasbourg: Publisher Kehl, 1993: 927.
[29] 讓.皮克泰. 國際人道法的原則[J]. 王海平譯. 紅十字國際評論, 2004(1): 1?10.
[30] Ronald Griffin, C W Dumbleton.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pictet[C]// Pictet J S.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Commentary.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1958: 78?84.
[31] Gasser H P. Das humanit?re V?lkerrecht[M]. Geneva: Institut Henry Dunant/ Paul Haupt Print, 1991: 66?70.
[32] Wolfrum R, Fleck 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C]//Dieter Fleck. The Handbook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7.
[33] Fisher E C. Laws of arrest[M].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7: 91, 93.
[34] Kalshoven F, Zegveld L. Constraints on the waging of war: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8.
[35]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Addendum [EB/OL].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 / HRC / Regular Sessions/Session30/Pages/ListReports.aspx.A/HRC/30/38/Add. 5.doc, 2015?07?09.
[編輯: 蘇慧]
Regulation consideration over enforced disappearance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t war times
SHAO Yi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270, China;Norweg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Oslo, Oslo 0864, Norway)
In view of its wide use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nce World War II,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as been regarded earlier as a "national repressive policy" serving the dictatorship, with its essence being extensive and systematic aggression in human rights, and therefore most academics prefer to study it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Law. However since the 1990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as been in combined use with war and armed conflicts in an increasingly close and normalized mainstream way, employed more and more as a tactics of warfare by both sides. In spite of the lack of direct regulation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nd related relief for the victim, it is still essential to curb the occurrence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so as to ensure obtaining basic human rights at war times to the maximum by regulating the procedure of detention of both civilians and war prisoners and by ensuring individual rights of family life at war and just jurisdicti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Geneva Convention; State Act; family rights
D995
A
1672-3104(2017)05?0067?09
2017?02?23;
2017?06?05
教育部留學基金委資助項目“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201604920035)
邵懌(1990?),男,江蘇靖江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與挪威奧斯陸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挪威奧斯陸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