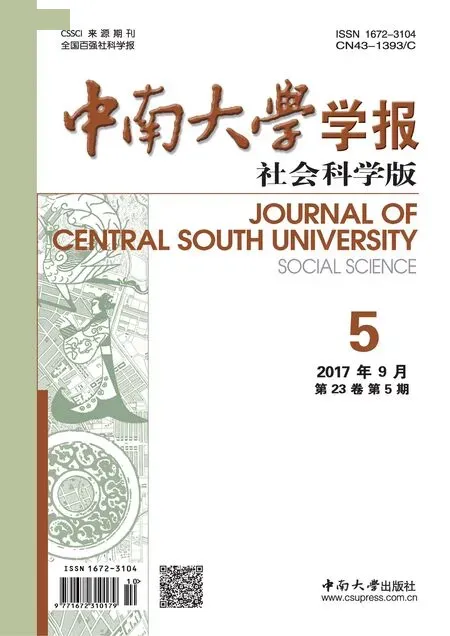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一個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模型
顏愛民,趙浩,趙德嶺,林蘭
?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一個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效應(yīng)模型
顏愛民,趙浩,趙德嶺,林蘭
(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湖南長沙,410083)
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一般將員工打破組織正式規(guī)則視為員工出于憤怒、自私自利或不認可組織文化而表現(xiàn)出來的偏差行為進行研究。基于不確定性管理理論和社會交換理論,從員工心理感知的視角來研究員工的親社會性規(guī)則違背行為,探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這種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作用機制。通過對30家企業(yè)的399名員工進行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親社會違規(guī)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不僅正向調(diào)節(jié)了心理安全感與親社會違規(guī)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還正向調(diào)節(jié)了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心理安全感;自我效能感
一、引言
Tyler和Blader[1]指出,在組織日常管理過程中,規(guī)則和政策是為了確保員工進行組織所期望的行為而存在的,它可以促進員工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性,因而當這些規(guī)則或政策被遵守時,組織即會獲益;相反,當員工違背了規(guī)則和政策,也就是做出了組織明令禁止的偏差行為,組織即會受損。近年來,針對員工的規(guī)則違背行為成為組織行為研究的熱點,出現(xiàn)了諸如“組織不當行為(organizational misbehavior)”、“工作場所偏差(workplace deviance)”以及“員工惡習(xí)(employee vice)”等概念[2?4],這些研究旨在探索規(guī)則違背的破壞性本質(zhì),發(fā)現(xiàn)員工做出此類行為的動機主要是源于對組織的不滿、低組織承諾、感受到的不公或趁機竊取組織利益[2]。代理理論認為,只要符合員工自身的利益并且沒有足夠的組織控制以確保其服從規(guī)則,員工就會傾向于打破組織規(guī)則[5],即規(guī)則違背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式,且常常被認定為一種自私和推卸責任的偏差行為。然而,員工做出規(guī)則違背的偏差行為一定會造成不良后果嗎?或者說此類行為背后的動機一定是消極的嗎?Spreitzer等[6]認為,現(xiàn)有關(guān)于員工偏差行為的研究忽視了機構(gòu)及其附屬公司員工如何表現(xiàn)出的一系列積極行為,而僅僅是關(guān)注其產(chǎn)生的消極方面,因此,他們開始從正面視角來研究工作場所中的偏差行為,提出了積極性偏差概念,Morrison[7]在此基礎(chǔ)上明確界定了“親社會性違規(guī)”(pro-social rule breaking,簡稱PSRB)概念,特指員工的那些“幫助組織或其利益相關(guān)者實現(xiàn)其目標”的規(guī)則違背行為。Vardaman等[8]認為PSRB行為的親社會屬性決定了員工做出的此類行為往往是對組織、同事或者顧客有利的,但對于他們自身幾乎沒有什么利益可言,甚至可能損害自身利益,如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和晉升機會等,這種利他卻不期望獲得報酬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理應(yīng)得到領(lǐng)導(dǎo)者和同事們的支持。此外,現(xiàn)有研究也實證了PSRB行為能為組織帶來諸多好處,例如,Galperin[9]研究發(fā)現(xiàn),如果員工一味地遵守死板的企業(yè)規(guī)范、程序和政策會不利于組織績效和財務(wù)狀況,而員工做出的非墨守成規(guī)行為能夠加速組織創(chuàng)新、促進組織變革和提升組織競爭力,防止組織的各項規(guī)則和制度處于“固化”狀態(tài)。可見,員工做出PSRB行為是源于積極的利他性意愿,并且可以為組織帶來諸多創(chuàng)新性成果,這完全不同于工作場所偏差、反社會行為等自利性驅(qū)動的消極偏差行為。
在日常管理實踐中,組織制定的規(guī)則和制度等通常需要領(lǐng)導(dǎo)者來貫徹執(zhí)行。對于員工而言,領(lǐng)導(dǎo)者已然成為了組織的象征和代理人,正因如此,他們的領(lǐng)導(dǎo)風格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員工的PSRB行為。此外,隨著知識經(jīng)濟時代的到來和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組織外部環(huán)境日趨復(fù)雜,市場化競爭日趨激烈,領(lǐng)導(dǎo)者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很難僅憑自身力量應(yīng)對高度復(fù)雜動態(tài)環(huán)境帶來的挑戰(zhàn),因此,各類組織紛紛采用授權(quán)型團隊替代傳統(tǒng)的層級管理結(jié)構(gòu),以提高組織的靈活性與效率[10],這種情境下,被授權(quán)的員工能夠充分利用授權(quán)信息,更加自主地表現(xiàn)出PSRB行為。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員工個體行為是由個體動機激發(fā)而表現(xiàn)出來的,領(lǐng)導(dǎo)實施的授權(quán)行為未必能夠直接影響員工行為,多數(shù)情況下是直接作用于員工心理感知層面[11],進而對員工的PSRB行為產(chǎn)生影響。與建言行為、創(chuàng)新行為等冒險性行為一樣,員工做出PSRB行為也會面臨風險,可能會受到來自上司和同事的負面評 價[12]。因此,本文引入心理安全感知作為中介變量,來衡量員工愿意做出風險性行為的程度。此外,除了組織情境因素,員工的PSRB行為也會受到個體特質(zhì)和核心自我評價等個體層面因素的影響[7,12],本文引入自我效能感作為調(diào)節(jié),以探究其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心理安全感知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關(guān)系之間產(chǎn)生的 影響。
二、理論綜述與研究假設(shè)
(一)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
關(guān)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學(xué)界有著不同的研究視角。一種是情景視角,即“情景授權(quán)”(situational empowerment),該視角強調(diào)從組織情境(工作設(shè)計、領(lǐng)導(dǎo)行為等)出發(fā),并將其定義為組織中一系列下放決策權(quán)的管理實踐措施,如下放職權(quán)、組建自主工作小組和自我管理團隊以及工作豐富化等[13];另一種則從心理視角出發(fā),即“心理授權(quán)”(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相比情景授權(quán),它更多地關(guān)注員工的內(nèi)在心理感受[14],如心理授權(quán)、心理安全感知等。后來,有學(xué)者將兩種視角相結(jié)合,演變出“整合視角”,如Zhang和Bartol[15]將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界定為通過闡明工作意義、允許較大自主性、對員工能力表示信心、排除績效障礙等方式實現(xiàn)同員工共享權(quán)利的過程。
Dahling[12]在Morrison研究基礎(chǔ)上運用情景實驗法進一步對員工的PSRB行為展開研究,并開發(fā)出一套測量PSRB行為的工具。總結(jié)Morrison和Dahling等學(xué)者的研究,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中的“規(guī)則”是指組織明確規(guī)定的、期望組織成員遵照執(zhí)行的政策、規(guī)章和禁令,具有合法性和強制性,但不一定被組織所有成員所認可,這也是其不同于“規(guī)范”(即群體成員所公認的有關(guān)他們應(yīng)當如何行事的期望或標準,具有自發(fā)性和非強制性特點)之處;第二,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具有親社會屬性,它不是員工自私自利的表現(xiàn),更多地關(guān)注組織利他性收益,即PSRB行為反映的是員工渴望“做好事”的動機;第三,組織成員做出PSRB行為是一種有意識的自愿行為,不包括無意或偶然打破組織規(guī)則的行為,因此具有更高自主性的員工更傾向于做出這種行為;第四,PSRB行為是一種典型的風險性行為,做出此類行為的員工很有可能會受到領(lǐng)導(dǎo)或同事的排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推斷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對PSRB行為產(chǎn)生影響:首先,根據(jù)不確定性管理理論[16],員工在工作情境中需要應(yīng)對人際交往中的多方面不確定性和人際風險,不確定性的體驗影響著個體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甚至?xí)拗频絺€體的自我意識。而領(lǐng)導(dǎo)表現(xiàn)出的下放職權(quán)、以身作則、信息分享、關(guān)懷[10]等一系列授權(quán)行為有利于營造一個清晰、透明、公平和包容的工作氛圍,有利于降低員工工作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員工自我意識和安全感知,降低員工工作壓力和對風險性行為的負面預(yù)估,從而更有可能主動地做出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其次,組織中的規(guī)則是由上級制定并監(jiān)督執(zhí)行的,對于員工而言,違反規(guī)則就意味著會冒犯領(lǐng)導(dǎo)者權(quán)威,而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并不是主要通過權(quán)力或權(quán)威來命令或指導(dǎo)他人,而是通過領(lǐng)導(dǎo)自身行為發(fā)展下屬的自我影響能力,使得下屬具備自我控制、自我調(diào)節(jié)、自我管理和自我領(lǐng)導(dǎo)能力[17],這會弱化組織管理層對員工遵循規(guī)則和程序的要求程度,有助于員工積極做出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再次,領(lǐng)導(dǎo)者通過與下屬分享權(quán)力、提供更多工作自主權(quán)、向他們闡明工作意義等[18],一方面有助于消除員工的無權(quán)利感知、增強員工工作的自主性,使員工更加自主地實施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7];另一方面還會提升員工內(nèi)在激勵水平、增強內(nèi)在動機,并顯著提高工作積極性,從而增強其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能力以及實施挑戰(zhàn)性角色外行為的意愿[15],實質(zhì)上也會增加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傾向。最后,授權(quán)允許員工參與決策,幫助他們擺脫停滯的心態(tài),進而冒險去嘗試新的東西,即以對組織有利的方式采取積極偏離組織規(guī)范的行為[19]。此外,根據(jù)社會交換理論,當領(lǐng)導(dǎo)者表現(xiàn)出闡明工作意義、下放職權(quán)、以身作則、鼓勵員工參與決策等行為時,員工基于對領(lǐng)導(dǎo)和組織回報的內(nèi)在動機需求,當遇到有利于組織或群體利益但又不符合組織既有規(guī)則要求時,員工會有更強的冒著個人風險、突破組織規(guī)則做出有利于組織利益的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動機。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二)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安全感反映的是個體在所處的工作環(huán)境中愿意冒人際風險的程度,是個體對周圍人際關(guān)系的一種感知[20],即當員工在表現(xiàn)和展示真我時,不必擔心這類行為會影響到其在組織中的形象或者發(fā)展的心理感知。已有研究表明,當員工感知到較強的心理安全時,會降低對工作環(huán)境不確定性的判斷,傾向于認為他人對自己冒風險的行為持寬容態(tài)度,從而更深地工作卷入并從事風險性行為[21]。國內(nèi)外諸多學(xué)者也證實了這一點:具有較高心理安全感知的員工更樂意給領(lǐng)導(dǎo)建言[22]、更傾向于與同事共享知識[23]、表現(xiàn)出更高的創(chuàng)造力[24],而建言、知識共享以及創(chuàng)新行為都伴隨著較大的風險。
Dahling[12]研究發(fā)現(xiàn),員工的PSRB行為與上司和同事對其任務(wù)績效評價均顯著負相關(guān),說明組織上下對這種行為的反應(yīng)是比較消極的,盡管該行為人的目的是幫助組織及其利益相關(guān)者,但似乎上司和同事并不“領(lǐng)情”,這使得PSRB行為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根據(jù)期望理論,員工在作出決策之前首先考慮風險與收益之比,并預(yù)期該行為有可能帶來的有利或不利結(jié)果,據(jù)此作出行為決策。換言之,只有當員工感受到強烈的心理安全時,才會認為上司和同事對他做出PSRB行為持寬容態(tài)度,也不會因為受到負面評價而影響自身的人際關(guān)系和晉升機會,因此員工會毫無顧忌地表現(xiàn)出PSRB行為;反之,當員工心理安全感知較弱時,便會過度擔心PSRB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認為風險遠遠大于收益,進而選擇規(guī)避PSRB行為。此外,李銳[25]通過問卷調(diào)查和情景實驗相結(jié)合的方法驗證了員工的心理安全感與PSRB行為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 心理安全感知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作為一種對風險程度的感知,心理安全感會受到組織中的多種因素,如人和制度等不同程度的影響[20],鑒于領(lǐng)導(dǎo)者在組織中的地位與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他們無疑會在員工心理安全感的形成和演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Walumbwa 和 Schaubroeck[22]通過對美國金融機構(gòu)中894名員工與222位直接上司的配對數(shù)據(jù)研究發(fā)現(xiàn),上司的道德型領(lǐng)導(dǎo)行為通過下屬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員工的建言行為。王永躍[24]基于認知評價理論,針對浙江的25家企業(yè),以配對的 328 組員工為樣本進行研究得出,倫理型領(lǐng)導(dǎo)對心理安全感顯著正相關(guān),心理安全感中介了倫理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創(chuàng)造力的關(guān)系。可見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nèi)情境下,學(xué)者們都已經(jīng)實證了領(lǐng)導(dǎo)風格對員工心理安全感有重要影響,而心理安全感又常常在領(lǐng)導(dǎo)風格與員工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Edmondson和Chen G等研究發(fā)現(xiàn),領(lǐng)導(dǎo)的授權(quán)行為先作用于員工心理感知層面,進而對員工的行為產(chǎn)生影響。根據(jù)不確定性管理理論,領(lǐng)導(dǎo)可以通過下放職權(quán)、促進參與決策、信息分享、關(guān)懷員工等授權(quán)行為,營造一個清晰透明、可預(yù)測的工作環(huán)境,這有利于降低員工的個人不確定性感和信息不確定感,進而促進個體心理安全感的形成。林曉敏等[26]以團隊為單位研究發(fā)現(xiàn),領(lǐng)導(dǎo)實施授權(quán)行為后,團隊氛圍更加開放包容,團隊成員之間地位更加平等,溝通更為順暢,對彼此也更加信任,從而有更加強烈的心理安全感知。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3 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 自我效能感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在特定環(huán)境下對自己完成特定任務(wù)的能力評估和信心,也是對自我價值的一種認知,它能夠有效調(diào)節(jié)人們對行為的選擇、投入努力的大 小[27]。當個體具備較高的自我價值認知時,會有著更強烈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信心,更不愿意被現(xiàn)有規(guī)則所約束。Luthans F[28]研究發(fā)現(xiàn),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傾向于更多地關(guān)注值得追求的機會,會以更加積極的心態(tài)審視組織的劣質(zhì)性因素,而較少關(guān)注需要回避的風險,并表現(xiàn)出積極的組織行為。實證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夠正向預(yù)測負責行為、創(chuàng)造性行為和積極性偏差行為[29]。Vardaman[8]綜合有關(guān)PSRB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構(gòu)建了一個親社會性違規(guī)影響因素模型,并推測核心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自尊等)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存在顯著正向關(guān)系。Schwarzer等[30]認為,自我效能感并不會使個體在面對風險時盲目樂觀,而是在自己能力范圍內(nèi)采取一定冒風險的行為,即在員工做出PSRB行為之前,不僅要評估當前工作環(huán)境的安全性,而且會考慮到自身能力的大小,只有當兩者相互協(xié)調(diào)才有利于PSRB行為的發(fā)生[20]。因此,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會認為PSRB行為給組織及其利益相關(guān)者帶來的福祉遠大于PSRB行為給自己帶來的風險和損失。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4 自我效能感正向調(diào)節(jié)心理安全感知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即自我效能感越高,員工心理安全感知對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越大。
綜合假設(shè)1?4的推導(dǎo)過程,本研究認為,自我效能感不僅調(diào)節(jié)員工心理安全感知與PSRB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還調(diào)節(jié)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影響員工PSRB行為的間接機制。原因如下,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對工作的自信水平較高,對不確定性環(huán)境及風險性行為的控制具有信心[31],因此,當領(lǐng)導(dǎo)者表現(xiàn)出下放職權(quán)、允許員工參與決策、信息分享、對員工能力表示信心等一系列授權(quán)行為后,員工會認為自己有能力充分利用這些授權(quán)信息,與此同時,一系列授權(quán)行為降低了員工工作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有利于員工心理安全感的生成,進而促進員工更加自覺地做出PSRB行為來回報組織及其利益相關(guān)者。相反,當員工的自我效能感較低時,他們對領(lǐng)導(dǎo)的授權(quán)信息反應(yīng)不夠敏感,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很難激發(fā)員工做出PSRB行為來回報組織,員工即使感知到了心理安全,也會因為對自身能力的不夠認可而規(guī)避具有風險的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5 自我效能感正向調(diào)節(jié)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即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通過員工心理安全感知影響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在自我效能感高的條件下會更強。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樣本與數(shù)據(jù)
本研究的調(diào)查對象選自廣州、長沙、鄭州三個地方的30家企業(yè),在每家企業(yè)隨機選取15~20名基層員工發(fā)放調(diào)查問卷,主要涉及制造業(yè)、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服務(wù)業(yè)等行業(yè)。共發(fā)放調(diào)查問卷565份,回收457份,問卷回收率為80.9%。按照本研究樣本要求,嚴格控制問卷有效性,剔除無效問卷后剩余399份,問卷回收有效率為87.3%。其中,性別方面,男性占58.4%、女性占41.6%;年齡方面,30歲及以下占12.9%、30~40歲占43.8%、40~50歲占30.6%、50歲及以上占12.7%;學(xué)歷方面,初中及以下占1.0%、高中及中專占10.5%、大專占22.8%、本科占58.4%、碩士及以上占7.3%;工作年限方面,3年及以下占19.8%、3~5年占38.3%、5~10年占31.1%、10年及以上占10.9%;行業(yè)性質(zhì)方面,制造業(yè)占23.6%、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占32.8%、服務(wù)業(yè)占26.3%、其他行業(yè)占17.3%。
(二) 變量測量
本研究為確保測量工具的信效度,四個變量均采用國內(nèi)外運用較為成熟的量表。因員工是組織管理實踐的對象,且處于感知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從而產(chǎn)生相應(yīng)態(tài)度和行為的最佳位置,因此本研究均采用員工的主觀測量方法,四個變量的測量量表均采用Likert 5點法測度,1~5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1)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該變量的測量采用Ahearne等[32]開發(fā)的量表,由員工對上級的領(lǐng)導(dǎo)行為進行評價,共有4個維度、12個題項,且4個維度的Cronbach's系數(shù)分別為076、0.92、0.90、0.86,典型題項如“我的主管會幫助我理解我的個人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該量表的總體Cronbach's值為0.92。
(2)心理安全感知。該變量的測量采用Edmondson[20]開發(fā)的量表,共7個題項,如“團隊成員中如果有人犯錯,不會受到其他人的反對”。該量表的Cronbach's值為0.80。
(3)自我效能感。該變量的測量采用Schwarzer和張建新等[30]開發(fā)的量表,共10個題項,如“如果我盡力的話,總是能夠解決問題的”。該量表的Cronbach's值為0.87。
(4)親社會性規(guī)則違背。該變量的測量采用Dahling等[12]開發(fā)的量表,該量表含有“改進效率”、“幫助同事”和“改善顧客服務(wù)”三個分量表,由于第三個分量表不具有跨崗位的普適性(本研究的樣本包含制造業(y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等非服務(wù)行業(yè)的員工,他們一般不會直接面對顧客并提供服務(wù)),因此本研究只采用了前兩個分量表,包含9個題項,如“為了幫助公司節(jié)省時間和金錢,我會違背組織策略”(改進效率);“雖然有時會違反組織規(guī)則,但我還是樂意去幫助同事”(幫助同事),兩個分量表的Cronbach's值分別為0.94和0.92。
(5)控制變量。相關(guān)研究表明,人口統(tǒng)計學(xué)變量能夠影響員工感知的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心理安全感、自我效能感和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因此,本研究對以下人口統(tǒng)計學(xué)變量進行控制:①性別:分為男、女;②年齡:30歲以下、30~40歲、40~50歲、50歲及以上;③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及以上;④本崗位工作年限:3年及以下、3~5年、5~10年、10年及以上。
四、研究結(jié)果
(一) 信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采用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來檢驗各量表的信度,運用SPSS19.0統(tǒng)計分析軟件對調(diào)研數(shù)據(jù)進行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測量。有關(guān)結(jié)果顯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心理安全感知、自我效能感和親社會性違規(guī)的Cronbach's值分別為0.891、0.764、0.855和0.869,均達到了“超過臨界值0.7”的要求。
其次,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判斷研究所采集數(shù)據(jù)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將四個變量的所有條目都放入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所有條目旋轉(zhuǎn)為7個因子,且第一個因子的累計方差解釋率為33.38%,因此,本研究采集的399份問卷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jié)果影響較小。
最后,本研究采用AMOS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來檢驗各量表的區(qū)分效度,選取2/、CFI、ILI、RMR和RMSEA共5個指標來說明模型的擬合情況,結(jié)果顯示,4因子嵌套模型具有很好的擬合效度(2/=2.063 ,CFI=0.967,ILI=0.924,RMR=0.072,RMSEA=0.054),而且擬合情況明顯好于3因子、2因子和1因子嵌套模型。因此,本文構(gòu)建的4因子模型能夠更好地代表測量的因子結(jié)構(gòu),變量的區(qū)分效度得到驗證,變量間關(guān)系的分析可以進行。
(二) 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
本研究所測量的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見表1,其中,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心理安全感、自我效能感、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4個變量量尺分數(shù)均介于1~5之間,平均數(shù)分別為3.57、3.49、3.62和3.36。
從表1中可以看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心理安全感顯著正相關(guān)(=0.697,< 0.05),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PSRB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0.544,< 0.05),心理安全感與員工PSRB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0.766,< 0.05),自我效能感與員工PSRB行為也顯著正相關(guān)(=0.556,<0.05)。由此,假設(shè)1和假設(shè)2均得到了初步支持。
(三) 假設(shè)檢驗
1. 中介效應(yīng)檢驗
本研究擬采用層級回歸來分析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按照溫忠麟等[33]提出的中介效應(yīng)分析方法,步驟如下:①檢驗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是否具有顯著影響;②檢驗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心理安全感與心理安全感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是否具有顯著影響,如果都顯著則進行步驟③,如果有至少一個不顯著則運用Bootstrap 法進行檢驗;③檢驗加入心理安全感之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直接影響是否顯著。有關(guān)回歸結(jié)果統(tǒng)計見表2。
由表2可知,將控制變量(性別、年齡、學(xué)歷和工作年限)納入模型1,模型2顯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0.610,<0.001),由此,假設(shè)1得到進一步支持,步驟①也得到驗證。模型3顯示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心理安全感知具有正向顯著影響(=0.631,<0.001),模型4顯示心理安全感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0.947,<0.001),由此,假設(shè)2也得到進一步支持,步驟②也得到驗證。對比模型2與模型5,在引入中介變量心理安全感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變得不再顯著,且心理安全感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正向影響顯著(=0.927,<0.001),由此,假設(shè)3得到支持,即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通過心理安全感影響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

表1 描述統(tǒng)計與變量相關(guān)性分析(N=399)
注:*、**分別表示<0.05、<0.01
2. 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檢驗
本研究采用調(diào)節(jié)回歸分析來檢驗自我效能感的調(diào)節(jié)作用(見表3)。在回歸之前,先對相關(guān)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在表3中,模型3顯示心理安全感與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項系數(shù)顯著(=0.175,<0.01),能夠顯著解釋57.6%的變異,這說明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安全感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起著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由此,假設(shè)4得到支持。
為進一步驗證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的作用模式,本研究參照Liu等[34]提出的二階段被調(diào)節(jié)的中介作用的層次路徑分析方法,運用M-plus7軟件對假設(shè)進行檢驗(結(jié)果見表4),由第二階段結(jié)果可知,在低自我效能感(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的條件下,心理安全感的間接效應(yīng)不顯著(=0.002,>0.1),95%的置信區(qū)間為[?0.093,0.107],包含0;在高自我效能感(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的條件下,心理安全感的間接效應(yīng)顯著(=0.108,<0.01),95%的置信區(qū)間為[0.052,0.237],不包含0。即在自我效能感高低不同的兩種情境下,心理安全感中介作用差異顯著(=0.106,<0.01)。由此,假設(shè)5得到支持。
本研究還根據(jù)Aiken[35]的方法畫出了對應(yīng)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圖(見圖2)。由圖2可知,相比于低自我效能感的條件,心理安全感知對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正向影響效果在高自我效能感條件下得到了明顯的加強。

表2 回歸結(jié)果統(tǒng)計分析(N=399)
注:*、**、***分別表示<0.05、<0.01、<0.001

表3 自我效能感的調(diào)節(jié)回歸分析(N=399)
注:*、**、***分別表示<0.05、<0.01、<0.001

表4 自我效能感的路徑分析結(jié)果
注:*、**分別表示<0.05、<0.01

圖2 自我效能感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
五、結(jié)論及意義
(一) 研究結(jié)論
(1)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的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該結(jié)論與何燕珍和張瑞[36]的實證研究結(jié)果相一致,也從側(cè)面印證了Morrison[7]的情景實驗結(jié)果,即感受到較高工作自主性或者能與上司保持較好關(guān)系的員工更容易產(chǎn)生PSRB行為。(2)心理安全感正向促進員工的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而且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作用過程中起到中介效應(yīng)。本研究驗證了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風險性屬性,只有當心理安全感緩沖了來自工作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員工才傾向于冒著人際風險去挑戰(zhàn)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25]。(3)自我效能感不僅調(diào)節(jié)了心理安全感知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關(guān)系,而且還調(diào)節(jié)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用實證數(shù)據(jù)驗證了Vardaman等[8]構(gòu)建的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關(guān)系概念模型,一般自我效能感與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往往對自己的工作能力充滿自信,也能充分理解并利用領(lǐng)導(dǎo)的授權(quán)信息,當其產(chǎn)生較強的心理安全感時,便不會輕易受組織現(xiàn)有規(guī)則的束縛,進而努力實施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來為組織及其利益相關(guān)者謀取福祉。
(二) 理論意義
(1)作為積極性偏差(建設(shè)性越軌)行為的一種,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研究是對積極組織行為學(xué)和積極性偏差研究的融合與發(fā)展,豐富了積極組織行為學(xué)理論,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和良好的研究前景,值得研究者給予更多的關(guān)注。(2)以往有關(guān)組織行為學(xué)的研究多運用社會交換理論、信息加工理論和資源保存理論等,本文引入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為組織情境變量如何通過員工心理感知影響員工行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3)本文引入心理安全感作為中介變量,第一次從風險感知的視角來考察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于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機制,有助于揭開領(lǐng)導(dǎo)行為對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影響過程和作用機制的“黑箱”。(4)現(xiàn)有關(guān)于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前因變量的研究多從兩個層面著手,一個是個體層面的員工特質(zhì),如個體冒險傾向、工作自主性、責任感、自我效能感、自尊等;另一個是員工所處的工作環(huán)境,即組織層面的“情境因素”,如領(lǐng)導(dǎo)方式、倫理氛圍、上司?下屬關(guān)系質(zhì)量等。但極少研究從個體特質(zhì)與情境因素的交互視角展開探討,本文則同時從個體層面“自我效能感”與組織層面“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PSRB行為的影響展開研究,為從交互視角研究PSRB行為奠定了基礎(chǔ)。
(三) 實踐意義
(1) 本研究實證了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PSRB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員工在組織中的規(guī)則違背行為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因為消極情緒或感知到不公選擇報復(fù)組織的消極性偏差,這種違規(guī)行為可能會影響組織生產(chǎn)效率、浪費組織資源;另一種是為了提高組織及其利益相關(guān)者福祉而做出的PSRB行為,此種行為可彌補組織制度剛性缺陷,提升組織的內(nèi)在活力,增加組織的靈活性和應(yīng)變能力,所以PSRB行為是組織所期待和應(yīng)該鼓勵的員工行為。本研究結(jié)論說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會降低組織制度剛性的負面影響,通過增加員工的PSRB行為提升組織的活力和市場應(yīng)變力,彌補組織制度設(shè)計本身的缺陷。根據(jù)組織設(shè)計有關(guān)理論,組織制度的正面和負面效應(yīng)永遠存在,如何在組織制度設(shè)計和運行中盡可能減少負面影響,是組織和員工行為研究的永恒問題。本研究揭示了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該類問題的解決,這無疑為領(lǐng)導(dǎo)方式的選擇和組織制度的設(shè)計提供了新的應(yīng)用啟示。(2)本研究揭示了員工心理安全感知在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即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通過提高員工心理安全感進而提升員工的PSRB行為。一方面說明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心理安全感具有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引發(fā)員工更多地做有利于組織的行為;另一方面說明員工的PSRB行為受到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正向影響。由此,給予各級管理者重要啟示是:在管理過程中關(guān)注員工的心理感受、增加其心理安全感就是提升員工和組織績效的有效方法。(3)基于PSRB行為特征——基于積極動機的有利于組織的違規(guī)行為,本研究帶給我們的應(yīng)用啟示是:第一,如果組織中的優(yōu)秀員工大面積地頻繁出現(xiàn)PSRB行為,一方面說明可能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方式具有明顯優(yōu)勢,值得保護和持續(xù);另一方面也說明組織的管理制度過于繁瑣和僵化,需要對制度進行完善和修正。第二,如果組織對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依賴程度高,比如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或研究機構(gòu),需要更多地保護和鼓勵員工PSRB行為,根據(jù)本研究發(fā)現(xiàn)的員工自我效能感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建議企業(yè)在招聘時盡量選用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有助于組織的發(fā)展。
六、局限與展望
首先,由于資源和調(diào)研時間有限,本研究的數(shù)據(jù)采用的是橫截面數(shù)據(jù),且數(shù)據(jù)來源均為員工。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縱向研究的方法,并從多個來源(上下級之間配對數(shù)據(jù))搜集數(shù)據(jù),一方面,可以考察領(lǐng)導(dǎo)授權(quán)后組織氛圍的演變過程,從而更好地驗證親社會性規(guī)則違背行為與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的因果關(guān)系;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規(guī)避問卷調(diào)查過程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其次,由于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親社會屬性,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影響親社會違規(guī)行為的前因變量,但關(guān)于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學(xué)界一直沒有統(tǒng)一的說法。目前只有Dahling[12]對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結(jié)果變量進行過研究,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實證或者實驗研究的方法,將PSRB行為作為前因變量,研究其對組織整體績效、創(chuàng)新績效、員工幸福感、員工自我效能或領(lǐng)導(dǎo)方式轉(zhuǎn)變等的影響。
最后,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群體在價值判斷、工作觀念和行為方式上往往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與老一代員工相比,新生代員工(特別是90后)崇尚自由、擁有更強的主動型人格和更高的自我實現(xiàn)需要,對成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且不愿被現(xiàn)有規(guī)則所束縛;此外,新生代員工還多是風險偏好者,有著很強的自我意識與成才意識。鑒于新生代員工的這些特點,當上級領(lǐng)導(dǎo)對他們充分授權(quán)后,他們是否會在更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因此,本文建議,以后的學(xué)者可以專門以新生代員工(或者90后)作為研究樣本,對其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展開研究。
[1] Tyler T R, Blader S L. Can businesses effectively regulate employee conduct? The antecedents of rule following in work setting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6): 1143?1158.
[2] Vardi Y, Weitz E. Mis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Theory, research and management[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4.
[3] Robinson S L, Bennett R J. A typology of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stud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555?572.
[4] Moberg D J. On employee vice[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1997, 7(4): 41?60.
[5] Eisenhardt K.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 (1): 57?74.
[6] Spreitzer G M, Sonenshein S. Positive deviance and extraordinary organizing[J].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 2003, CA: 207?224.
[7] Morrison E W. Doing the job well: An investigation of pro-social rule break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32(1): 5?28.
[8] Vardaman J M, Gondo M B, Allen D G. Ethical climate and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in the workplace[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4, 24(1): 108?118.
[9] Galperin B L. Exploring the nomological network of workplace deviance: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measure of constructive devi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42(12): 2988?3025.
[10] Arnold J A, Arad S, Rhoades J A, et al. The empowering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leader behavior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21(3): 249?269.
[11] Chen G, Sharma P N, Edinger S K, et al. Motivating and demotivating forces in teams: Cross-level influences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1, 96(3): 541?557.
[12] Dahling J J, Chau S L, Mayer D M, et al. Breaking rules for the right reasons? An investigation of pro-social rule breaking[J]. Jour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2, 33(1): 21?42.
[13] Leach D J, Wall T D, Jackson P R. The effect of empowerment on job knowledge: An empirical test involving operators of complex technology[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76(1): 27?52.
[14] Spreitzer G M.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 38(5): 1442?1465.
[15] Zhang X, Bartol K M. Linking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J].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2010, 53(5): 107?128.
[16] Lind E A, Van den Bos K. When fairness work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uncertainty management[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4(2): 181?223.
[17] 易健, 關(guān)浩光, 楊自偉.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家庭生活質(zhì)量的影響[J]. 外國經(jīng)濟與管理, 2014, 39(9): 52?60, 80.
[18] Ahearne M, Mathieu J, Rapp A. 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 your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behavior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5): 945?955.
[19] Spreitzer G M, Doneson D. Musing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employee empowerment[J].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2005(17): 311?324.
[20] Edmondson A C.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2): 350?383.
[21] 王端旭, 李溪. 包容型領(lǐng)導(dǎo)對員工從錯誤中學(xué)習(xí)的影響機制研究[J]. 世界科技研究與發(fā)展, 2015, 37(1): 61?66.
[22] Walumbwa Fred O, Schaubroeck John.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Mediating rol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ork group psychological safet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5): 1275?1286.
[23] Zhang Y, Fang Y, Wei K K, et al. Exploring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in promoting the intention to continue sharing knowledge in virtual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0, 30(5): 425?436.
[24] 王永躍. 倫理型領(lǐng)導(dǎo)如何影響員工創(chuàng)造力: 心理安全感與關(guān)系的作用[J]. 心理科學(xué), 2015, 38(2): 420?425.
[25] 李銳, 田曉明, 凌文輇. 管理開放性和上下屬關(guān)系對員工親社會性規(guī)則違背的影響機制[J]. 系統(tǒng)工程理論與實踐, 2015, 35(2): 342?357.
[26] 林曉敏, 林琳, 王永麗, 等.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與團隊績效: 交互記憶系統(tǒng)的中介作用[J]. 管理評論, 2014, 26(1): 78?87.
[27] Bandura A.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86, 4(3): 359?373.
[28]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3): 541? 572.
[29] Tierney P, Farmer S M. Creative self-efficac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over tim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1, 96(2): 277?293.
[30] Schwarzer R, Babler J, Jianxin Zh, et al. The assessment of optimistic self -beliefs: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Spanish,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46(1): 69?88.
[31] Bandura A, Locke E A. Negative self-efficacy and goal effects revisited[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1): 87?99.
[32] Ahearne M, Mathieu J, Rapp A. To empower or not to empower your sales for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behavior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5): 945?961.
[33] 溫忠麟, 葉寶娟. 中介效應(yīng)分析: 方法和模型發(fā)展[J]. 心理科學(xué)進展, 2014, 22(5): 731?745.
[34] Liu D, Hang Z, Wang M. Mono-level and multilevel mediated moderation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Theorization and test[C]// Chen X, Tsui A, Farh L.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553?587.
[35] Aiken L S, West S 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M]. Newbury Park: Sage, 1991: 9?21.
[36] 何燕珍, 張瑞. 授權(quán)型領(lǐng)導(dǎo)對服務(wù)類員工親社會性違規(guī)行為的影響機理[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 2016(2): 17?28.
[編輯: 譚曉萍]
The effect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YAN Aimin, ZHAO Hao, ZHAO Deling, LIN Lan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generally view employees’ rule-breaking behavior as originating from anger, self-interest, or misfit wit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However, employees may also engage in so-called “pro-social rule-breaking,” that is, breaking rules for pro-social or non-selfish reasons. Based on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on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perception.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f 399 employees from 30 firms, we found that empowering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with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safety mediating this relationship. We also found that self-efficac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on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through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safety.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empowering leadership; psychology safety; self-efficacy
F272.92
A
1672-3104(2017)05?0076?09
2017? 04?25;
2017?07?28
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項目“高績效工作系統(tǒng)在不同組織中的形成與演化——多案例研究”(71372062)
顏愛民(1963?),男,湖南邵陽人,管理學(xué)博士,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趙浩(1992?),男,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趙德嶺(1991?),男,河南濮陽人,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林蘭(1993?),女,福建福州人,中南大學(xué)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