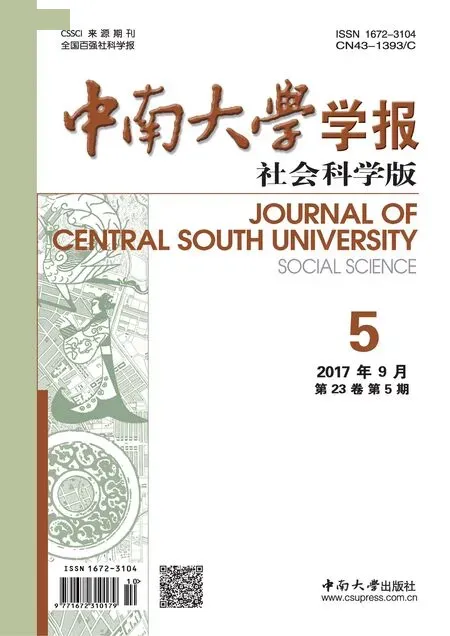曹植擬樂府的創作模式及其詩歌史意義——漢魏六朝詩歌傳播研究之六
吳大順
?
曹植擬樂府的創作模式及其詩歌史意義——漢魏六朝詩歌傳播研究之六
吳大順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桂林,541004)
曹植擬樂府存在“擬調”和“擬篇”兩種方式。他在“擬篇”中大膽創新,突破樂府詩的音樂限制,突出樂府詩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結,為文人徒詩在立意、謀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經驗和范式,進一步鞏固了“建安風骨”的文壇地位,從而完成了中國詩歌從“應歌”到“作詩”的轉移,還創建了文人擬樂府的基本模式,為西晉傅玄、陸機等文人擬樂府提供了參照。曹植“擬樂府”的創新,又是以建安時期詩歌的文本傳播和文人結集之風的興起為背景的,“建安風骨”發生、發展、形成及其在文壇確認的歷史進程剛好處于中國文化傳播媒介由簡帛為主向紙張為主的大轉變時期,紙張書寫的興起,為文學傳播提供了媒介基礎,有效刺激了詩歌的文本傳播和文人結集之風。
曹植;擬樂府;模式;文本傳播;范式
隨著建安七子的相繼離世,鄴中文人詩酒唱和的文學活動場被打破,加之曹丕稱帝后對曹植等曹氏諸王的政治排擠和迫害,建安文學的政治文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曹植的詩歌創作,較鄴中時期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是在題材上開始由游宴、贈答、送別等社交性內容向抒發個體人生遭遇和政治苦悶轉向;二是在詩歌體式上多采用樂府體;三是在詩歌結構上增加了抒情的比重;四是在創作技巧上更注重比興和辭華。這些創新,使曹植詩歌在情感上做到了濟世之情與個人私情的交融,在藝術上做到了風骨與文采的結合,所謂“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1],從而完成了中國詩歌創作由“應歌”向“作詩”的轉變,推動了詩歌文學的自覺。中國詩歌在曹植時代完成這個轉變,除曹植這位天才詩人的大膽創新和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等因素外,此期文學傳播媒介的變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擬重點探討曹植擬樂府的創作模式,以及曹植擬樂府的新變與建安文學傳播媒介變革的關系。
一、黃初、太和時期曹植詩歌體式述略
據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曹植黃初時期的詩歌有:《雜詩》“高樹多悲風”、《磐石篇》《仙人篇》《游仙》《升天行》二首、《責躬詩》《應詔》《七步詩》《贈白馬王彪》《浮萍篇》《七哀》《種葛篇》《苦思行》《矯志》《鞞舞歌》五首等20余首。


曹植還是建安詩人中大量使用五言創作的詩人。現存41首樂府詩中有30首五言,其中相和三調樂府13首,擬雜曲樂府13首,《鞞舞歌》4首。另外,曹植現存36首文人徒詩,除《元會》《責躬》《應詔》《朔風》《矯志》《閨情》等6首四言、《離友》2首騷體外,其余28首全為五言。五言詩體占曹植全部詩歌的75%①。建安是“五言騰踴”的時代,建安詩人普遍采用五言進行詩歌創作,曹植最為突出。
二、擬調與擬篇:曹植擬樂府的兩種方式
漢魏擬樂府存在擬調和擬篇兩種基本方式,曹植作為建安時期擬樂府最多的詩人,他對擬調、擬篇兩種方式都有采用。總體而言,其相和三調歌辭多擬調,而雜曲歌辭則多擬篇。
(一) 擬調與擬篇的雙重觀照:曹植相和三調歌辭的創作模式
曹植作為一名喜愛并精通音樂的文人,他的很多樂府詩是擬調而成的。如《平陵東》“閶闔開”: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采靈芝。靈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平陵東》古辭: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二者句式結構大體一致,當是典型的擬調之作。
又如《薤露行》“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曹操《薤露行》:
惟漢二十二世,所在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樂府解題》曰:“曹植擬《薤露行》為《天 地》。”[2]397內容上,曹操作品從漢代建國歷史開始,重點敘述漢末國亂的史實,表達其對漢王朝的“黍離之悲”。曹植作品開篇依循《薤露行》曲調的挽歌性質和悲嘆“人命奄忽”的傳統主題,敘寫人生短暫之悲,接著詩歌拓展出以王佐之才“輸力明君”、以“逕寸”之翰“流藻華芬”的愿望。《薤露》古辭,《宋書·樂志》失載,《樂府詩集》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曹操、曹植的擬作在結構上完全一致,而與《樂府詩集》所載不同,二者依擬的可能是曹魏時期傳唱的《薤露行》曲調。曹植另有一首《惟漢行》,則是擬曹操《薤露行》“惟漢篇”的作品,屬于擬篇之作。《樂府詩集》曰:“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曹植又作《惟漢行》。”[2] (396)總體而言,曹植擬相和歌及清商三調的作品,在句式結構上與原作和同期其他擬作基本相似,這一特點是擬作遵循原曲音樂要求的結果,屬于擬調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曹植的作品除了句式結構上與原作保持一致外,在題材、主題和抒情方式上也與原作保持一定的內在聯系:或從原作主題中引申,或從原作的某個點宕開拓展,體現了文人擬樂府的新創。在情感表達上,曹植詩歌也以抒發個體情感為主,但與曹操、曹丕不同的是,他往往以史事和寓言式的故事影射現實、傳達比興寄托,顯得含蓄曲折。在結構上,曹植詩歌也多以史事或虛構的寓言故事展開,而且這些史事或寓言僅僅作為詩歌主題的說明,不求故事的完整性。這種結構方式大大減弱了詩歌的故事性,增強了詩歌的抒情性。如曹植《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云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淵。驚飚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愿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麋滅豈不痛,愿與根荄連。
《樂府解題》曰:“曹植擬《苦寒行》為《吁 嗟》。”[2](499)可見,《吁嗟篇》是曹植擬曹操《苦寒行》“北上篇”的作品。在句式結構上,曹植《吁嗟篇》與曹操《苦寒行》完全一致,但在主題上,《吁嗟篇》不依擬《苦寒行》“冰雪溪谷之苦”[2](496),而是敘寫轉蓬“長去本根逝”“流轉無恒處”的飄零之悲,表達轉蓬“愿與根荄連”的愿望,在曹操《北上篇》基礎上進行了拓展和升華。詩歌雖然以第三人稱展開敘述,但“轉蓬”故事是作者虛構的,具有明顯的比興寄托意義。在抒情方式上,詩歌以轉蓬為喻,通過轉蓬“愿與根荄連”的愿望,表達作者對自己“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轉蓬式命運的感傷,感情雖然慷慨悲苦,但用寓言方式表達,顯得委婉含蓄。又如《怨歌行》“為君”: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泫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盡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后莫相忘。
詩歌開篇發出“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的感慨,接著以周公旦推心輔佐王室,而管叔、蔡叔以流言反之的史事予以說明,詩中的史事篇幅雖然很大,但僅是詩歌觀點的“論據”,不是詩歌的主體,而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又使詩歌與漢樂府傳統保持一定聯系。
可見,曹植的相和三調樂府詩創作是在原曲音樂風格和歌詞內容的二維參照中進行的,作品既考慮了曲調的音樂要求,也充分注意了曲調反映的傳統內容和主題,體現了擬調與擬篇的雙重性質。
(二) 擬篇:曹植雜曲歌辭的創作模式
曹植的雜曲歌辭在其樂府詩中獨具特色,是典型的“擬篇”之作。《樂府詩集》共收曹植雜曲樂府21篇②,內容涉及游仙者最多,有《升天行》《仙人篇》《游仙》《遠游篇》《飛龍篇》《驅車篇》等10余篇,其他涉及游俠如《白馬篇》、履險如《盤石篇》、美女如《美女篇》、棄婦如《種葛篇》、宴娛如《名都篇》等,題材十分廣泛。據《樂府詩集》“雜曲歌辭”解題,雜曲有幾種情況:一是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二是不見古辭而后人繼有擬述者;三是因意命題,學古敘事者[2](885)。雜曲歌辭或存古辭、或存擬辭、或學古自作的三種情況,說明這些曲調基本不歌、不傳了,曹植的雜曲樂府多是以古辭或擬古辭的文本為依據的“擬篇”之作,其中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的作品,當是根據曹植對樂府詩傳統和藝術精神的理解而進行的獨創。相比相和三調樂府而言,曹植的雜曲樂府更加強調詩歌的文本意義,文人化特征更為鮮明。
第一,在情感表達上,往往通過神話故事、美女棄婦,或他事他物的比喻和象征,表達詩人的個體情感體驗。這些詩歌的情感雖然多從詩人個體角度而發,但又總是將觸發情感的真實原因隱藏在虛構的人物和場景之中,使詩人個體的特殊情感通過人們所能感受到的人物或場景的比喻象征意義表達出來。如《美女篇》借一位妖閑皓素的美女成年處房室而不得所配的嘆息,表達詩人為君猜忌而不得任用的痛苦;《盤石篇》借“盤石”的身世和遭遇表達詩人“身本盤石而跡類飄蓬”的痛苦;《飛龍篇》借乘龍升天、求仙問道來表達詩人急欲擺脫現實的超世之情。
第二,在詩歌結構上,往往通過故事來結構全篇,在敘事中抒情。如《白馬篇》塑造了一位為國赴難、視死如歸的“游俠”形象,詩歌以賦筆展開描寫,上半敘述游俠的著裝、出身,接著鋪陳游俠高超的射技;下半敘述國家有難,游俠挺身而出,不顧性命和私情;最后以“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結束,總結游俠高尚的品質。全篇從頭至尾都是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敘述游俠的故事。最后兩句在對游俠故事的概括和總結中表達詩人對游俠高尚品質的贊美。《美女篇》全詩30句,前22句都是敘事。開篇寫女子采桑歧路,接著寫女子的穿著打扮和高潔的氣質,并以行徒和休者的反應作映襯,再寫女子青樓高門的家世和門第。最后8句抒發“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的感慨。全詩以第三人稱視角展開敘事,美女采桑情節及外貌描寫明顯是模仿漢樂府《艷歌羅敷行》而來,后半的感慨抒情,也從美女角度著眼。《飛龍篇》則以乘龍升天為線索展開敘事,先寫晨游太山、忽逢二童、長跪問道,后寫西登玉堂、授我仙藥、教我服食,最后表達“壽同金石,永世難老”的愿望,構成詩歌以敘事為主的結構模式。比較而言,曹植相和三調樂府詩往往弱化敘事成分而突出抒情色彩,而雜曲樂府則有意強化敘事成分,并多從第三人稱視角敘事,體現了詩人對漢樂府傳統的認識和理解。

另外,在曹植雜曲樂府中還出現了“當××行”的詩題,如曹植雜曲樂府《當來日大難》《當墻欲高行》《當欲游南山行》《當事君行》《當車已駕行》等。《說文解字》曰:“當,田相值也。值者持也,田與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持相抵皆曰當。”[3]后引申為“頂替”“代替”。曹植雜曲樂府“當××行”的“當”就是“代替”的意思,是魏晉擬樂府的標志。《樂府解題》曰:“曹植擬《善哉行》為‘日苦短’。”[2](540)“日苦短”是曹植《當來日大難》的首句。朱乾《樂府正義》曰:“當,代也,以此代《來日大難》也。”[4](147)又黃節《當墻欲高行》解題曰:“郭茂倩《樂府》墻欲高 行無古辭,蓋已佚,以子建此篇之當字,知必有古辭也。”[4](153)陸機有《當置酒》1篇,是擬曹植《野田黃雀行》“置酒”篇而成的作品。《樂府解題》曰:“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言歸于知命而無憂也。”[2](570)陸機《當置酒》首句“置酒宴嘉賓”來自曹植“置酒”篇。后來鮑照的樂府詩往往用“代××行”。曹植雜曲樂府“當××行”標題,說明詩人已經有意識地擬作樂府古辭,標志文人擬樂府的創作意識開始形成了。
如果說曹植相和三調樂府是在音樂曲調和歌辭文本的二維參照中進行的,具有擬調和擬篇的雙重性質,那么其雜曲樂府則更多地體現了曹植對歌辭文本意義的重視。曹植能在雜曲樂府中創新,是因為他所擬的這些雜曲歌辭基本上都是以文本傳播的,其因意命題、學古敘事的一些作品其實就是自己的獨創,沒有依擬對象,但憑作者對漢樂府歌辭的認識和理解,確立主題,安排結構,選擇表達方式。
三、建安文學傳播媒介變革與曹植樂府詩的文學史意義
漢末建安時期,隨著造紙技術的發展和工藝的改進,紙張被大量用于書寫領域。日常往來書信、書法作品、朝廷文書、詩文作品以及經傳圖書均開始使用紙張書寫,傳播媒介進入簡、帛、紙并用時代。紙張書寫的普及,為文學文本傳播提供了便利的物質技術條件,帶動了詩歌文本傳播由簡向紙的過渡,建安詩歌傳抄和文人結集之風開始興起。
建安時期的曹魏政權十分重視典籍整理和詩文結集。曹操時代,就十分重視對圖書典籍的收集工作。《三國志·袁渙傳》載,魏國初建時,袁渙向曹操建言,“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深得曹操贊許。建安三年,曹操破呂布時,曾“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5](334?335)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戰,曹操破袁紹,“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5](21)。曹操還曾向蔡琰征集家藏墳籍。《后漢書·烈女傳》載:“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有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6]
魏文帝黃初時期,設立秘書監,專門負責圖書典籍的收集和整理。《晉書·職官志》載:“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后省。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7](735)《初學記》卷十二,秘書監條曰:“魏文帝黃初初,分秘書立中書,中書自置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別掌文籍焉。……及王肅為監,以為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之職,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不復焉。”[8]
曹魏政權收集的圖書文籍,皆藏于秘書監藏書閣,秘書監中有秘書丞、秘書郎等屬官負責圖書文籍的整理、校勘和編撰。曹魏時期在圖書典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大的兩件事,一是魏文帝組織眾多文人編撰大型類書《皇覽》[5](65);二是魏明帝時期,秘書郎鄭默對曹魏秘書中外三閣的藏書進行“考覆舊文,刪省浮穢”[7](1251)的整理,并按甲乙丙丁四部,編撰《中經》十四卷[9],此不贅述。
在此背景下,建安時期的文集編撰也開始盛行起來。曹丕是建安時期文集編撰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他曾親自編訂自己的文集。其《與王朗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余篇,集諸儒于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5] (88)此信首先強調“著篇籍”對于人生“不朽”的重要意義,然后回顧自己將“所著《典論》、詩賦百余篇”結集之事,即如《本紀》所云:“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5] (88)此外,他還編訂過建安七子的文集。其《又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5](608)“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就是將建安七子的遺文合編成一集,此有后來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及序為證。曹植也曾自編過自己的文集。其《前錄自序》云:“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10]曹植死后,魏明帝曾下詔“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5](576)。其他文人作品的結集情況亦有載籍,如《三國志·吳書·薛綜傳》載:“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于 世。”[5](1254)《三國志·王昶傳》注引《別傳》任昭先傳曰:“文帝時,為黃門侍郎……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余言。嘏卒后,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群言。”[5](555)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說:“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11]
曹植樂府詩創作是在上述傳播媒介變革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從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為太子至建安二十五年代漢稱帝,曹植身處曹丕、曹睿父子猜忌、排擠和嚴酷迫害的環境之中,其樂府詩被樂官采集、配樂演奏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事實上,曹植現存40篇樂府詩,有配樂記錄者僅《野田黃雀行》“置酒”篇(《箜篌引》亦用此曲)、《怨歌行》“為君”篇、《鼙舞歌》5篇及《怨詩行》“明月照高樓”等8篇③。劉勰說:“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12]建安時期,由于文學媒介的紙本化變革和文人對文本文學的日益認可,曹植便有意識地突破樂府詩的音樂限制,突出樂府詩的文本化特征和文人文化情結,在情感表達、詩歌結構和命題方式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和創新。曹植在樂府詩創作方面的探索和創新,為當時文人徒詩創作在立意、謀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經驗和創作范式,進一步鞏固了“建安風骨”這一時代風格和創作范式在文壇的地位,完成了中國詩歌從“應歌”到“作詩”的轉移,也為西晉傅玄、陸機等文人擬樂府提供了參照,創建了文人擬樂府的基本模式。曹植樂府詩的文學史意義正在于此。
注釋:
① 關于曹植現存詩歌的數量問題,存在一些爭議: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收詩77首,另收非曹植所撰而舊集誤收者3首;黃節《曹子建詩注》收詩70首。今據《曹植集校注》,定為77首。
② 郭茂倩《樂府詩集》將曹植《斗雞》亦收錄為雜曲歌辭。
③ 曹植《明月》篇,《曹植集》《文選》皆作《七哀詩》,《玉臺新詠》作“雜詩”,《宋書·樂志》作《楚調怨詩》“明月”,《樂府詩集》作《怨詩行》,當是樂工選詩配樂所至,與擬樂府性質不同。
[1] 曹旭. 詩品箋注[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9: 56.
[2] 郭茂倩. 樂府詩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9.
[3]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697.
[4] 黃節. 曹子建詩注[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5] 陳壽. 三國志[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6] 范曄. 后漢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2801.
[7] 房玄齡. 晉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4.
[8] 徐堅. 初學記[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294.
[9] 魏征. 隋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3: 906.
[10] 趙幼文. 曹植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434.
[11] 章學誠. 文史通義[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296.
[12]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103.
[編輯: 何彩章]
The creation and propagation modes of imitation of Yue Fu from Cao Zhi
WU Das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There are two modes in Cao Zhi's imitation of Yue Fu: imitation of music and imitation of article. He intentionally breaks through the music limitation of Yue Fu poetry, boldly innovates in the imitation of article, emphasizes the papery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ti complex of Yue Fu poetry, and provides creation templates on concept, plan, and expression for literati. All of those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ole of vigorous style of Jian An,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or Chinese poems from being in response to song to create poems. The innovations of imitation of Yue Fu by Cao Zhi is dependent on the papery propagation of poems at Jian An period and the rise of literati gathering habi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or vigorous style of Jian An from birth, development, maturity on literature conforms with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Chinese culture propagation main media from bamboos slip to paper. The emergence of paper provides media bassis for literature propagation, and spurs the papery propagation of poems at Jian An period and literati gathering habit.
Cao Zhi; imitation of Yue Fu; model; papery propagation; template
I207.226
A
1672-3104(2017)05?0166?05
2017?03?13;
2017?08?25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學史研究”(15XZW016)
吳大順(1968?),男,苗族,湖南保靖人,文學博士,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文學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