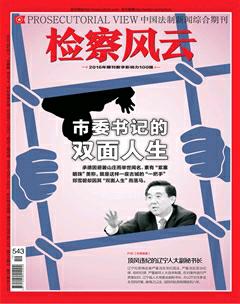遺忘讓人更聰明
貢水
遺忘是記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根廷著名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中,塑造了一個“超憶癥”患者富內斯。他從馬上摔下來后,獲得了不可思議的記憶能力。不但輕而易舉地學會了幾國語言,而且細到連朝霞的形狀、水池的漣漪、書皮的紋理……都能過目不忘。然而這些技能并不讓人羨慕,因為最終只能讓富內斯墜入了永無止境的細節之中。
心理學家發現了導致“超憶癥”患者擁有這種超常能力的大腦構造差異,他們連接大腦中間和前部的白質比常人更強健,這些腦部構造的差異主要存在于和自傳式記憶相關的區域。事實證明,“超憶癥”患者在考試中記憶事實和數字等方面的能力并不比普通人突出。試想,如果將經歷的每一個無關緊要的細節都深深烙印在大腦里,人還能聰明起來嗎?
英國《每日郵報》6月21日報道,最近有關大腦遺忘機制的研究數量明顯增加,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遺忘是記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久前,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保羅·弗蘭克蘭和布萊克·理查茲在《神經元》雜志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了大腦積極地選擇“遺忘”這個長久以來被我們忽視的問題。他們提出,人類大腦不像攝影機那樣機械記錄,記憶的目標并非隨著時間推移傳遞最準確的信息,而是通過掌握最有價值的信息以指導和優化智能決策,忘記或許會更有助于人們日后做出最佳判斷。
大腦是如何形成記憶的呢?可分為對信息的編碼、鞏固和提取三個階段。編碼階段指收集信息的過程,對通過聽覺、嗅覺等不同渠道感知到的信息進行收集與處理,形成短期記憶。
鞏固階段是將記憶穩定儲存的過程,將其中一部分短期記憶保留下來成為更長期、穩固的記憶,另一部分短期記憶則會被遺忘。研究發現,大腦會在人們的睡夢中回顧過去收集到的信息,并選擇出重要的部分,將它們從儲存短期記憶的區域挪到儲存長期記憶的區域中去。提取階段指的是將儲存的記憶取出,來回應外界刺激的過程。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想起”一些事時,就是經歷了記憶的提取階段。由于一段記憶的細節信息分散儲存在大腦里,我們回憶時會用自認為合理的方式,重新組合細節信息,形成一段記憶敘事。如果一些細節模糊了,大腦甚至會將其他記憶中的細節拿過來,填補這段記憶的空缺。
我們總認為,好記憶就是永遠不會忘記東西,能夠長時間清晰地記住更多信息。心理學家的觀點卻正好相反,說大腦正積極努力地忘記,忘記東西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操縱”一個隨機和不斷變化的世界。忘記不相干的細節是大腦的一項重要工作,可以讓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助于現實決策的信息上面。大腦的原則是,終生記住那些特別的事情,像遭受襲擊等,以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別的一律會忘記。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大腦只選擇記住進化觀點上對我們有益的事情。
為了研究遺忘的作用,弗蘭克蘭和理查茲曾進行過一項訓練小鼠尋找“水迷宮”的實驗。科學家將它們分成兩組,首次尋找“水迷宮”之后,給第一組小鼠注射一種藥物,幫助它們忘記原來的記憶,第二組小鼠則沒有注射藥物。接著移動“水迷宮”再次進行實驗,結果忘記之前位置的第一組小鼠發現新迷宮的時間要比第二組短得多。
新增神經元“抹去”童年記憶
許多人記憶力不錯,但奇怪的是在記憶兩頭會處于空白階段,一頭是在老年,另一頭是在童年。老年時的失憶不難理解,因為人老了許多生理機能會退化。但兒童的失憶癥卻很費解。那么,彌足珍貴的童年記憶是在哪里丟失了的呢?
曾有觀點認為,孩子7歲之前根本無法形成穩定的記憶,所以遺忘是必然的。然而1980年后的一系列實驗表明,兒童早在3歲前就開始記事了,嬰兒6個月時的記憶可以至少持續一天,兩歲可以記得一年前的事情。2005年,心理學家們發現,4歲半的孩子可以詳細回憶18個月前的一次迪尼斯之旅;5歲半的時候,能把3歲時80%的記憶記住;大約到了7歲半,孩子們才開始忘記許多早期記憶,只能記住40%的童年生活。綜上所述,可見兒童不是因為沒有發達的記憶能力才記不住。他們同樣可以創建記憶,并且能檢索記憶。
心理學家將重點放在研究是什么讓記憶7歲后快速消失,除了缺乏語言能力和自我意識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我們的童年記憶。研究人員注意到,人們并不會忘記童年時代的所有事情,比如小時候學會的行走、游泳和騎自行車這些動作就一直歷歷在目。相較而言,往往忘掉的是那些與長期記憶有關的過往經歷或事件的情景記憶。
在大腦的長期記憶中,海馬體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位于大腦顳葉,緊密聯系著大腦的邊緣系統,經過過濾的信息會在海馬體中暫時儲存,時間是幾分鐘至幾周,重要的感觀信息會由海馬體中的神經元傳輸到長期記憶區中。嬰兒每秒會形成700個新的神經元連接,問題是不是出在這些神經元上?
為了研究神經元和遺忘之間的相關性,心理學家進行了一個這樣的實驗:訓練老鼠,使它們對輕微的電擊環境十分害怕,然后分成兩組;將第一組放到一個可以踩車輪的環境,隨之再返回到電擊環境中,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忘記了電擊的恐懼;第二組老鼠因為沒有踩過輪子,依舊記住了電擊環境和恐懼的關聯性。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第一組老鼠之所以忘記了之前的恐懼,在于踩車輪運動提高了神經元的活躍度,換句話說,老鼠新生的神經元可能干擾了之前的記憶。
科學家證實,新增的神經元是偷走童年記憶的“真兇”。哺乳動物在成長過程中,大腦中有兩個其他動物沒有的區域在不斷地產生神經元,海馬環路是其中一個。新的神經元在海馬環路中不斷生成,激烈地爭奪著“地盤”,改變預先存在的神經元連接,建立新的神經元連接,嚴重擾亂了儲存舊記憶的大腦電路。大多數這些早期的連接最后會被“修剪掉”。導致其被毀壞,使這部分記憶被遺忘。在7歲之前,這種“地盤”爭奪尤其激烈,后隨著年齡增長神經元形成會放緩。大概在7歲左右,大腦的海馬體實現了較穩定的神經元連接,人們開始能保存情景記憶。
心理學家指出,要想找回童年記憶目前看來不太可能,因為一些舊的神經元連接可能已經被“修剪掉”,無法再恢復。即使一些早期記憶經受住了大腦生長和衰退的周期動蕩,但也可能產生記憶變形,無法令人過于相信。1995年,研究人員曾進行過一次實驗,向志愿者講述了一些他們自己的童年故事。故事是從志愿者親友那兒征集來的,其中有一個純屬虛構,他們并不知情,說的是曾經在5歲前在商場走失過。結果有25%的志愿者認定這就是自己童年時候發生的事情。在被告知這個故事是捏造的,一些人依然堅持是真的。實驗表明,一些人認為自己能回憶起來的童年經歷,有可能摻雜了許多別人的故事或幻想成分。endprint
“隨著新神經元整合進海馬,新連接重建海馬環路并覆蓋存儲在這些環路中的記憶,使得它們更難獲取,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孩子們不記事。由于神經元在不斷新增,防止一些已經存在的記憶被遺忘是不太可能的,我們也許會不可避免地丟掉童年記憶。”弗蘭克蘭表示,“但有失就會有得,如果沒有這樣靈活可塑的大腦,年幼的孩子將沒法展示驚人的學習能力和記憶能力。”
記憶和遺忘的交互做出的決策更明智
研究人員發現,大腦存在促進遺忘的機制,而且與存儲信息的機制不同。遺忘的機制之一是削弱或消除編碼記憶的神經元之間的突觸連接,強行讓人遺忘。弗蘭克蘭在實驗室還發現另一種機制——干細胞中產生新的神經元。大腦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創造出新的神經元損害記憶,似乎是違反直覺的。弗蘭克蘭和理查茲希望通過人工智能的學習原理來尋求答案。他們構建了人腦以智能決策為目的的“記著”和“遺忘”互作框架,其中“遺忘”可以讓我們拋棄過時的、潛在錯誤的誤導信息,幫助適應新環境。
“如果你試圖駕馭世界,而你的大腦不斷地回閃許多沖突記憶,這使你很難做出明智決定,”理查茲強調道,“遺忘讓我們不得不將過去事件概括成新事件,從而促進決策生成。” 這兩位科學家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大腦去粗取精的遺忘會創造出簡單的記憶,記憶與遺忘之間的相互作用使我們能夠做出更加智能的基于記憶的決策。當我們只記得重點而不是每一個細節時,對于我們預測新的經驗更為有效。
遺忘促進決策過程以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通過遺忘過時和潛在的誤導性信息,使大腦更有效率,能夠適應新環境。以環游世界為例,如果大腦不斷地冒出多個相互沖突的記憶,那么就難以做出明智的決定。二是通過對以前的事件進行歸納,以記住更重要的信息,并將其應用于新的事件。這與人工智能“正則化”的學習過程極為相似,具體實現是通過創建優先處理核心信息和消除具體細節的簡單計算模型,拓廣適用范圍。大腦記憶只需抓住要點,不必記住所有細節。這種主動控制的遺忘機制能過濾無關緊要細節,生成簡單記憶,使大腦更有效率地預測新情境。
遺忘機制還被我們所處的環境所引導,不斷變化的環境可能會讓大腦遺忘更多。至于在哪種環境中選擇記憶或遺忘,取決于環境的穩定性以及事物將來再次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可能性。例如,收銀員每天遇到很多新顧客,只會在短期內記住他們的姓名。但是設計師就不一樣了,由于與客戶定期會面,能將信息記得更久。研究表明,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情景記憶比我們日常接觸的常識會更快地被遺忘,為了更好地做出基于記憶的決策,最好拋棄那無關緊要的記憶。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