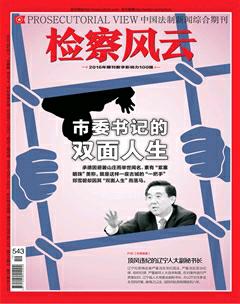犯罪“供給側(cè)”改革理念的價值
盡管長期以來,理論界和實務(wù)界更習(xí)慣和樂于站在犯罪“需求側(cè)”的角度,精雕和細耕何種行為應(yīng)規(guī)制為犯罪、當如何量刑、該怎樣刑罰。然而,歷史和事實都反復(fù)告誡我們,嚴刑峻罰從來無法、也沒有真正制止住犯罪。因此,改革犯罪“供給側(cè)”的結(jié)構(gòu),降低既有犯罪“供給側(cè)”造成的犯罪高發(fā)現(xiàn)象,是一個利國利民的重要法治理念和制度創(chuàng)舉。
有助于摒棄“刑法中心主義”治理方式
刑法在打擊和遏制犯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始終居于最后法和保障法的地位。刑法的結(jié)果雖然非常嚴厲,但只能懲罰犯罪,不能消滅犯罪,而且刑法的處置只能是事后的、謙抑限縮和片段性的最后措施,甚至其預(yù)防犯罪的功能有限、成本太高。馬克思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歷史和統(tǒng)計科學(xué)非常清楚地證明,從該隱以來,利用刑罰來感化或恫嚇世界就從來沒有成功過。”其實,以暴易暴,倚仗暴力來解決問題,就容易形成社會的對立,但社會總不能處在兩極對立中走向危險的毀滅邊緣。比如,應(yīng)對和處置反恐問題,如不能充分重視行政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反恐法等刑法前置法的作用與價值,相反,過于倚重刑法對涉恐行為的處置和報應(yīng),則會使刑法難以承受之重,也起不到應(yīng)有的治理效果。
犯罪“供給側(cè)”改革理念的提倡,就是要盡大限度地減少社會治理對刑法的路徑依賴,“迫使國家和全社會在刑法之外尋求解決犯罪之道,促使國家和社會反犯罪措施走向理性化、科學(xué)化”。事實上,就作為自由人和犯罪人大憲章的現(xiàn)代刑法而言,其存在的意義也根本不是為了制止犯罪和打擊犯罪,而是為了保障人權(quán)、限制國家刑罰權(quán)的任意發(fā)動。人們會經(jīng)常性地反思和推敲刑法的界限在哪里,是否存在濫用、無效、過度和昂貴之刑,是否能通過其他相對平和的社會規(guī)范,如道德的、紀律的或者民事、行政、經(jīng)濟等法律手段來解決社會治理問題,而非把刑法作為國家應(yīng)對犯罪的主要法治方式和方法。
有助于推動社會制度革新和社會政策完善
犯罪是文明社會的衍生品,是社會各種矛盾與問題堆積、交織和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國家應(yīng)該針對有規(guī)律性的犯罪生成,著力采取措施,改變產(chǎn)生這些罪行的制度。如果只是一味依靠刑法來解決犯罪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也是對人的基本權(quán)利的不尊重,即“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的手段應(yīng)當是動用社會力量消除犯罪的社會的致罪因素。”這句話高度契合了德國刑法學(xué)家李斯特的那句至理名言,“最好的社會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相反,如果片面站在犯罪“需求側(cè)”的立場去思考,就會把眼光局限在定罪量刑的泥潭中、糾纏于刑法適用的質(zhì)量上。然而,一個國家的刑法立法無論設(shè)計再完美,也無非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甚至因立法的不當而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給社會傳遞了錯誤的信息,進而無法實現(xiàn)其預(yù)設(shè)的效能;同樣,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實踐再公平、再公正、再正義,即使不發(fā)生一個冤假錯案,也遠遠比不上防止一個犯罪的發(fā)生來的意義重大、功德無量。
犯罪“供給側(cè)”改革理念的提倡,就是要從源頭和制度層面加強對社會制度的革新和社會政策的完善。就拿當今依然十分嚴重的貪墨犯罪來說,如果貪腐的溫床還在,預(yù)防腐敗的制度還跟不上,那么,即便刑事法網(wǎng)再過嚴密、懲罰再過嚴重,到最后依然會形成官員的貪墨犯罪數(shù)額越來越高的現(xiàn)象。顯然,貪墨犯罪要完成“供給側(cè)”改革,除了要嚴格依法、重懲貪墨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從嚴治黨,將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讓黨紀黨規(guī)挺在刑法面前,準確運用好監(jiān)督執(zhí)紀“四種形態(tài)”,注重抓早抓小,盡可能在萌芽狀態(tài)發(fā)現(xiàn)貪墨行為、在黨紀黨規(guī)的范疇內(nèi)作出懲戒,確保實現(xiàn)“經(jīng)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tài);黨紀輕處分、組織調(diào)整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shù);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wù)調(diào)整的成為少數(shù);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shù)”。這才是依規(guī)治黨、依法反腐、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零容忍”反腐敗國家戰(zhàn)略應(yīng)有的正確態(tài)度和方式。
有助于倒逼刑法學(xué)與犯罪學(xué)實現(xiàn)整體互動
由于復(fù)雜的歷史原因和深刻的社會原因,我國的刑法學(xué)和犯罪學(xué)不僅長期保持彼此分離、各自發(fā)展的狀態(tài),而且還存在著發(fā)展嚴重不平衡問題,即刑法學(xué)的顯學(xué)和犯罪學(xué)的勢微。對于刑法學(xué)而言,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形成的社會機理、制度原因和環(huán)境因素等均不在或主要不在其研究的視野之中,其更多的是關(guān)注把那種行為入罪、怎么表述罪狀、如何設(shè)置刑罰等等;而對于犯罪學(xué)而言,由于人員的不足、資源的有限和學(xué)科地位的旁落等原因,對犯罪原因和犯罪規(guī)律的事前、事中研究卻難于深入、系統(tǒng),自然更談不上對刑法規(guī)定的某種或某類犯罪提出具有足夠說服力的廢、改、立建議。如此一來,就導(dǎo)致在認識和對待危害社會的行為上,我國總是習(xí)慣于在刑法出手后,對所謂的犯罪實行嚴厲打擊,而鮮見在犯罪發(fā)生之前或形成之時進行迅速反應(yīng)和有效預(yù)防。
犯罪“供給側(cè)”改革理念的提倡,使得人們的視線能夠跳出刑法看犯罪,實現(xiàn)了既能夠聚焦孤立犯罪的特殊成因,又能夠思考該類犯罪的普遍性原因。對犯罪原因的持續(xù)關(guān)注,必將倒逼刑法學(xué)和犯罪學(xué)的良性互動,表現(xiàn)在國家在治理某類危害社會的行為時,將由動輒刑法化處置方式轉(zhuǎn)向全面預(yù)防和消除該類行為產(chǎn)生原因的方向,通過對犯罪原因的深入研究,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檢疫機制、風(fēng)險預(yù)警機制和犯罪預(yù)防機制。顯然,對犯罪原因的研究和對危害社會行為的預(yù)防,遠比嚴刑峻法的懲罰手段來得更為高明、有效,因為對犯罪的懲罰畢竟是事后的社會反映,一個聰明的社會應(yīng)當將犯罪消滅在萌芽之中,“真正起釜底抽薪作用的是一個國家應(yīng)當如何有效地防止犯罪的發(fā)生。”這既包括還未進入刑法視野的一定程度的危害社會行為,還包括刑法雖然已經(jīng)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但國家和社會通過有效的犯罪原因分析、風(fēng)險預(yù)警機制和預(yù)防機制有效阻止該犯罪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