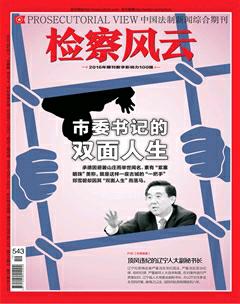暴徒先生
鄭金玉
前一陣子看澳洲的報紙,看到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前財長,可能當官時得罪了人,離職后在餐廳遭到三個年輕人攻擊。三人把他堵在衛生間里,其中一人按著他的腦袋向墻上猛撞。有意思的是,他是這樣描述打他的人:“這時一個Gentleman(先生) 沖了進來,開始打我的頭……”在描述案情時,他一直用極其正式的“先生”一詞,來稱呼對他施暴者。我們在這種情形下,一般應當咬牙切齒地說:有一個“家伙”,或有一個“暴徒”。
我于是注意到一個法律文化的細小差別。
在許多國家,對刑事被告人,無論他犯了什么樣的罪,法庭成員對他仍然以“先生”相稱。而我們是絕不會稱這些壞蛋為先生的。我從參加工作第一天起,就發現我們起訴書、判決,或者報道,都喜歡用“竄”這一個詞。犯罪分子一定是“竄”到犯罪地點的。一個人一旦成為社會的敵人,我們對其一定要用貶義。
在這樣的習慣之下,很多現象會讓我們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號稱“紅色男爵”的德軍王牌飛行員,擊落過八十多架英軍飛機,用我們的話來說:雙手沾滿了英國人民的鮮血。但是,當他被英軍擊落時,英軍卻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還放排槍向這位“英勇的戰士”致敬。
我們如果有人這樣做,可能會被追問:立場哪里去了?會遭到整個社會的唾罵。但是,當我們看到這幾個故事時,我們是不是對那位稱打人者為“先生”的前財長,對厚葬敵方飛行員的英軍,隱約有一些稱許呢?有什么東西,讓我們產生這一隱隱的稱許之意?
我們因此會發現:在仇恨與文明之間,后者往往擁有更強大的道德的力量。而這一道德力量,對于我們的社會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
當法庭對一個“人渣”仍然以“先生”相稱時,這不僅僅是尊重一個不值得尊重的人,這同樣關系到仇恨可能弄臟了我們自己的靈魂,從而破壞了文明,最終危害社會。
很久以來,我們一直不能容忍對敵人的尊重,而更崇尚“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我們對仇恨的考慮,甚于對文明的考量。西西里黑手黨有一個規矩:凡出背叛組織者,全家殺光。但是,如果這個人自殺了,家人就可以豁免。
一味強調“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就容易走向極端,甚至造成恐怖。我們崇尚“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但不幸的是,我們往往無法同時做到這兩種境界。習慣對敵人這樣以后,對同志一般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因為“無情”一旦變成習慣,對誰都會一樣了。我們有些機關,對待人民群眾,同樣也是“門難進,臉難看”,就是一例。在這樣的文化下,有些人連親屬也做不到“春天般溫暖”。遼南農村曾有一案,姐夫與舅哥打牌,為了五角錢,姐夫一刀捅死了舅哥。
其實,面對敵人仍要保持文明,這不是他國的特權,本來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太平天國李秀成東征,清軍猛將張國梁戰死于橋下,李秀成感其忠勇,也厚葬了對手。但不知從何時起,面對仇恨與沖突時,我們開始缺乏一種從容不迫,一種溫文爾雅,而更多是一種暴戾之氣。
兒童讀《狼和小羊》的故事,沒有孩子會說:“一條惡狼如何如何。”其實,人類的本性,還是知道:尊重敵人,其實是維持自己的文明。我們長大了以后,還是莫忘這一本性為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