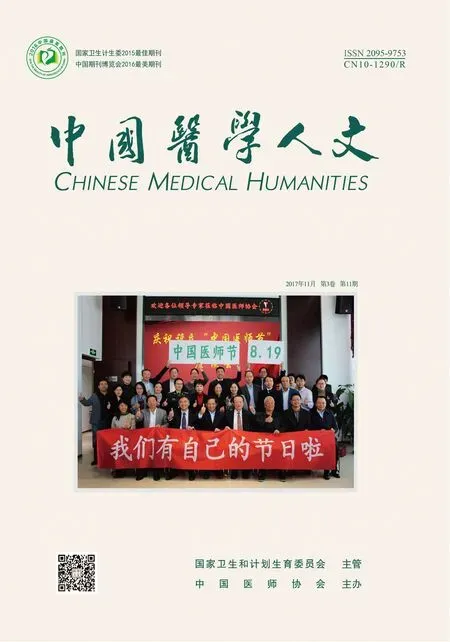賦予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
——安寧療護工作中的醫學靈性照顧
文/鄧 滌 路桂軍
賦予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
——安寧療護工作中的醫學靈性照顧
文/鄧 滌1路桂軍2
人文精神以一種非功利性的、以穿越時空的文化積累的形式全面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其作用就是為了維護人類尊嚴與自由,維護人類生存價值與意義。人文情懷是每個個體靈性能力的表現,不同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著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在醫療實踐中表現為患者的多元化需求和醫務人員應該具備的道德情懷。作為安寧療護工作的踐行者,應該敏銳地意識到患者對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的迷失和如何引導患者去追求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以提高終末期患者的生活質量并可能緩解當前尖銳的醫患矛盾。
人文精神 生命意義 醫學靈性關懷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替代醫學”改變了全球的醫學模式,醫學從單純的生物醫學模式轉換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在中國,為了積極發展醫養結合和延續性醫療服務,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的健康需求,國家衛生計生委制定《安寧療護中心管理規范(試行)》和《安寧療護服務指南(試行)》。安寧療護工作為終末期患者在臨終前,提供疼痛管理,心理疏導治療和人文關懷等相關醫療護理服務,以減輕患者痛苦與不適,提高生活質量。臨床工作中,對患者的癥狀控制和心理關注已經逐漸得到完善和深入人心,而對人文關懷卻總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更談不上臨床上的操作規范。本文試圖從醫學靈性照顧的角度厘清人文關懷在終末期患者診治行為中的概念,并初步介紹目前醫學靈性照顧的現狀。
靈性:人文角度的人的多元化需求
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首先是要活著,但為了與動物相區別,避免成為行尸走肉,還會考慮活著的意義,這是人的靈性使然。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會存在物,具有社會屬性,人終其一生都是在通過社會實踐營造自己的社會關系。因此,對一個人而言,死亡僅僅標志著以個體為中心的各種社會關系的不復存在,但同時卻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維系了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1。隨著人類適應和改造自然界的進步,文化的積累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類人文關懷的發展。
人文精神,體現了對人的終極關懷。它起源和形成于一個民族的文化軸心時代,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其意義是以一種非功利性的、以穿越時空的文化積累全面提升人的綜合素質,為民族的發展提供終極關懷。在特定時期,人文精神又表現出對歷史遺產的懷疑、批判和反思,如“五四運動”帶來了中華民族思想上的革命。同時,人文精神以一種并不反對科學的態度反對唯科學主義,其目的除了維護科學層面的“真”以外,還要促使人們追求非科學層面的“善”與“美”2。
人文科學,作為一門研究人文精神的學科,其作用就是為了維護人類尊嚴與自由,維護人類價值與意義。它可以讓一個人在建設物質世界的實踐中擁有一個可以克服私利與偏見、堅持公正美德的純粹的靈魂,擁有能夠敏銳判斷是非、善惡的自由心靈,最終為建立一個更好的倫理世界而不懈努力。
人們的心目中有一個熟悉而又陌生,與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關,體現人們日常生活多元化需求的詞匯來表達著自己的人文情懷和人文追求——靈性。長期以來,因為“靈性”被宗教獨占,或在強調集體作用的文明發展中,“靈性”被壓抑而得不到理論研究和個體實踐;同時也因為“靈性”這種帶有偶然性的表現難以發現其規律,更多地被誤認為是超自然的力量3。因此,“靈性”這個客觀的但又沒有一個確切描述的存在變得更加虛幻、神秘或者模糊不清。
其實,從人們熟悉的具備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來感知物性世界的角度分析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會發現“靈性”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陳勁松教授認為:人們用自己的感覺器官對自然界產生了感性認識,人們在實踐中逐漸具備了將事物概念化、做出判斷、進行推理的理性能力;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為一個人在“朝向物性世界”發展中,謀求生存的動力;人具有的靈性會在實踐過程中讓自己“遠離物性世界”,能夠不斷自我超越,用來規整自己人生方向,使自己不斷完美,進而體現一個人活著的意義與價值。靈性可以對一個人追求物性的“心理傾向”做出適度的調整,從而促進個體“自我實現”或“止于至善”,保證一個人既要活著,又要活得有意義。與物質生活相關的感性和理性成為追求幸福體驗的靈性工具,而靈性最為重要的能力又是能夠促使個體擺脫物性世界的束縛,保持一個適度理想的人生方向3。
因此,從追求生命意義與價值的角度,靈性是個體在精神生活中彰顯自己的文化素質、與自身的人文精神高度統一的科學能力。
醫學人文:健康領域的人的多元化需求
醫學越來越發達,生存壽命越來越長,能為人們解決越來越多的軀體上的病痛,并且產生了醫學科學無所不能的錯覺,鼓勵著人們追求生命永恒的幻想。然而,科技發展至今,醫學不但沒能為患者提供能夠達到生命永恒的希望,而且還讓患者產生了物非所值、被欺騙的孤獨感與憤怒感,我們的醫患關系越來越緊張,問題出在哪里呢?
人類在不斷追求生命永恒的過程中,疾病成為導致個體死亡最常見的原因,死亡總是在提醒和打斷人們的思緒。因此,人的靈性能力的成熟與覺醒促使著人的需求開始多元化,追求生命的意義成為醫學人文需求的首要表現,人們在其生命的各個階段,以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需求詮釋這種與自己文化環境和文化素養密切相關的對永恒生命的理解。
反映到醫療活動的實踐中,就表現為患者的醫學人文需求和醫學從業者的醫學人文情懷。
1981年,美國密蘇里大學哲學系的繆森在《醫學與哲學》雜志上提出“醫學不僅僅是一門科學”的觀念,恰當地反應了關于人的醫學的精髓。科學為醫學打開了一扇關于生命研究的廣闊大門,但精神、心理還不能完全被認為是純科學,醫學作為關于人的學問就成了摻雜著人的感情色彩的科學。人的感情色彩是什么——人文需求。“大夫,你是在觀察,而我是在感受”,這是一位患高位截癱的女性哲學家圖姆斯(Toombs)著名的用來描述醫生與患者之間關于疾病的感覺方面差距的名言,當一個醫生自己躺在病床上時,他(她)就會發現病人的世界是如此的敏感、豐富與無奈,僅有技術是遠遠不夠的。患者具體的人文需求需要醫學從業者敏銳的覺察和體現醫者醫學人文情懷的臨床實踐。
醫學人文情懷是一個醫學從業者人生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了《天才博士與非洲叢林》一書的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以其一生不平凡的經歷,在反復叩問自己為什么會放棄優越生活,重新學習醫學并服務非洲叢林土著居民52年的原因時,第一個用“敬畏生命”來感悟自己的心靈,只有這樣才能與其他的生命建立一種傾其所愛、具有向善的原動力的靈性、人性的關系,使自己的生命中追求永恒的生存意志與永恒生命得到結合。這種對生命的“敬畏”成為醫學倫理學的核心,體現在自己與自己生命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等層面的對生命的敬畏。
醫學人文情懷的培養正是在處理自己與自我、他人、社會以及自然的關系中形成與實現的。在醫學技術的人生中存在一個巨大的精神天幕,沿著博物學這條幽雅的精神路徑,可以尋訪醫學的美學意義、社會責任、對自然與知識的批評意識,可以獲得觀察世界時人性的、多元視角的寬容心態,從而在體制化的醫學與醫療的束縛下心存對自然的永恒好奇、天真、真誠,使醫學成為真正的人學,塑造具有人格化的技術,找回在技術時代里被忽視的人文精神。醫學的多元關懷就是要幫助醫科學生、執業醫師根據自己的認知個性、人格取向建立起有序、有益、有智慧、有情趣的道德生活,通過非職業閱讀、道德體驗、人生反思來培養人文情懷,使他們的職業生涯充滿世俗的高尚、溫寧的圣潔、平凡的智慧4。

因此,醫學的職業道德是一種尋常的關懷心,世俗的悲憫心,是一道人性的光芒、一份人道主義的內在呼喚。其本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價值追求,可以被傳統道德中的情懷、精神所教化與熏陶,它需要的是一個過程,需要產生誘導作用的機會去理解、去實踐、去升華。
醫學靈性關懷:賦予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
不論在個體成長的哪個階段,生命中各種“機緣”都會成為引領個體靈性感悟的關鍵事件。當現有醫療水平的局限使個體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時,這種生命中人人都有、時時都有、一度沉睡的靈性會再次覺醒、頓感迫切。這些需求與困惑正是患者對醫學技術之外、體現人文關懷需求的醫學靈性需求。每個個體在不同階段、所處的不同環境使每個患者會用自己的方式和語言來表達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和求之不能得的痛苦。患者因為對死亡的無知與恐懼,感受到的只是生命中的身體這種“物性”的得失,這種失去可能遮蔽了“靈性”的光芒,暫時感受不到自己的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這種在面臨困難時不能體會到自己的靈性需求和不能感悟自己靈性超越后的喜悅等狀況會明顯地影響到患者和家屬的生活質量。
醫學靈性照顧是一門古老而又新穎的科學,是人文精神和醫學人文關懷在現代醫學模式下確切的、與文化相關、與世界醫學研究接軌的醫學學科,為提高終末期患者的生活質量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弄清楚每個患者個體化的醫學靈性需求成為提供個體化醫學靈性照顧的前提。作為專業的照顧者,醫務人員除了關注醫療技術的進步外,重點關注的就是如何意識到患者對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的迷失和如何引導患者去追求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有時能治愈,常常給幫助,總是去安慰”,這句鐫刻在特魯多醫生的墓碑上的名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醫學從業者的切身體會和病患者的真實需求。在醫學人文情懷的引導下,照顧者使用個體化的醫學靈性照顧的方法和途徑發現每個患者醫學靈性困擾的具體表現、分析產生生命意義與價值迷失的原因、引導患者感受和重建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是履行醫學靈性照顧的必經之路。所有這些我們稱之為給患者“賦予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要給予面臨生命威脅的患者以高質量的醫學靈性照顧,讓患者找回和體會到他自己余下的、有限的、痛苦的生命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的永恒意義與價值。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在西方國家那些有著虔誠宗教信仰的終末期患者,在他們明知有限的生命里最希望做的前五件事分別是與家人和朋友待在一起、看到別人的微笑、想一些幸福的往事、大笑和談一些日常的事情,祈禱只是排在那以后,專門舉行儀式或親自交待與自己靈性有關的主題則排在更后面了5。在中國,我們調查那些放棄抗腫瘤治療,僅僅接受安寧療護的終末期患者的靈性需求時發現,他們同樣是更愿意與家人和朋友待在一起,他們首先是希望能更好地緩解自己的不適癥狀,然后想去完成一些因為種種原因過去沒有完成的、甚至因為疾病已經永遠不能完成的愿望,如出去旅游、陪伴家人、彌補過去犯下的過失、完成自己人生的回憶錄等,他們同樣是希望在自己離去后家人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設想沒有自己家庭的生活情境、自己靈魂的歸處6。如果我們將患者的這些想法稍作總結與條理化,我們不難發現患者的靈性需求大約應該包括生命末期的希望與夢想、表達生命意義的儀式、回憶并整理自己的往事、尋找支持內心力量的源泉、與他人接觸、創造一個安全的休息環境、照顧好家人等方面的內容7。
從這些調查結果中我們發現: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不論是有宗教信仰還是沒有具體宗教信仰,終末期患者在其生命的最后階段,他們的靈性需求和靈性困擾絕大多數還是圍繞著表達自己生命的延續的,包括對自己和家人的四道人生(道愛、道謝、道歉、道別)6。其實這并不奇怪,家庭是一個人賴以生存和發展最熟悉的環境、是一個人寄予希望的生物學載體、是一個人的社會生活的表現形式。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個家庭的生命是無限的,由一個個家庭組成的社會生命也是無限的,每個人將自己有限的生命看作為家庭無限生命延續中的一環,這一環對組成家庭、社會這種無限生命的鏈條是必不可少的,否則無限生命就不可持續。終末期患者的靈性需求和靈性困擾都是圍繞著自己最迫切的希望與夢想。
這些愿望有些也許能夠實現、有些也許很難再親身經歷。怎么辦?我們的感受是:1.通過調動和強調親情,引導患者表達靈性需求;2.能努力解決的需求應在家屬、醫護的幫助下盡力解決,動員與靈性需求相關的家屬與患者及時溝通和承諾,以舒緩患者的擔憂和增加對可以預知的將來的了解和安排;3.對不能完成的心愿,則需工作人員和家屬與患者有效地充分溝通,使患者自己領悟,“認”可現實,以免增加自己的痛苦。
通過這種“賦予永恒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照顧方法,可以讓我們醫學專業照顧者,認可姑息照顧中面臨生命威脅的患者的思想中存在的、體現患者個人人文情懷的、以家庭為中心的靈性需求,厘清和明確患者的靈性需求、甚至是成為靈性困擾的不好完成的需求對患者本人、患者的家庭、對社會的意義與價值,借助包括醫學治療、藝術治療、音樂治療、文學治療、芳香治療、園藝治療、團隊照顧等多種手段完成對患者“幽谷伴行”式的有質量的陪伴,達到“生死兩相安”的結局。
結語
新的醫學模式和安寧療護工作是“全人照顧”的理念,既強調醫療技術進步為人類健康事業帶來的日新月異,同時也要關注個體在不同的環境下多元化的精神需求。理想的醫學不僅僅是功利目標的實現,還是哲學境界的知識拓展、精神發育與職業價值的最優化,是人類智慧之花在醫學園地里美麗綻放8。
1.金明武.生死觀探索[M].北京:線裝書局,2015:151-152.
2.王一方.醫學人文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36.
3.陳勁松.靈性引導生活[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2.
4.王一方.醫學人文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14-120.
5.Hampton DM,Holis DM,Lloyd DA,et all.Spiritual Needs of Persons with Advanced Cancer[J].AM J Hosp Palliat Care,2007,24(1):42-48.
6.Deng D,Deng Q,Liu X,et al.Expectation in Life Review: A Term of Spiritual Needs Easily Understood by Chinese Hospice Patients[J]. AM J Hosp Palliat Care,2015,32(7):725-731.
7.Vermandere M,Lepeleire JD,Mechelen WV,et al.Spirituality in Palliative Home Care:a Framework for the Clinician[J].Support Care Cancer,2013,21(4):1061-1069.
8.王一方.醫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0.
/ 1.武漢大學中南醫院2.解放軍總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