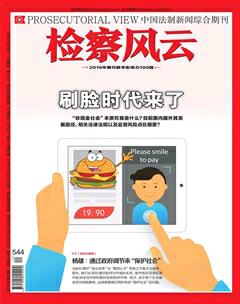居安思危:聚焦后現代社會的風險面孔
著名的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將后現代社會理解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征在于: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制造的風險。同時,他依據不同社會的類型概括出三類風險:第一類是前工業社會的風險,是自然力的作用,如地震、傳染病等;第二類是工業社會的風險,是資本原始社會的結架,如安全事故、勞資矛盾、兩極分化、失業、腐敗等;第三類是工業社會晚期的風險,是科技進步的產物,如環境污染、生態惡化、核技術威脅等等。
第一、二類風險稱為傳統風險;第三類風險稱為現代風險。貝克認為,我們當前生活的后工業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人類正遭受現代風險的威脅。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高速發展期,在此過程中,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控制體系正在趨于解體,而新的體系與機制還在建立與完善之中,尚未充分發揮作用,所以誘發和加劇了一些特殊風險。同時,由于我國高速發展壓縮了發展的時空,西方社會所產生的三類風險在我國同時顯現,既有前工業社會的風險,又有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風險。因此,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期這種風險呈現出一種混合狀態,具有共生特征,是一種“共生風險”,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處于急速社會變遷中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可以說是高風險的社會。
具體來說,我們正面臨如下風險的威脅:一是傳統類型的風險如傳染病、自然災害等依然是公共安全的隱患。還有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不斷涌現的風險,諸如貧富分化、城鄉差距拉大,失業、生產事故、群體性事件,極端個人暴力事件,勞資沖突和刑事犯罪等社會風險。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發生的新型社會風險。如恐怖主義、網絡犯罪、網絡暴力事件、民族分裂主義、國際販毒走私、信用卡詐騙犯罪等等社會風險。
從城市公共安全的視角看,在低標準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城市安全也存在著社會風險和隱患,有的已經給城市安全造成了危害。如非典、城市內澇、雨雪癱城、食品安全危機、嚴重刑事犯罪、群體性事件等等。因而增強全民風險意識,健全城市公共安全體系,預防和減少社會危機的發生是城市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公共安全問題大致可以分為自然類、社會類和國際類。自然類的主要是由自然環境本身所導致的自然災害、環境惡化等;社會類的主要是由社會性因素導致,包括民族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行為,交通安全、信息安全、群體性事件等;國際類則主要由國際環境因素導致,包括國際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攻擊、策反,國際恐怖主義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以及國際海盜(索馬里海盜)等的威脅,還有鄰國因爭奪資源而實施殺害漁民等事件。
中國社會轉型也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這期間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但是我國的城市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城市化的速度快,城市人口、城區擴容、城市設施建設等各方面都極速發展;二是我們的城市化還是低標準的城市化。城市的硬件設施發展的速度快,城市的軟件發展的速度慢,城市管理能力嚴重滯后,“安全瓶頸”和各類隱患突出。由于城市發展的速度快,各類隱患雖然顯現,還沒有集中爆發,所以,人們的危機和風險意識并不強,這使得預防措施顯得滯后。
面對城市風險加大 ,閆立老師就如何維護城市公共安全,建立城市安全體系的問題接受了采訪——
檢察風云:您認為當前城市公共安全存在哪些問題?
閆立:從風險社會理論看,城市公共安全中所有的風險隱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自然類的風險、社會類的風險和國際類的風險都在城市有集中反映。由于城市人口集中,波及面廣,傳播速度快,這些風險在城市發生,其社會影響大,造成的損失也大。應該說目前城市中處處有隱患,時時有風險。
檢:當前城市公共安全隱患很多,您能否舉例談談具體有哪些?
閆:當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隱患和危機尚處于潛伏期,還沒有形成集中爆發階段,有的已經發生的危機只是淺表層的隱患,如火災、地震、食品安全、群體性事件、環境污染、勞資矛盾等等。為什么說當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隱患和危機處于潛伏期?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城市化的建設速度太快。西方國家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建設城市化進程,我國壓縮在十幾年完成。建設速度快造成硬件完成了,管理的軟件跟不上,埋下了隱患,一遇情況即容易發生事故。比如,地下管網建設缺乏系統性綜合規劃,在布局規劃時,上下水、電力、電信、燃氣、供暖等管理部門相互分隔,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和協調,一旦地下管網出現問題即難以應對。又如我國地鐵線路多是單向路線,一旦出現緊急情況,逃生和救援存在一定的困難。還如城郊結合部“棚戶區”人類復雜,混亂不堪,有的就是藏污納垢的場所,極易發生問題,西方的貧民窟現象也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此外,上海目前2633幢高層建筑有玻璃幕墻,有的專家估計有4000幢,這些玻璃幕墻一旦老化都是潛在的危機。上海的高層建筑中的電梯、大型商場的電梯也有壽命期,一旦老化也存在著危機。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所以我說城市中時時有隱患,處處有風險。
檢:您認為造成城市公共安全隱患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閆:我個人認為,低標準的城市化必然埋下安全隱患。我們痛心地看到樓倒倒、橋塌陷、路塌方等一系列豆腐渣工程,這些工程不出事故不正常,出事故倒是正常的。那么又為什么造成這種現象呢?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政府社會管理能力的滯后和均等化公共服務的缺失。公共安全是一項基本公共安全產品,類似消防站點的合理布設,加強建設社會警務室、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等,都是均等公共服務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一些經濟適用房和保障房社區必須考慮綜合公共服務,通過設置必要的社區停車場地以預留消防通道、建設避難點(場所)等措施,才能保證公共安全產品的有效提供,但我們這方面還有一定差距。
檢:您認為當前城市公共安全體系建設應注意解決哪些問題?
閆:我認為,當前黨中央提出的社會管理創新和上海市落實一號文件鄉鎮街道職能轉換的具體改革,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破解城市公共安全“安全瓶頸”的根本之策就在于提高政府社會管理能力,創新社會管理辦法,完善社會管理法律,探索公共安全應急機制。同時,需加強均等化公共服務建設,特別是必要的公共安全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設置。endprint
檢:請您談談公共安全應急機制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閆:公共安全應急機制是一定范圍內社會各種組織、群體和個人對各種危及公共安全的事態采取應急反應的具體制度和措施。包括:(1)預警機制;(2)處理機制;(3)反饋與評估機制;(4)指揮協調機制;(5)保障機制;(6)國際合作機制。
檢:國外大城市管理普遍接受了“風險管理”的理念,您認為我國應該如何加以借鑒?
閆:“風險管理”的理念目前在國外大城市管理中普遍運用。我們也應合理借鑒。目前我們的風險意識不強,處理危機的能力也欠缺。而日本政府在城市規劃中對防火通道、防火街區、避難點、社區消防水源;生命線工程的抗災防災、災后城市恢復、巨災保險等內容系統考慮,增強了城市安全標準。英國政府把內閣緊急事務秘書處打造成風險管理平臺,傳播經驗,提高防災避險指導,加強政府與公眾溝通。我國臺灣地區高層住宅有專門的應急預案,每年組織一到二次逃生演練。
檢:在國外一些國家非常注意加強城市基礎信息數據庫管理,你認為我國城市基礎信息數據庫應如何建設?
閆:我國城市基礎信息數據庫目前還不適用城市公共安全的需要。如英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基礎工作扎實,若發生地震、火災、恐怖襲擊等重大突發事件,基本在24小時內能評估出災情,形成災情評估報告,這對于及時實施救援決策很有幫助,在應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應急管理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對人口、地理、建筑等作長期的調查、統計和研究,同時要有一個應急管理部門做經常性的工作。而我國城市信息分散,各自為政,底數不清,缺乏統一管理,不適應應急管理需要。如現有地上建筑美觀,而地下管線老舊失修,且相關資料缺失,一旦發現管線破裂,甚至連布局圖都沒有,給應急處置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檢:您認為我國當前城市應急預防工作做得如何?
閆:總體上我們是重建設輕預防,往往是事故過后,政府付出大量資金用于賠償善后,以安撫社會。如果我們換個思路,把這些錢用于當前的公共安全設施建設上,防患于未然,不出或少出事故和問題不是更好嗎?
檢:您對健全城市公共安全體系還有什么期望?
閆:在風險社會,特別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高速發展時期更要增強風險意識。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風險意識,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防患于未然;其次要下決心提高城市化的質量,要把速度與質量相統一;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創新社會管理,建立有效的社會組織,形成成熟的公共治理領域,讓民眾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來,最終完成由政府管理向“社會共同治理”的轉型。
采寫:夏草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endprint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