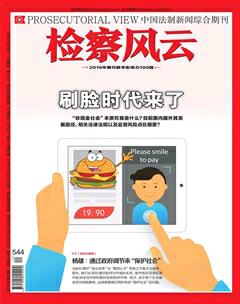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適用
劉棟

自2014 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ì)通過(guò)《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四中全會(huì)《決定》),并明確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以來(lái),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逐漸成為刑事司法領(lǐng)域中舉足輕重的一項(xiàng)內(nèi)容。在現(xiàn)有法律與相關(guān)政策的規(guī)制下,審查起訴階段與審判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已經(jīng)得到了學(xué)界廣泛的認(rèn)同。至于偵查階段是否同樣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處罰,目前則還有諸多爭(zhēng)議。
2014年10月四中全會(huì)《決定》首次明確規(guī)定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而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lǐng)導(dǎo)小組、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紛紛就此制定試點(diǎn)方案和試點(diǎn)辦法,該制度也引起學(xué)者們廣泛關(guān)注。就目前的法律法規(guī)及政策內(nèi)涵來(lái)看,該制度并沒(méi)有十分明確的概念,但學(xué)界對(duì)此都有了基本的共識(shí),即:認(rèn)罪體現(xiàn)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rèn)自己的行為及犯罪性質(zhì),但這種承認(rèn)必須是基于自愿而非強(qiáng)迫;認(rèn)罰不僅包含接受實(shí)體法上可能的處罰后果,也包含程序法上可能引起的程序后果;而從寬也當(dāng)然地包含了實(shí)體從寬和程序從寬兩個(gè)方面。
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可行性
有學(xué)者鮮明地指出,認(rèn)罪認(rèn)罰制度的適用應(yīng)當(dāng)有嚴(yán)格的訴訟節(jié)點(diǎn)限制,只能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發(fā)揮特定優(yōu)勢(shì),而不能適用于偵查階段。原因在于偵查階段該項(xiàng)制度的適用很可能會(huì)導(dǎo)致偵查人員放棄法定查證職責(zé),不去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無(wú)罪的各種證據(jù),過(guò)分依賴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定罪,而口供本身的獲取也可能會(huì)加劇偵查機(jī)關(guān)刑訊逼供的危險(xiǎn)性。筆者贊同上述考量,但依舊認(rèn)為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適用還是具備一定的可行性的。
首先,理論可行性。一方面,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并不必然滋長(zhǎng)刑訊逼供,刑訊逼供也不會(huì)因?yàn)椴贿m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而處于真空狀態(tài)。從思想和制度上的“有罪推定”到程序上的依靠口供,刑訊逼供的產(chǎn)生有著多方面多層次的原因,但在無(wú)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沉默權(quán)以及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逐漸確立的態(tài)勢(shì)下,如果偵查訊問(wèn)得到有效監(jiān)督以及部分偵查訊問(wèn)人員素質(zhì)得到提高,刑訊逼供現(xiàn)象將會(huì)大大減少,甚至得以解決。刑訊逼供有其自身存在的基礎(chǔ),但筆者認(rèn)為,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并不必然滋長(zhǎng)刑訊逼供。
另一方面,偵查階段與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呈現(xiàn)出程序遞進(jìn)的過(guò)程,每一訴訟過(guò)程都可能會(huì)為冤假錯(cuò)案提供相應(yīng)的生長(zhǎng)土壤,而偵查階段的可能性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因此許多制度的適用會(huì)得到限制,但同時(shí)也會(huì)衍生出相應(yīng)的制約機(jī)制,制度的產(chǎn)生本身就存在相輔相成的過(guò)程。在當(dāng)前法律法規(guī)與政策都未明確排除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形勢(shì)下,全面否定的做法在筆者看來(lái)還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實(shí)踐可行性。在當(dāng)前司法改革不斷深化,依法治國(guó)全面貫徹實(shí)施的大背景下,對(duì)偵查機(jī)關(guān)偵查活動(dòng)的監(jiān)督力度有望大大增強(qiáng)。2015年以來(lái),最高人民檢察院選擇山西等10省市進(jìn)行試點(diǎn),由各地檢察院向公安派出所派駐檢察室或檢察官,開(kāi)展對(duì)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dòng)的監(jiān)督工作。試點(diǎn)以來(lái),檢察機(jī)關(guān)監(jiān)督公安派出所立案5243件,對(duì)違法偵查活動(dòng)提出糾正意見(jiàn)15162件次,促進(jìn)公安派出所辦案質(zhì)量明顯提高……偵查活動(dòng)中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非法取證案件是檢察院派駐公安派出所進(jìn)行刑事偵查活動(dòng)監(jiān)督的重中之重。這一監(jiān)督工作的全面開(kāi)展無(wú)疑為偵查階段中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提供了合適的司法環(huán)境。
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意義
依據(jù)刑罰目的論,犯罪人對(duì)其犯罪行為認(rèn)罪和真誠(chéng)悔過(guò)是改造的開(kāi)始。如果我們認(rèn)為刑罰的目的之一是矯正犯罪人的行為,那么從一開(kāi)始就予以從寬處分,正是給那些已經(jīng)有悔改、矯正表現(xiàn)的人( 認(rèn)罪認(rèn)罰之人) 一個(gè)機(jī)會(huì),使之更快地回歸社會(huì)。在貫徹落實(shí)我國(guó)寬嚴(yán)相濟(jì)刑事政策的基礎(chǔ)上,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的制度設(shè)計(jì)在司法改革的深化過(guò)程中不斷體現(xiàn)著自身價(jià)值:一方面秉承人道主義原則和我國(guó)傳統(tǒng)的仁愛(ài)和寬恕理念;另一方面,極大地優(yōu)化了刑事司法過(guò)程中的資源配置。而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又有著自身獨(dú)特的意義。
第一,節(jié)約偵查階段的司法資源。由于偵查階段需要花費(fèi)較多的人力、財(cái)力、物力和時(shí)間等寶貴的司法資源,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能真誠(chéng)悔罪,將會(huì)為偵查機(jī)關(guān)指明偵查方向,大幅減少由于偵查方向偏差導(dǎo)致的司法資源浪費(fèi)。
第二,在現(xiàn)行司法制度框架下,雖然法律援助等手段也提前到了偵查階段可適用,我國(guó)偵查階段刑事律師的介入和參與還是存在著一定的現(xiàn)實(shí)困境,犯罪嫌疑人經(jīng)常會(huì)面臨權(quán)利架空的現(xiàn)實(shí)威脅,受到的正當(dāng)保護(hù)效益較之于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會(huì)大打折扣。確立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可適用性,將會(huì)帶動(dòng)律師辯護(hù)制度在此階段的完善,通過(guò)認(rèn)罪認(rèn)罰制度的適用細(xì)化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hù)權(quán),進(jìn)而通過(guò)律師辯護(hù)制度在偵查階段的完善,促進(jìn)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刑事合法權(quán)利和地位的強(qiáng)化,以此實(shí)現(xiàn)通過(guò)制度來(lái)促進(jìn)制度間的互動(dòng)和改善。
第三,彌補(bǔ)認(rèn)罪認(rèn)罰協(xié)商從寬制度在偵查階段的缺失。在我國(guó)的制度設(shè)計(jì)中,控辯雙方的協(xié)商只能是在檢察機(jī)關(guān)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控辯雙方就犯罪嫌疑人積極認(rèn)罪而獲得的可能優(yōu)惠達(dá)成協(xié)議。偵查階段合法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前提下,越早允許犯罪嫌疑人對(duì)自身行為和犯罪事實(shí)進(jìn)行承認(rèn),越有利于挽回或減少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并且其間的搜集證據(jù)及破案的難度和阻力也會(huì)越小。這也是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適用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因此,落實(shí)完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在偵查階段的適用,有利于彌補(bǔ)認(rèn)罪認(rèn)罰協(xié)商從寬制度在偵查階段的缺失,從整體層面保證該項(xiàng)制度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使之真正契合刑事訴訟各階段的制度運(yùn)行機(jī)制。
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適用的制度設(shè)計(jì)
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明確規(guī)定了偵查階段的案件處理方式:“在偵查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不應(yīng)對(duì)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應(yīng)當(dāng)撤銷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應(yīng)當(dāng)立即釋放,發(fā)給釋放證明,并且通知原批準(zhǔn)逮捕的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第二十二次會(huì)議通過(guò)的《關(guān)于授權(quán)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qū)開(kāi)展刑事案件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試點(diǎn)工作的決定》也規(guī)定: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shí)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shí),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guó)家重大利益的,經(jīng)公安部或者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zhǔn),偵查機(jī)關(guān)可以撤銷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duì)涉嫌數(shù)罪中的一項(xiàng)或者多項(xiàng)提起公訴。”endprint
從中可以看出,偵查機(jī)關(guān)在實(shí)體層面的司法處置權(quán)限十分小,只有在確實(shí)無(wú)罪或是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guó)家重大利益并經(jīng)公安部或者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zhǔn)的情形下才有案件撤銷權(quán),而第二種情形本身也存在著十分嚴(yán)謹(jǐn)?shù)闹贫劝才拧T诂F(xiàn)有法律框架下,突破偵查階段的特殊性而強(qiáng)硬地從實(shí)體上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可能會(huì)帶來(lái)一系列難以預(yù)估的后果。但如前所述,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當(dāng)然地包含了實(shí)體從寬和程序從寬兩個(gè)方面,在實(shí)體難以突破的情形下,可以側(cè)重考慮在程序上對(duì)其進(jìn)行制度設(shè)計(jì),并形成刑事訴訟中整體有效的制度框架。
首先,保障認(rèn)罪認(rèn)罰的自愿性。在完善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應(yīng)當(dāng)采取有效措施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rèn)罪認(rèn)罰表示確實(shí)出于自愿。在偵查階段,由于主要任務(wù)是搜集證據(jù)和查獲犯罪嫌疑人,偵查活動(dòng)具有比刑事訴訟中其他專門機(jī)關(guān)的訴訟活動(dòng)更為突出的強(qiáng)制力,因而犯罪嫌疑人在此階段容易受到脅迫而作出非自愿的認(rèn)罪表示。所以,要在偵查階段確保犯罪嫌疑人認(rèn)罪認(rèn)罰的自愿性,應(yīng)當(dāng)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由于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偵查破案的過(guò)程會(huì)減輕阻力,相應(yīng)延伸到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整個(gè)司法程序會(huì)提高相應(yīng)效率。檢察機(jī)關(guān)和法院就必須對(duì)認(rèn)罪認(rèn)罰的自愿性作出實(shí)質(zhì)的考察評(píng)估,對(duì)此加以限制。
其次,細(xì)化偵查階段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的適用條件。由于偵查階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必須從規(guī)范視角明確在偵查階段能夠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的條件。學(xué)者們主張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時(shí),將案件進(jìn)行輕罪、微罪和重罪的類型化處理。筆者認(rèn)為,這是一種較為可取的做法。
再次,確立包括偵查階段在內(nèi)的認(rèn)罪認(rèn)罰反悔權(quán)。認(rèn)罪認(rèn)罰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作出的選擇,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的選擇自由尤其值得保障。雖然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向偵查機(jī)關(guān)承認(rèn)自身所犯罪行,接受偵查機(jī)關(guān)在程序上的從寬處理以及由此延伸至審判階段的實(shí)體量刑,但該認(rèn)罪認(rèn)罰行為并不必然產(chǎn)生最終的司法效力。即便是宣判后,被告人仍然有反悔的上訴權(quán),這是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的一項(xiàng)基本權(quán)利,程序可以簡(jiǎn)化,但不能以此剝奪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權(quán)利。
最后,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偵查階段檢察監(jiān)督的力度。被告人是否被從寬處罰,司法工作人員具有自由裁量權(quán),這一權(quán)力領(lǐng)域容易滋生司法腐敗,這就需要檢察機(jī)關(guān)加大在法律執(zhí)行過(guò)程中對(duì)高危領(lǐng)域和環(huán)節(jié)進(jìn)行犯罪預(yù)防的力度,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使加大監(jiān)督、預(yù)防力度。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上海交通大學(xué)凱原法學(xué)院研究生)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