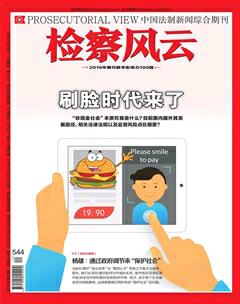開啟360度無死角式監管
李延
2017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其中有幾個比較新的提法:一是強調“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即所謂的無死角監管;二是強調“更加重視行為監管”,注重從被監管主體的金融行為來應對監管機構,降低監管套利的空間;三是強調“有風險沒有及時發現就是失職、發現風險沒有及時提示和處置就是瀆職”,即監管問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奠定了未來至少五年金融監管的基調,對于非現金社會涌現的新技術、新業態,無疑也確定了基本主題。
就非現金社會的監管而言,當前尤其需要監管部門關注的是眾多缺乏立法和執法覆蓋的灰白區域,運用穿透式的監管方式滲透真空地帶。非現金社會的發展加劇了混業經營的特征,不同種類的金融業務之間盤根錯節,相互交織、鉤稽,使得業務形態多樣、易變,不易簡單地界定監管的歸屬和權責。有的支付機構提供的創新服務或產品,實質上以損害平臺用戶的權益為牟利手段,但消費者很難訴諸救濟。近期有媒體報道,某消費者投訴在第三方支付機構環迅支付上遭遇失聯商戶。在我國,第三方支付平臺對于所接入企業的資質和信用審核責任一直比較模糊隱晦。部分小型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了提升業務空間,下調準入企業的資質標準,乃至不對平臺企業進行資質評估,給平臺用戶的權益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2015年,人民銀行曾發布《非金融支付機構支付業務報告管理辦法》(試行),規定支付機構和銀行機構同時向央行下轄中心支行報送與支付機構支付業務相關的報告,包括重大事項報告、月報、季報和年報。但實際操作中,第三方支付機構很可能與商戶串通,或者怠于履行自身義務。作為消費者,要追究平臺的法律責任也往往非常困難,因為第三方平臺作為信息中介,往往并不承擔商戶的信用審核義務。
基于這樣的原因,監管部門開始要求支付機構提取備付金,以保障平臺用戶權益。例如,自2017年4月17日起,支付機構需將客戶備付金按照一定比例交存至指定機構專用存款賬戶。但衍生的新問題是,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備付金賬戶開立不規范、使用不合規、未建立有效的備付金核對校驗機制、存管銀行未有效履行監管責任等。非現金社會的金融監管必然需要對這些細枝末節的地方進行實質的規范,這也將考驗我們的監管智慧。
消費者
金融隱私權保護箭在弦上
霍姆斯大法官說:“法律從人類本性的需要中找到了它的哲學。”隱私權在法律中的確立,正是社會進展和人們社會觀念發展的產物,并且隱私權的內涵外延也隨著社會變遷出現了重大的改變。在非現金社會時代,個人隱私主要以“數據”的形式表現出來,即我們所說的“信息隱私權”,比如信息持有者的信用狀況、消費習慣、財產狀況和財產流向等。
第三方支付用戶的隱私安全與反洗錢要求下的信息披露事實上存在著天然的對立性,信息的披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隱私權的侵犯,因而金融隱私權的保護是與信息披露以及打擊洗錢犯罪相互沖突的,保護隱私權和知情權之間存在著天然的鴻溝。我國現有的金融消費者資信狀況保護規則只是籠統地提出原則性規定,基本還處于“三無”狀態:一是無金融消費者保護意識,金融產品消費者的保護還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二是無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體系,目前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但對金融消費者的隱私權等保護適用性不強;三是無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目前還沒有什么監管機構明確承擔和履行金融消費者隱私安全的保護責任,受理消費者投訴。
傳統上各國法律一般都規定金融機構對在業務中取得的消費者個人金融信息負有保密義務,僅在司法調查、金融稽查、稅務調查或者反洗錢等場合存在例外。在首開英美國家銀行對金融隱私權負有保密義務先河的“圖尼爾”案中,英國上訴法院便援用“默示條款”理論作為認定銀行承擔該種義務的基礎。該案法官認為,銀行對金融隱私權保護的范圍不限于客戶賬戶本身,還應包括銀行因其與客戶關系的存在而可獲得的任何信息,并且這一金融信息保護義務并不因銀行與其客戶結清賬戶或停止使用賬戶而終止。
我們的監管部門,目前需要做的,首先是出臺法律規則讓金融隱私權保護有法可依。1993年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當時的立法背景與目前我們非現金社會的環境早已相去甚遠,難以成為有效的法律救助工具。未來針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立法,應當明確消費者權益和金融機構、支付機構的義務,體現立法向弱者傾斜。同時,還應設立專門的金融隱私權保護機構,并賦予其一定的執法權,深化監管機構對于消費者隱私權益保護的滲透度和有效性。通過法律手段懲處侵犯隱私行為是我們的事后救濟手段,而事前要做的則是讓電商平臺、第三方支付機構等盡可能少地掌握和手機用戶與交易無關的信息。何謂與交易有關的信息,又是一個我們監管部門需要反復斟酌的概念。
前沿科技
助力提升非現金社會監管效率
以最新的科技手段服務金融監管是目前國內金融監管的一個基本方向。2017年5月15日,央行稱成立金融科技委員會,加強對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規劃和統籌協調,并加強監管科技的應用實踐,積極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豐富的金融監管手段,提升跨行業、跨市場交叉性金融風險的甄別、防范和化解能力。例如,將人工智能引入監管系統,可以有效地解決監管者的激勵約束問題。其優勢在于,人工智能監管不需要考慮薪酬和獎勵,基于人工智能的監管系統可以依據監管規則即時、自動地實施監管,避免因激勵不足導致的監管不力等問題。此外,人工智能還能解決不少個人監管者無法處理的問題,例如如何判斷一個金融機構或者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特定行為是否會導致系統性、全局性的風險。這個問題如果由監管者主觀判斷,會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且很難全局性分析,而人工智能可以較好地考慮全局,納入所有需要重點分析的因素,并依靠案例輸入和自我學習不斷加強自身的決策能力。
監管科技目前仍處于起步的階段,其效用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體現。但非現金社會涌現出的很多問題實際上更多的是技術問題,例如前面我們提到的如何界定什么是金融交易過程中金融機構“必須”獲取的消費者信息。如果我們的監管部門能通過高效、科學的技術手段予以偵查、應對,那么很多創新型的業務或許可以落地得更為順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