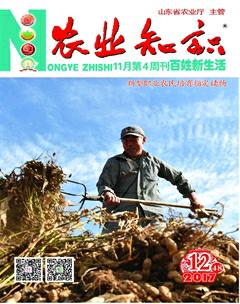當年那些初二畢業的孩子
張豐
經濟學家羅斯高最新的演講談到了一個數據,“現實是,有63%的農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這個數據或可商榷,但鄉村教育的問題仍需直視。妹妹就是這其中的一員,她讀到初三第一個學期,第二個學期開始,就到城市打工了。
那一年,農村取消了中專。初三畢業,只有考高中一條路了。我問她:“為什么不想上高中呢?”“考不上啊。”“也許能考上呢?”“那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學。”持這種看法的農村孩子很多。當年在我們那里,女孩子中,能讀到初中三年級,已經算比較罕見了。父親有點愧疚,最終還是接受了這樣的現實。
很多男孩子選擇在初二退學。大部分農村孩子,都是7歲開始讀小學一年級,到了初三畢業,也才15歲,出去打工的話還是童工呢。初二、初三,都是孩子正在發育的時候,在學校多待一年又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是初三畢業,就要面臨中考。到底要不要考呢?初三畢業又不參加中考的話,可能會影響到學校的升學率。
這種看法,很有“新聞性”,其實卻不太符合實際。對很多農村孩子來說,初二退學其實更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他們不會用“退學”來形容自己的行為,而是會大大方方地說出“畢業”兩個字。“你幾年級畢業?”“我初二畢業。”畢業是很正規的“結束”,而不是一種意外。這兩個字甚至表達了自己的滿意之情,就和那些能讀完初中的孩子一樣圓滿。
事實上,那些正常讀完初三的孩子,才讓人看著有點“不足”呢:既然不想考高中,那讀初三干嘛呢?初二畢業,已經可以去打工啦。當然,這是童工,但是他們并不在乎,家長也不在乎。很少有正規的企業會接受童工,這沒關系,就做不那么正式的。男孩子就這樣走向了裝修工地,他們跟著包工頭或者鄰居家的哥哥,按天計酬。到了18歲,他們就已經成為老手了。
我讀高中之前,村里只有很少的人讀過高中。上世紀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都沒有高中生。對農村孩子而言,考大學是一個太漫長的旅程,那時升學率很低,考高中,篩掉90%的學生,高考,又要篩掉90%。沒有哪個家長會天真地認為自己的孩子一定能夠成功,農民的孩子,最終的歸宿還是田野。
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人們開始外出打工,很多家長認識到了讀書的重要性。“要識字”,成為對孩子的硬性要求。最好能夠自己寫信回來(那時還沒有電話),最差也要能辨別城市的路名,不然會成為睜眼瞎,這是第一批進城務工者的深切體會。因此,很多家長都會把孩子供到小學畢業,那時還沒有實行義務教育,讀小學還需要一點點費用。
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到城里打工的孩子,給家里來了一封信,但是信不是寄到自己家,而是寄到了我家,因為父親是教師,可以幫他們讀信,也可以幫忙回信。當然,打工者的信,也有可能是代筆。最早一代打工者,往往是剛剛結了婚。妻子會臉紅紅地問:信里有沒有問我和孩子?大家一陣哄笑,大多數時候的答案都是沒有,信里往往只交代具體的事情。
我讀大學的時候,最早的一部電話出現了,裝在村干部家里。喇叭里會大聲喊出哪家來了電話,快過來接聽。通常情況下,會10分鐘后打過來。后來我家也裝了電話,也會去通知鄰居來家里接電話。等待的幾分鐘,成為迷人的時刻,鄰居激動和幸福的感情,在臉上就能看出來。
從那時起,在外打工的人就不再寫信回來了。等到有了手機,甚至可以視頻,識字就不再是必須的了。當然,那些初二就畢業的孩子,所認識的漢字已經足以讓他們在城市生活了。大部分農村孩子,從小就認清了自己的命運,讀到初中就去打工,這就是所有人的共識。如果哪個孩子成績非常棒,反而會讓家長困擾,該不該參加中考呢?好在他們只是小學成績不錯,到了初中,就掉隊了,家長反而也釋然了。
在鄉村,能夠有考大學志向的,往往是教師子弟。即使是鄉村教師,也能窺見到知識中所藏的秘密。我上高中的時候,那些從農村考來的,大部分都是教師子弟。他們是鄉村里的做夢者,比農民家的孩子文靜一點。而當教師的父母,往往藏著很大的志向,希望子女能夠考上大學,改變全家的命運。因此,鄉村教師可能是內心相當痛苦的群體,他們到了中年,還沒有和命運達成一致。
那些一天高中都沒有讀過的人,那些初二就畢業的孩子,他們對此似乎沒有太多憂愁。而這是需要改變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