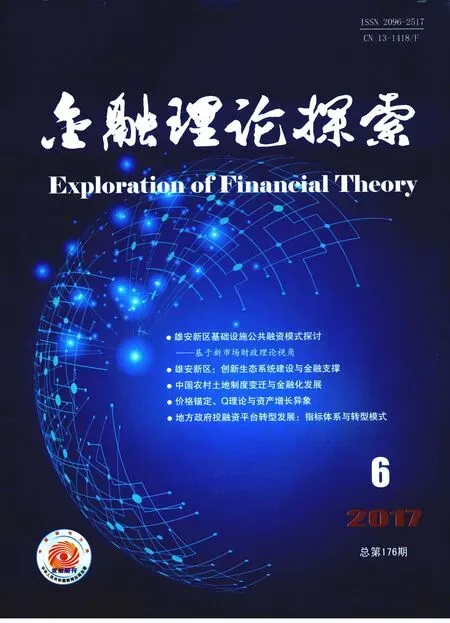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探討
——基于新市場財政理論視角
叢海濤,郭 凈
(1.中央財經大學 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北京 100081;2.河北金融學院 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51)
雄安新區專題
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探討
——基于新市場財政理論視角
叢海濤1,郭 凈2
(1.中央財經大學 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北京 100081;2.河北金融學院 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51)
雄安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問題具有特殊性,涉及到復雜的政府間公共財政關系。以新市場財政理論為分析框架,認為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主要面臨資金投入和風險管理水平遠超公共資金的能力范疇,財稅基礎薄弱、地方負債水平受限以及公共服務收入難以作為資金來源等三個方面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滿足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建設這一社會共同需要的融資需求,應協同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構建新的公共融資模式,如加強基礎設施的信息透明度建設,構建宏觀、部門、項目與合約三個層面的融資市場制度體系,創新與項目風險和收益相匹配的融資工具。
新市場財政理論;雄安新區;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
一、引言
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基礎設施融資都存在從公共財政體系向金融市場體系轉移的傾向,在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運營過程中采用PPP模式也成為一種趨勢。在這一背景下,雄安新區基礎設施融資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雄安新區的首要建設目標是建成綠色智慧新城,將面臨巨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和較長的投資周期,在公共財政支出之外需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作用。雄安新區基礎設施作為未來城市綠色發展、智慧發展的物理軌道,必須是綠色的、智慧的、可持續的,其“質量”和“技術”的內涵為基礎設施融資帶來了特殊挑戰和困難。同時,雄安新區新城建設涉及到的政府間公共財政關系較為復雜,縱向看,涉及從中央到省再到新區多個政府層級;橫向看,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涉及構成京津冀城市群的多個地方政府。雄安新區基礎設施融資問題的特殊性決定了其解決方案的特殊性,雄安新區作為改革創新引領區,需要以理論創新為指導探索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改革。
新市場財政理論是李俊生(2017)構建的以增強對當前國內外財政實踐解釋力和預測力為目的,將傳統市場財政學合理理論內核與社會公共需要論、以及制度性的研究方法與思想等跨學科研究成果相結合的新型財政學研究與分析范式[1]。它基于市場平臺觀強調了社會共同需要這一核心概念,重新定義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關系,重新定義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認為兩者都是市場交易平臺中的平等主體;與市場平臺觀相對應,重新定義了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強調了市場規則的重要性;該理論還認為,市場規則的范圍很廣泛而不僅限于法律法規。新市場財政理論為建設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提供了新的視角,包括加強基礎設施信息透明度建設,構建基礎設施融資市場制度體系以及創新融資工具等方面。新市場財政理論緊密聯系了當前的財政實踐,并考慮了中國思維和中國方案的融入,成為中國正在推動的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工具。
本文將嘗試以新市場財政理論提供的概念體系和研究范式探索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二、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面臨的目標和約束條件
(一)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
雄安新區的首要建設目標是綠色智慧新城,其基礎設施資金需求巨大。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具有基礎設施的一般特點,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如何選擇一個切實可行的投資運營模式是其推進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此外,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還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綠色化和智慧化,雖然后期運營成本低于一般基礎設施,同時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城市產業競爭力,但往往具有增量的前期建設成本,存在更為明顯的期限錯配和外溢性,而且還包含氣候變化風險、技術風險、政策風險等在內的更為復雜的風險因素。這意味著綠色智慧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不僅是較高的資金投入水平,還需要有較高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創新的風險配置工具相配合,超過了公共資金投入能夠解決的范疇,需要借助金融機構和私人部門的資金和能力。
(二)公共財政狀況和財稅體制改革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資金來源一般有以下幾個方面: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當前和未來的財稅收入、財政收費和使用者付費、政府負債以及其他來源[2]。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需要在中國財稅體制改革背景下探索一個新的公共融資框架,以實現基礎設施融資的經濟可持續性。中國當前的公共財政狀況和財稅體制改革對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有直接的約束,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打破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以往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對于土地財政有較高的依賴,通過在出售和交易環節獲得一次性的土地批租收入和相關稅收成為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但是近年來土地財政日益暴露出來種種弊端,不僅由于城市土地資源自身的有限性造成這類基礎設施資金來源不可持續,同時也引發了城市蔓延現象,不利于城市土地資源集約利用。雄安新區對土地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將土地批租制改為年租制,以打破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
2.財稅收入增長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財稅收入是具有較高可持續性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但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三期疊加”使得國內財政稅收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時波動性有所上升,未來從減輕企業稅負和激發經濟活力的目標出發,也難以進一步提高稅負水平,總之,財稅收入作為基礎設施資金來源中短期內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不過,中國正在通過財稅體制改革賦權地方政府,其改革內容包括:明晰政府間事權和穩定地方稅收基礎,探索通過房地產稅的制度設計推動地方公共財政轉型,探索一定條件下地方政府未來財稅收入資本化的手段(如市政債、稅收增量融資等),這些改革措施將有利于提高地方財稅對基礎設施的支撐能力[3]。需要注意的是,雄安新區還面臨著一些特殊的財稅收入狀況,即自身的經濟規模較小,財稅收入基礎薄弱,其未來的經濟規模和財稅收入基礎將隨著承接非首都功能帶來的稅源遷入而有所擴大,但最堅實的財稅基礎取決于雄安新區未來發展出高端高新產業和服務型經濟。
3.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面臨限制。近年來,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所形成的隱性債務風險受到廣泛關注,根據新《預算法》以及宏觀金融風險防范的要求,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將面臨上限約束,同時中國還將通過“開正門,堵偏門”的改革,允許地方政府在一定條件下發行市政債。但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雄安新區還難以作為市政債的發行主體,其地方政府財力和信用都比較有限,因此亟需發展一個不單純受制于地方財政實力的、以市場化機制運營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模式。
4.公共服務收費改革具有政治含義。使用者付費等公共服務收費也是具有較高可持續性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它有利于增強公共服務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價格聯系,使得地方能夠通過自有的收入資源支撐當地的區域性公共服務。但是,公共服務收費具有一定的政治含義,需要基礎設施實現面向所有公眾的公平接入和體現包容性,例如,城市的水資源供應要能保證低收入群體也同樣消費得起,因此其定價不能太高,存在收費上限,這就導致了公共服務收費形成的收入可能并不足以彌補基礎設施的投入成本。在公共服務收費方面,雄安新區還具有特殊性。雄安新區當前處于人口導入初期,市民等公共服務對象的規模和消費能力還難以確定,同時,必須將提供高標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良好的環境條件作為吸引高素質技能勞動力的前置條件。顯然,雄安新區還難以將公共服務收費作為其新城建設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
三、以新市場財政理論的核心概念重新界定問題
(一)新市場財政理論
李俊生的新市場財政理論認為,財政活動的本源是滿足社會共同需要,圍繞社會共同需要這一核心概念,李俊生發展了市場平臺觀、政府參與觀、市場規則觀和公共價值觀等概念體系[1]。這一理論的實質是把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和以企業為代表的私人部門置于地位“平等”的市場平臺之上,倡導融合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思想和方法,分析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基于公共價值最大化和私人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在市場上進行博弈的過程和機理。
傳統的市場財政理論的核心概念和邏輯起點是市場失靈。這一理論下的市場和政府是配置資源的兩個對立主體,政府是居高臨下的,一旦市場出現失靈問題,政府就會通過“規制”、財政政策等手段“干預”市場,甚至代替市場完成某些物品和服務的供給。但是,在面對政府債務、土地財政、PPP、政府采購等問題,傳統的市場財政理論越來越缺乏解釋力和預測力,這種分析范式忽略了所有這些問題所包含的一個關鍵環節:政府在按照市場運行的規則與私人部門合作、交易。尤其針對綠色智慧城市建設這個命題,傳統的市場財政理論更是難以進行解釋并給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在綠色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私人部門是以私人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從事活動的,“綠色”“低碳”“韌性”“可持續”是政府作為公共部門的代表所追求的公共價值,而政府在彌補這些公共品的空白和差距方面又存在規制不能和規制不足的政府失靈問題。
舊的市場財政學實際上是以凱恩斯總需求經濟理論為基本分析范式解釋和預測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財政活動,其財政分析范式源于盎格魯-撒克遜學派。李俊生提出的新市場財政理論強調了財政活動是超經濟形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并不限于市場經濟形態。李俊生發展了歐洲大陸學派財政理論的合理內核,借鑒了社會學、產業組織學、政治學等學科對市場定義和作用的分析,重新界定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把市場看作是提供規則體系的平臺。
財政學是應用性極強的一門社會科學,其解釋力和預測力體現在對各種財政現象和政府決策的分析能力上。李俊生的新市場財政理論緊密地聯系了當前的財政實踐,并考慮了中國思維和中國方案的融入,為中國正在推動的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工具。
(二)市場平臺上的基礎設施融資模式
當前的主流公共財政學以“市場失靈”解釋政府財政活動。但是在雄安新區,基礎設施融資來源和參與主體是多樣化、復雜的。在新城規劃和建設初期,政府的公共資金將是主導性的資金來源,同時,政府對“綠色”“低碳”“韌性”“可持續性”等公共品負有主要的供給責任。但是公共部門的資金將會受到雄安新區公共財政狀況和信用能力的限制,必須要廣泛動員私人部門的資金,同時,基于綠色智慧城市建設運營的復雜性和專業性,還需要與私人部門廣泛合作以借助后者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在負有支出責任的政府主體、市場投融資主體多元化背景下,可以預見雄安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還需要借助一些混合金融平臺和共同融資結構,使得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形成更加復雜的交互作用關系。實際上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局面下,已經很難再用二元對立的“市場失靈”理論去解釋雄安新區的公共財政活動了。李俊生以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為財政學本質特征重新定義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構了具有強大解釋力和精準預測力的財政學研究范式,其核心概念體系有助于解釋雄安新城建設中存在的復雜的財政活動,并可以導出具有啟發性的雄安新區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
在李俊生提出的研究范式中,社會共同需要是一個最核心的概念。可以認為,形成雄安新區綠色發展的物理軌道和公共服務設施就是一種社會共同需要,滿足其資金需求是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財政活動的根本出發點。
在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是什么關系?在李俊生看來,市場和以企業為代表的私人部門并不是同一個概念,市場其實是一個平臺,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是在這個平臺上相互作用的行為主體,他們的市場地位應該是相同的。這就解釋了當前世界范圍內正在廣泛興起的PPP模式,其實質是政府與私人部門為了實現各自目標而形成的合約化的長期伙伴關系。對于政府與私人部門設定各自的目標,新市場財政學引入了公共價值和私人價值這一對矛盾統一、一定條件下互為因果的概念。對于雄安新區的綠色智慧城市建設來說,政府的公共價值就是最大化按照社會邊際成本貼現的具有外部性、長期性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應,而私人價值就是最大化按照私人風險回報率要求貼現的基礎設施資產的未來現金流。
與市場平臺觀相輔相成,李俊生提出了政府參與觀,認為政府不是凌駕于市場之上的行為主體,而是市場的參與主體之一。對于所有參與主體來說,市場規則非常重要,是所有參與主體(無論他們是競爭還是合作關系)都必須遵守的規則體系。當前,中國政府正在推動PPP模式在污水處理等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中的廣泛應用,但是實際落地的、真正意義上的PPP項目比例還較小,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還沒有秉承契約精神形成真正平等的伙伴關系,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兩者所在的市場還不是一個規則化、制度化的平臺,從而導致合約的可執行性較低。從新市場財政學出發,雄安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不能僅僅是鋼筋水泥的堆砌過程,而是要加強制度化、規范化的市場平臺建設,形成加強PPP合約可執行性的法律法規和規則體系。
李俊生還認為,市場規則包含的范圍很廣泛,法律法規只是一種上升到立法機構層面的市場規則,同時,任何市場規則的確立都是市場行為者相互博弈、相互妥協的結果。對于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建設來說,這意味著,信息透明度建設和能力建設對于市場形成協調一致的規則體系極為重要。近年來,根據全球綠色智慧城市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學術界還提出了綠色智慧城市需要以市民為綠色智慧城市之本,需要市民的參與式治理,進一步擴大了立規者的范圍。
四、新市場財政理論對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模式的啟示
(一)加強基礎設施信息透明度建設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價值體系,有效資源配置首先取決于雙方在決策中基于相關信息的掌握情況對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評價。
私人部門對于透明度的要求主要在于基礎設施資產的風險收益和投資環境兩個方面。私人部門對城市基礎設施資產參與的興趣由來已久,這源于基礎設施資產貫穿周期的風險收益特征,進入運營階段的基礎設施資產往往能夠提供長期的、穩健的收益,尤其適合那些具有匹配中長期負債端需求的保險金、養老金等資金的要求。但由于傳統的基礎設施項目普遍存在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的問題,私人部門不僅難以掌握最新的投資機會,而且無從及時追蹤項目進展,更難以基于歷史數據對項目進行合理的收益與風險預估。這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私人部門的投資風險與難度,使得基礎設施項目還難以成為私人部門可投資的資產類別。由此可見,基礎設施作為資產類別的風險收益等信息透明度對充分撬動私人部門資金是非常關鍵的。除此之外,基礎設施資產受規制和政策影響較大,私人部門需要分析和判斷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對于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部門而言,透明度的要求也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財政支出情況的透明度。由于政府具有“公權”保障,很難回避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問題,因此很難讓私人部門產生信任。李俊生認為,應當將“公權”剝離出來納入公眾視野,通過提高“財政透明度”以約束財政公權。財政透明度和可追責性有密切的聯系,沒有財政透明度,就沒有可追責性,特殊利益集團也容易發生尋租行為[4]。其次,財政投入績效的透明度,包括撬動了多少私人資本,對環境社會經濟的可持續性產生了什么影響,這方面的信息透明度為采用創新的公共融資工具提供了依據。
互聯網對未來綠色智慧城市有全方位滲透,帶來顛覆性的城市管理模式與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度,不僅提升了公共部門的決策效率,降低了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也將大幅降低私人部門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投資風險,為私人資本打造一個更為優良的投資環境。就雄安新區的綠色智慧城市建設而言,促進其基礎設施信息和數據的透明度建設,有利于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的資源配置作用。可以預見,通過加強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信息透明度建設,雄安新區可以促使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成為一種可投資的資產類別,其信息標尺和示范效應將使得未來私人資本參與中國綠色智慧城市建設的廣度與深度都將大為改善。
(二)構建基礎設施融資市場制度體系
主流的公共財政學以“市場失靈”為核心概念,而新市場財政理論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概念。基于“市場失靈”的視角,在財政支撐能力不足的情況下,PPP合約是制度設計的重點。但是,PPP僅是政府在項目層面和私人部門的長期合約,是項目融資工具。而將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公共財政出發點和歸宿,市場平臺良性運行的條件才是制度設計的重點,包括市場基礎設施、功能主體和所有參與方都須遵守的規則體系,在財政支撐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需要在三個層面進行討論:宏觀層面、部門層面和微觀的項目與合約層面。
1.宏觀層面
實際上,在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是最根本的。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基礎設施部門是產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投入要素,對于產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其交易成本和提升了產業競爭力,對于居民部門來說,滿足了其公共服務需求,提升了其勞動生產力和獲得感。我們要看到,沒有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難以落實“招商引資”和吸引高素質的勞動力,但更要看到,沒有高端高新產業和高技能勞動力,基礎設施融資的償付就會失去可持續的財稅收入和公共服務收費的支持。
對于雄安新區來說,認識到這一點更加重要。雄安新區所在的京津冀區域是全國大氣污染、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是全國水資源最為短缺、地下水漏斗最大的地區,是全國生態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矛盾最為尖銳的地區。雄安新區之所以面臨這些問題,其產生的根源在于我國傳統以資源環境為代價、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雄安新區打造綠色智慧新城,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就是要謀劃創新驅動、考慮環境社會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方式[5-6]。因此,從基礎設施融資可持續性的本源出發,雄安新區應積極探索有利的技術創新制度設計,以形成基于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綠色經濟和智慧經濟的創新元動力和核心競爭優勢。
2.部門層面
基礎設施部門的投融資市場化已經成為全球趨勢。基礎設施一般由政府規劃和建設,具有資金投入量大、工程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的特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傳統經濟增長動力面臨轉型,導致財稅收入增長趨緩,同時,為了應對危機,主要國家的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政府負債水平上升,繼而影響了政府通過資本市場為基礎設施融資的能力。正是在公共財政預算緊約束的背景下,出現了投融資市場化的趨勢,廣泛動員和撬動私人部門的資金成為基礎設施融資制度設計的主要目標。
綠色智慧基礎設施是基礎設施的綠色化和智慧化,體現了基礎設施在“質量”和“技術”上的要求。由于在建設運營過程中包含了技術風險、氣候變化風險、政策風險等更為復雜的風險因素,綠色智慧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不僅是較高的資金投入水平,還需要有較高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創新的風險配置工具相配合,借助金融機構和私人部門的資金和能力就成為必然。由于在綠色智慧基礎設施規劃、投資、建設、運營過程中,參與主體更多元化、合約復雜性和專業性更高,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更高,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更為明晰的法治保障、爭端解決機制和發展完善的市場規則體系。此外,綠色智慧基礎設施具有“綠色”“低碳”“韌性”“可持續性”等外部性特征,導致了風險收益不匹配,為了充分撬動私人資本,還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風險分擔和利益共享機制。
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風險收益特征是不同的,商業性和準公益性的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存在一定的收費機制和盈利模式,私人部門的資金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PPP模式有應用的基礎。而公益性的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一些基礎性的基礎設施如貫通的交通網絡[7]、地下綜合管廊和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等,仍然需要發揮政府在公共產品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另外,在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前期仍然需要充分發揮系統規劃作用和公共資金引導作用,但到了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中后期風險收益相對匹配的階段,應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避免政府的過度干預。
政府是參與市場博弈的主體之一。雄安新區面臨較復雜的政府間關系,應通過加強政府間聯盟以提升對于私人部門的議價能力。雄安新區可設立京津冀基礎設施基金作為區域財政協同的資金平臺,統籌京津冀地區用于綠色智慧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財政資金。為了突破區域財政能力的限制和充分撬動私人部門的資金,雄安新區可發展混合金融結構和共同融資結構的資金平臺,探索建立有利于緩和私人部門投資風險的財政擔保機制。對一些私人部門難以有效承擔的風險,如政策風險、監管風險等,可探索推動相應的政策性保險創新。
對于小型分布式綠色智慧基礎設施項目而言,缺乏聚合平臺以及標準化交易產品是其引入私人資本的主要障礙,例如:能效型項目通常體量過小,以至于私人資本進入單個項目的識別與交易成本過高;對于機構投資者而言,小型項目的規模也未達到其投資的最低要求。未來結合綠色智慧城市的發展特征,雄安新區可在兩方面推行資產證券化:一是對水務、交通運輸等市場化程度高、公共服務需求穩定、現金流可預測性強的行業開展資產證券化,即將項目收益權作為基礎資產發行證券;二是將分布式太陽能貸款、新能源汽車貸款等信貸資產經過重組形成資產池,以此為基礎發行證券。
3.項目與合約層面
由于面臨巨大的融資缺口和公共資金的預算緊約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融資模式。自2014年起,中國PPP全面啟動,超過22個國家部委和90%以上的省市地方均將PPP作為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區域開發、軌道交通和能源等建設的有效創新路徑。雄安新區綠色智慧城市項目采用PPP模式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一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和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增加對雄安新區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運營的投入,二是打造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典范。總結探索綠色智慧城市建設、運營和管理的經驗,形成綠色智慧城市項目利益分享和風險共擔的法律法規、標準和流程等制度框架。
2017年7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出臺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條例》)。雖然《條例》對當前PPP模式進行了規范,為已經發現和發生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式,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雄安新區作為以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為任務的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和財政部重點支持開展PPP項目的地區,應針對PPP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比如稅收減免、公眾參與、“物有所值”、定價調價等,將其納入地方性法規,通過開展PPP立法的先行先試為全國PPP模式的發展積累經驗,促進當地PPP項目有序、健康發展。
(三)創新融資工具
一是政府融資工具。主要是政府用以吸引投資者的債務融資工具。由于這類融資工具大多是有一定的免稅優惠,因此對于投資者來說具有較高的吸引力。此類融資工具包括:一般義務債券、收入債券、產業收入債券、綠色債券、合格節能債券、社會影響力債券、公共利益債券,低息貸款項目、能效貸款、資產估價清潔能源基金(PACE)、碳排放配額拍賣和使用費等。
二是開發收費。通常是針對開發項目對城市的影響收費,被作為城市可持續增長的資金來源。
三是公私合作。PPP、基于績效的付款、證券化和結構融資、巨債債券等。
四是私人部門。貸款損失準備基金,債務償付準備,貸款擔保,賬單融資、集合債券融資、集合租購、價值捕獲、稅收增量融資、慈善資金,國際非政府組織資金和一些合作融資工具等。
雄安新區在未來建設過程中可借鑒開發以上創新融資工具以匹配綠色智慧城市項目的風險與收益要求。由于雄安新區的很多綠色項目具有規模大、期限長、環境外部性明顯等特征,雄安新區可開發“基于績效付費”的金融工具,如環境影響力債券。作為結構性債券的一種,環境影響力債券與綠色債券的不同之一在于其并不具有一個固定的回報率,而是基于最終的環境績效來決定投資者是否能獲得約定本息以及政府獎勵。因此,環境影響力債券為確保項目達成特定環境目標提供了一個創新融資機制。在雄安新區的環境公益領域中,尤其是尚且缺乏使用者付費機制、主要依賴于公共資金的領域,環境影響力債券為緩解財政壓力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以白洋淀的水環境治理為例,通過事先設立水質目標,政府建立“基于績效給付”的機制,讓私人投資者在選中某個優勝水治理方案以及綜合服務供應商后,以貸款形式支持供應商全面鋪開水治理工程。最終政府根據第三方對水環境治理的效果進行評定并付費,而服務供應商則在獲取費用后向投資者支付本金與利息。
五、結語
雄安新區的首要建設目標是建成綠色智慧新城,其面臨著巨大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在雄安新區綠色智慧城市基礎設施融資面臨的公共財政約束下,如何突破當地政府信用和財力限制,建立市場化的公共融資體系?
李俊生教授是我國財政學術界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他認為中國應該推動傳統財政學理論的發展創新,以緊密地聯系中國當前的財政實踐,考慮中國思維和中國方案的融入,增強對現實的解釋力與預測力。在融貫中西財政理論及借鑒其他社會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李俊生教授提出了新市場財政理論,重新定義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認為兩者都是市場交易平臺中的平等主體。這一理論有助于解釋雄安新區新城建設涉及到的復雜的基礎設施公共融資活動。本文以李俊生的新市場財政學理論為指導,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核心概念,重新界定了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面臨的主要問題,并探討了雄安新區基礎設施公共融資體系的構建模式,主要涉及三個重點:基礎設施信息透明度建設,基礎設施融資市場制度體系,以及創新融資工具。
[1]李俊生.新市場財政學:旨在增強財政學解釋力的新范式[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7(5).
[2]程哲,蔡建明,歐陽如琳等.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成因、演化及創新[J].工程經濟,2016(3).
[3]李建華.我國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研究文獻綜述[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9).
[4]STIGLITZ J E.Markets,States and Institutions.Roosevel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EB/OL].(2017-06-01).http://roosevelt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
[5]牛文元.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鎮化的動力標志[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4(1).
[6]徐振強.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與智慧雄安的有效創新[J].區域經濟評論,2017(4).
[7]王俊.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市場化的演進與創新[J].改革與戰略,2015(7).
Research on Public Financing Mode of Infrastructure in Xiongan New Are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rket Finance Theory
Cong Haitao1,Guo Jing2
(1.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2.Research Center of Finance Innov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Hebei Finance University,Baoding 071051,China)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 Xiongan New Area has its specialty,involving complicated public financial relations among governments.The paper based its analysis on New Market Finance Theory and discovered that infrastructure public financing in Xiongan New Area mainly faces three problems.These problems are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level are far beyond public fund,inadequate fiscal and tax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limited local debt level,and improbability of transforming public revenue income into capital source.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 Xiongan New Area,new pubic financing mode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integrating public and private departments,improv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establish multilevel financing market system and compatible financing tools among innovation,project risk and profit.
New Market Finance Theory;Xiongan New Area;green smart city;infrastructure;public financing mode
2017-09-28
叢海濤,女,山東蓬萊人,博士,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可持續金融;郭凈,女,河北保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金融創新。
F830
A
2096-2517(2017)06-0003-07
李丹;校對:盧艷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