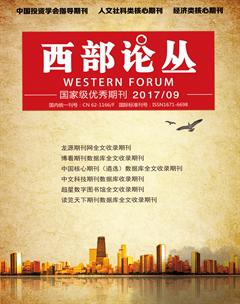淺析潘天壽的書法藝術(shù)
張婕
摘 要:潘天壽是中國現(xiàn)代文人畫大師。在繼承傳統(tǒng)文人畫基本形式的基礎(chǔ)上,也已完成了極具個性風(fēng)格的獨創(chuàng),創(chuàng)造了富于現(xiàn)代感的文人畫新樣式。在整個20世紀(jì),中國人思想觀念上充滿彷徨,呈現(xiàn)動蕩的中國畫壇上,潘天壽是立足于傳統(tǒng),承前啟后延續(xù)傳統(tǒng)繪畫的一面旗幟,他的書法作品也有獨特面貌。潘天壽藝術(shù)的不朽,正是源于他自身具有的豐富而鮮明的人文根源。
關(guān)鍵詞:潘天壽 藝術(shù)思想 書法藝術(shù)
一、生平
1897年3月14日,出生在浙江省寧海縣北鄉(xiāng)冠莊村。現(xiàn)代著名畫家,美術(shù)教育家。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早年署阿授、懶道人、三門灣人等別號,晚年多署頤者、雷婆頭峰壽者。
祖父潘期照是“國學(xué)生”,善耕耘,會置業(yè)。父親潘炳璋25歲舉秀才,人稱“達(dá)品公”。1920年畢業(yè)于浙江第一師范,受到過著名教育家經(jīng)亨頤、李叔同等教師人品學(xué)養(yǎng)的多方面熏陶。1923年被上海美專聘請為國畫教授,并與諸聞韻共創(chuàng)全國第一個中國畫系。1928年國立藝術(shù)院在杭州誕生,他被聘為教授,支持中國畫教學(xué)。又兼教上海美專、新華藝專、昌明藝專的國畫課。八年抗戰(zhàn),杭州藝專與北平藝專合并為國立藝專,他仍任國畫系主任,1940年任國立藝專校長,1957年任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華東分院副院長,1959年復(fù)任浙江美術(shù)學(xué)院院長,他曾任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副主席,美協(xié)浙江分會主席,蘇聯(lián)藝術(shù)學(xué)院名譽院長。潘天壽對中國畫的教育思想,教學(xué)體系和教學(xué)方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改變了傳統(tǒng)中國畫師徒相傳的教學(xué)方式,倡導(dǎo)了中國畫山水、人物、花鳥教學(xué)的分科,又主持創(chuàng)辦了全國當(dāng)時唯一的篆刻專業(yè),在教學(xué)上循循善誘,尤其重視人格教育。一生光明磊落,樸實正直,謙虛和藹,淡泊寡欲。從而成為名符其實的現(xiàn)代中國畫教學(xué)的奠基人。
二、藝術(shù)學(xué)習(xí)過程
青少年時期對于書畫的學(xué)習(xí):潘天壽在練習(xí)毛筆字的時候非常認(rèn)真,而且他把每天練毛筆字的習(xí)慣一直保持到晚年。由于對毛筆的運用熟練自如,為他日后作畫打下基礎(chǔ)。兒時的書法基礎(chǔ)使他繪畫中的筆墨大膽肯定,這個時期他的繪畫作用特點是粗放野逸,無論是花鳥還是山水,都是簡筆,筆墨不多卻十分概括生動。作畫時運筆用墨的生動變化就恰是于一幅書法作品。后來吳昌碩初次見到他的作品,便為之吃驚,稱之為“天驚地怪見落筆”,即使對其藝術(shù)啟蒙時期的充分肯定。
筆墨自具風(fēng)格:潘天壽用筆蒼勁以側(cè)鋒為多,凝重中見力度和剛度,墨色則力求整體而略其變化。色彩以原色為用,呈古雅調(diào)子;
書法風(fēng)格的形成期:以漢隸魏楷得基礎(chǔ),廣取黃道周、倪元璐、張瑞圖之長。善用硬毫側(cè)鋒,且結(jié)構(gòu)大小方扁多變,而整篇氣脈順暢。書壇謂之有“整整復(fù)斜斜,好如風(fēng)際鴉”的意境,書中有畫,頗具形式美;畫中有書,書中有畫。由于他的書法功力極其深厚,因此畫上的筆墨線條都是筆筆有力。
三、藝術(shù)思想
潘天壽對中國畫獨立價值的捍衛(wèi)和堅持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他認(rèn)為世界的繪畫可以分為東西兩大統(tǒng)系。中國傳統(tǒng)繪畫是東方繪畫統(tǒng)系的代表。統(tǒng)系與統(tǒng)系間,根本處相反而各有其極則,可互相吸取所長,然不可漫無原則,以徒炫中西折中為新奇。
①“文如其人”,在潘天壽身上,文格、藝格與人格統(tǒng)一的特征特別顯著。他的繪畫美學(xué)思想和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實踐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的繪畫美學(xué)思想是從繪畫實踐中提煉出的思想精華,而其繪畫作品又是美學(xué)思想的“感性顯現(xiàn)”。
潘天壽明確指出決定作品格調(diào)的高低,不在于玩弄筆墨技巧,而在于如何追求作品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說在作品應(yīng)該具有較高的思想性,正如他所說:“文藝作品歸根結(jié)底是在寫自己、畫自己,它不是江湖騙術(shù),而是人的心靈的結(jié)晶。”格調(diào)是作品的藝術(shù)總匯效果或藝術(shù)境界中體現(xiàn)出的精神境界,歸根結(jié)底是反映作者的精神境界。中國書法講究品德。鄧白在《潘天壽先生與三不朽》一文中說:“潘先生所以值得大家敬佩,不惟是他的畫品高,尤其是因為人品高。他有很高的做人標(biāo)準(zhǔn)和道德標(biāo)準(zhǔn)。”在學(xué)術(shù)上,他從不隨波逐流、不虛假、不做作,真實對待自己,真實對待藝術(shù)的品格。畢生的精力堅定地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民族書法藝術(shù),并體現(xiàn)了他高尚的人格與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完美統(tǒng)一的理想境界。潘天壽渾樸堅定、高風(fēng)峻骨的品行。奠定了他一生書法的基調(diào)。他的品行決定了他所選擇的藝術(shù)形式是充滿矛盾沖突,體現(xiàn)時代雄強和剛健質(zhì)樸民族精神的形式。
②藝術(shù)的民族性:潘天壽十分重視藝術(shù)的民族性,但他對藝術(shù)民族性持有發(fā)展的觀點,就是說民族性要與時代性相統(tǒng)一,民族的藝術(shù)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他曾在1957年《談?wù)勚袊鴤鹘y(tǒng)繪畫的風(fēng)格》中提出:“文藝上形成風(fēng)格,是脫不了歷史傳統(tǒng)輾轉(zhuǎn)延續(xù)的影響的。例如中國繪畫的表現(xiàn)技法上,向來是用線條來表現(xiàn)對象的一切形象的。因為用線條來表現(xiàn)對象,是最概括明豁的一種辦法。是合于東方民族的欣賞要求的。因此輾轉(zhuǎn)延續(xù)地直到現(xiàn)在,造成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高度明確概括的線條美。反過來說,沒有歷史相互延續(xù)的積累,也無法完成中國繪畫在線條上充分發(fā)展的特殊成就。”
③繼承與變革:潘天壽先生曾說:“借古”是手段,“開今”是目的。“借古開今”,即推陳出新,但“新”必須從“陳”中推出。也就是說“借古”與“開今”應(yīng)具有對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借古”,要求發(fā)揚優(yōu)秀傳統(tǒng);“開今”要求創(chuàng)造與時俱進(jìn)的新的藝術(shù)。藝術(shù)上的變革,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現(xiàn)代的社會、生活環(huán)境起了變化,人的思想意識必然起變化,藝術(shù)也自然會有變化。所謂新,不僅是新題材、新內(nèi)容,更重要的是新的感受、新的意想。出新,也就是要有時代性。同時,藝術(shù)家必須有自己的個性、風(fēng)格、特點。[1]
④造化與心源:對于藝術(shù)中的主客觀關(guān)系問題。潘天壽持辯證觀點。他在《論畫殘稿》中說:“畫為心物熔冶之結(jié)晶。”[2]另外在其著名畫論《聽天閣畫談隨筆》中提到:畫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畫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畫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自然之理法,又非畫中之理法也。因畫為心源之文,又有別于自然之文。故張文通云:“外事造化,中得心源。”
四、書法特征
蘇東坡說:“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3]會通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藝觀。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杰出代表,潘天壽先生在思想上繼承了這一文藝觀,認(rèn)為“不僅詩和畫同出一源,廣義地說,各個藝術(shù)門類都是同出一源的。”[4]
“一味霸悍”和“強其骨”,是欣賞和理解潘天壽書畫和思想的關(guān)鍵詞。潘天壽書法在他的藝術(shù)實踐中居于重要地位。正是因為他從小到大不間斷的書法練習(xí),才使他擁有了深厚的書法功力。從而在他畫面上反映的就是筆墨線條凝重有力、瘦挺奇崛、氣骨張開。流暢的書法也使他的畫面頗具形式美感。
潘天壽自幼酷愛書法,14歲進(jìn)入寧海縣城小學(xué)讀書,選購了《瘞鶴銘》和《玄秘塔》朝夕臨習(xí),愛不釋手。對書法用功日深,經(jīng)常臨讀碑帖,兼長各體,甲骨文、石鼓文、秦篆、
漢隸、章草等。
⑴潘天壽先生筆墨變化的淵源來自于擷取魏碑之精華,對東漢隸書摩崖石刻《石門頌》和東晉正書碑刻《爨寶子碑》都下過很深的功夫。在筆法上以結(jié)構(gòu)美為其特點,突破前人窠臼,加以變化,他采用扁筆,在黃字基礎(chǔ)上,對字的結(jié)構(gòu)做參差變化,氣勢連貫,“活眼”很多,注意追求全幅氣勢節(jié)奏而成整體,風(fēng)格豪邁飄渺,個性強烈鮮明,獨樹一幟。
(2)潘天壽的書法具有深厚的功底,行草師承二王、顏真卿、黃道周等傳統(tǒng)一派,其用筆勁健生辣,斬釘截鐵,于爽利中見綿厚,于方折中寓圓轉(zhuǎn)。
明末書風(fēng)之后,潘天壽東涂西抹的滿腹才氣才開始尋到了最合適的表現(xiàn)語言。他的書法斜畫緊結(jié),以側(cè)取勝,方折用筆,強調(diào)銳角造型,他盡力使其書法造型尖銳化,“尖銳化主要是產(chǎn)生分離,加強差異,強調(diào)傾倒。”這與他至大、至剛、至中、至正之個性十分相近。書法用筆以側(cè)鋒入,鋒利而不偏薄,而以中鋒運行,以保證線條的立體感和厚度。側(cè)鋒入筆,起筆之處就會造成三角的尖銳形狀,古人說:“側(cè)以取研”,“有鋒以耀其精神”。另外,也用方筆橫畫直入筆鋒,豎畫橫入筆鋒,好像要截切筆畫一樣,由此造成方折的形狀,方筆棱角分明,骨力開張,表現(xiàn)出竣利爽辣、氣骨雄強的效果。
他曾說過:“開始學(xué)書法,必須求法則,要正規(guī),要從正楷開始。學(xué)正楷要知道行、草書。學(xué)行草應(yīng)先學(xué)草書,再學(xué)行書,行書介于正、草之間。隸書也要學(xué),隸書可以用于題款,題在畫上較好看,篆書題款不多。我們所以學(xué)習(xí)漢隸魏碑,要取其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形似。”
(3)從布局和章法上看,他充分調(diào)度著字與字之間的聚散、避讓、生克,乃至由字與行、點線與空白的互動關(guān)系所構(gòu)成的收放對比、動靜對比、虛實對比,無不貫穿著造險、破險、以險制夷、反欹為正的創(chuàng)作思路,以服務(wù)于章法上的開合起落效果,而且打破行行相列、正文與署款主從分明的傳統(tǒng)習(xí)慣。
潘天壽存世書法一部分是條幅、屏樟、對聯(lián)等形式的作品,另一部分是他在畫上的題跋款識。他最擅長的書體是行草、次為篆隸,楷書較少見。由此知道,他偏嗜更適宜抒情的書體,因為這樣更能發(fā)抒他雄肆奇逸的審美理想--陽剛之美感。潘天壽的書法特征都標(biāo)志著他對傳統(tǒng)成規(guī)的反叛與突破,也體現(xiàn)著他對書法藝術(shù)的美學(xué)思考。
注 釋
[1] 潘天壽.1963年9月在泰安談中國話問題
[2] 潘天壽.《論畫殘稿》
[3] 《跋君謨飛白》,《東坡題跋》卷四,《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
[4] 《潘天壽論畫筆錄》《詩畫融合,相得益彰》上海人民書畫出版社。1984年版
參考文獻(xiàn)
[1] 《潘天壽》盧炘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2] 《潘天壽》郝興義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年2月第1版
[3] 《潘天壽》楊成寅 林文霞著/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6] 《潘天壽書法形式張力研究》郭文志著
[7] 《潘天壽談藝錄》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 1985年
[9] 《淺談潘天壽的書法對其繪畫的影響》李欣羽著
[11] 《試議獨樹一幟的藝術(shù)大師-潘天壽先生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劉鋼著
[12] 《也談潘天壽》劉暢著
[20] 《潘天壽藝術(shù)隨筆》徐建融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2年3月第1版